寫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寫作文
張大春
閱讀分享:一個人不管取得多么驕傲的成績,都應該飲水思源。應當記住是自己的老師為他的成長播下最初的種子。它點燃了心中的理想,放飛了手中的希望。星星火種,燎原之勢,它給了學子生活的樂觀,學習的積極,工作的激情。(特約教師:陜西省榆林市靖邊縣第七中學 景毛毛)
我在小學五年級遇到了俞敏之老師。俞老師教語文,也是班主任,辦公桌就在教室后面。那一年教育政策定案,初中聯考廢止。而俞老師卻神色凝重地告訴我們:“你們如果掉以輕心,就‘下去了!”
俞老師使用的課本很特別,是一本有如小說的兒童讀物,童書作家蘇尚耀寫的《好孩子生活周記》。兩年以后我考進另一所私立初中,才發現蘇尚耀也是一位語文老師。
我初見蘇老師,是在中學的校長室里。那是我和另一位女同學沈冬獲派參加臺北市中學生作文比賽。行前,校長指定高年級的語文老師來為我們“指導一下”。
在校長室里,蘇老師并沒有提供什么作文功法、修辭秘籍,只是不斷提醒:要多多替校刊寫稿子,“寫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寫作文”。至于我們所關心的比賽,他也只是強調:“參加就是參加了,得不得獎只是運氣,不必在意。”
說起俞敏之老師平時說話扼要,句短意白,從未賣弄過幾十年后非常流行的那些“修辭法則”,也沒有倡導過“如何將作文提高到滿分”的諸般公式。印象中她最常鼓勵我們多認識成語,不是為了把成語寫進作文,而是因為成語里面常常“藏著故事”。
有一回我在一篇作文里用“載欣載奔”這個成語,俞老師給畫了個大紅叉,說:“怕人家不知道你讀過陶淵明嗎?人家的東西拿來你家,你也不看一眼合不合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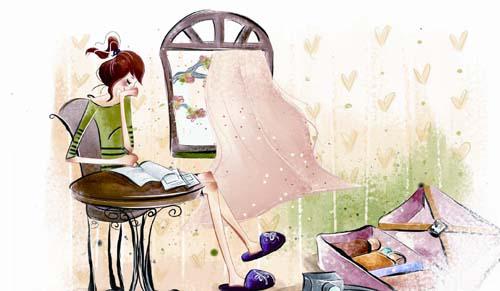
五年級下學期的某次月考,俞老師出了個作文題:《放學后》。我得的是“丙”。非但成績空前的差,在發還作文簿的時候,俞老師還特地用我的那篇當反面教材,聲色俱厲:“第一行跟第二行,意思差個十萬八千里,翻什么鬼筋斗啊?“我的第一行寫的是四個字、四個標點符號:“打啊!殺啊!”——這當然是指放學之后校車上最常聽見的打鬧聲。之后的第二行,另起一段,第一句如此寫道:“我是坐校車上下學的……”
俞老師搖晃著我的作文簿,接著再罵:“打啊殺啊跟你坐校車有什么關系?文從字順是什么意思你不懂嗎?上面一個字跟下面一個字可以沒關系嘛,上面一個詞跟下面一個詞也可以沒關系嘛,上面一句話跟下面一句話也可以沒關系嘛,上面一段文章和下面一段文章也可以沒關系嘛!”
從俞老師帳下,一直到高三,前后八年,教過我語文的還有六位老師,幾乎每位老師都當堂朗讀過我的作文。印象深刻的偏只有“載欣載奔”和《放學后》兩篇。
初中畢業前夕我帶著那本珍藏了五年的《好孩子生活周記》攔住了蘇尚耀老師,請他給簽個名。他從中山裝胸前的口袋里拔出老花鏡戴上,工整地簽下了名字。我問他:“為什么您說,寫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寫作文?”他沉吟了一會兒,才說:“作文是人家給你出題目;真正寫文章,是自己找題目,還不要找人家寫的題目。”我是在那一刻,感覺小學、中學一起畢了業。
(丁香清幽摘自《文章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