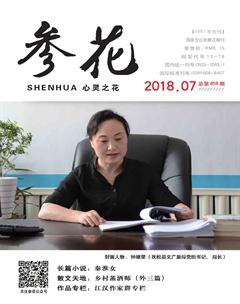從符號(hào)學(xué)的角度看表情包意義的表達(dá)和實(shí)現(xiàn)
摘要:現(xiàn)如今,表情包由于其生動(dòng)形象的表意方式,在大眾媒體的傳播中被廣泛使用。表情包往往通過(guò)明星頭像、影視截圖、動(dòng)漫等配上文字進(jìn)行加工,多以戲謔娛樂(lè)化的表達(dá)方式對(duì)熱門話題進(jìn)行二次傳播。隨著GIF、咔嘰等軟件的應(yīng)用,表情包開始走向原創(chuàng)和用戶生產(chǎn)的階段。從符號(hào)學(xué)的角度來(lái)看,表情包屬于“攜帶意義的感知”,可以被賦予特定的意義,其誕生的過(guò)程是新的符號(hào)文本創(chuàng)造的過(guò)程。
關(guān)鍵詞:符號(hào)學(xué)?表情包?表達(dá)和實(shí)現(xiàn)
一、從發(fā)送者角度而言的意圖意義——表情包是新媒體環(huán)境中的語(yǔ)言符號(hào)
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認(rèn)為媒介真正傳遞的是媒介的特性,傳播媒介本身就是傳播內(nèi)容。新媒體環(huán)境下的內(nèi)容則是更符合新媒體傳播特點(diǎn)、可視化的,并且可以傳遞情緒和感情的新的語(yǔ)言符號(hào),媒介的發(fā)展變化與表情包的發(fā)展特征不謀而合。
符號(hào)傳遞過(guò)程中的意圖意義必然離不開其誕生和發(fā)展的媒介環(huán)境。表情符號(hào)最開始誕生于美國(guó),1982年9月19日,美國(guó)卡耐基·梅隆大學(xué)的斯科特·法爾曼教授在電子公告板上第一次輸入了這樣一串ASCII字符“:-)”。從此,伴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和發(fā)展,網(wǎng)絡(luò)表情符號(hào)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使用。表情包的創(chuàng)造和發(fā)出必然賦予其一定的意義,和文字相比,表情包具有畫面感、網(wǎng)感、易理解傳播、互動(dòng)性強(qiáng)等特征,也被稱為“傳感器”,使人們能夠很好地表達(dá)和感知情緒。當(dāng)然,值得注意的一點(diǎn)是,表情包帶有強(qiáng)烈的草根性,最初的表現(xiàn)在于發(fā)出者的平民化。
二、表情包符號(hào)的文本意義——表情包是人的表情的延伸,以達(dá)到“在場(chǎng)”的效果
表情包來(lái)源于人們?cè)诂F(xiàn)實(shí)生活中約定俗成的對(duì)善惡美丑、喜怒哀樂(lè)的認(rèn)識(shí)與了解,其形式上看起來(lái)是只須調(diào)動(dòng)視覺感官的“熱媒介”,但是它戲謔化的表達(dá)特色使它又是一種“冷媒介”,需要加以豐富的聯(lián)想和再創(chuàng)造。因此,其含義既明確又含糊,既犀利又曖昧,是社會(huì)化媒體話語(yǔ)表達(dá)戲謔化發(fā)展趨勢(shì)的一種延伸,以達(dá)到看似在場(chǎng)的交流狀態(tài)。
在表情包里還存在另外一種“延伸”,那就是麥克盧漢認(rèn)為的“媒介是人體的延伸”,表情包就可以看做是人的表情的延伸。和我們面對(duì)面交流時(shí)非語(yǔ)言符號(hào)所起的作用一樣,在通過(guò)互聯(lián)網(wǎng)進(jìn)行交流時(shí),表情符號(hào)也有助于減少歧義、增強(qiáng)或緩和我們的情緒表達(dá)。也可以這么認(rèn)為,在大家廣泛使用社交媒體交流的今天,表情符號(hào)能幫助我們?cè)诜窒淼倪^(guò)程中,變得更為真誠(chéng)、更為自由。但是這種“真誠(chéng)和自由”僅僅是在網(wǎng)絡(luò)媒介上的表現(xiàn)。在網(wǎng)絡(luò)對(duì)話,特別是公共對(duì)話中,整個(gè)場(chǎng)域就是一個(gè)前臺(tái),由于聊天內(nèi)容可以被記錄,聊天的成員或者公共區(qū)域的其他人員都可以反復(fù)進(jìn)行查看,因此,用戶會(huì)精心地利用各種手段塑造自己的形象。除了表情符號(hào),微信中的用戶頭像、簽名、朋友圈內(nèi)容也具有說(shuō)明身份特征的功能,筆者將這種行為看成是“自我”為“在場(chǎng)”的形象進(jìn)行的管理。
三、從接受者角度而言的解釋意義——表情包的自由使用和意義解讀中的“認(rèn)知差”
在目前的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中,除了一些專業(yè)的設(shè)計(jì)師涉及的表情包需要支付費(fèi)用獲取以外,多數(shù)表情包都可以免費(fèi)獲取、自由使用,甚至可以自發(fā)生產(chǎn)和創(chuàng)造靜態(tài)或動(dòng)態(tài)的表情包,當(dāng)有限的表情包不足以表達(dá)某些特殊的情感或意圖時(shí),這種創(chuàng)造力會(huì)受到激發(fā)和催化。
傳播學(xué)理論認(rèn)為,意義交換的前提是傳受雙方有共通的意義空間,因?yàn)樯鐣?huì)的多樣性,社會(huì)成員的意義空間不可能完全相同,在符號(hào)傳遞的過(guò)程中也有類似的現(xiàn)象。解釋是符號(hào)意義最終實(shí)現(xiàn)的地方,但是由于年齡、地域、文化背景等因素,就會(huì)造成發(fā)送者本來(lái)的意義被接收者解釋為一種新的意義,也就是出現(xiàn)了符號(hào)傳遞中的“認(rèn)知差”。認(rèn)知差即自己對(duì)關(guān)于某事物的認(rèn)知不滿意,或是對(duì)另一個(gè)關(guān)于某事物的認(rèn)知不滿意,而認(rèn)為自己現(xiàn)在的理解可以對(duì)此進(jìn)行修正。
四、結(jié)語(yǔ)
表情包隨著媒介技術(shù)的發(fā)展被廣泛推廣,雖然其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低級(jí)趣味、過(guò)度惡搞、非理性的問(wèn)題,但是其存在的價(jià)值也是顯而易見的,從簡(jiǎn)單的表現(xiàn)情緒和表情逐漸發(fā)展到一種草根話語(yǔ)和去中心化傳播的構(gòu)建力量,從最初出現(xiàn)在人際交往中到影響大眾媒介去嚴(yán)肅化的表達(dá),其作為符號(hào)的積極意義都得以顯現(xiàn)出來(lái)。筆者從表情包傳遞過(guò)程分析了這種語(yǔ)言符號(hào)意義的表達(dá)和實(shí)現(xiàn),從發(fā)送者角度而言的意圖意義來(lái)看,表情包是新媒體環(huán)境中的語(yǔ)言符號(hào);就其文本意義進(jìn)行分析又可以看到對(duì)于表情的延伸和“在場(chǎng)”的效果;從接受者角度看到了表情包的自由使用和意義解讀中的“認(rèn)知差”。
(作者簡(jiǎn)介:郝越敏,女,成都體育學(xué)院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符號(hào)學(xué)角度的表情包)(責(zé)任編輯 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