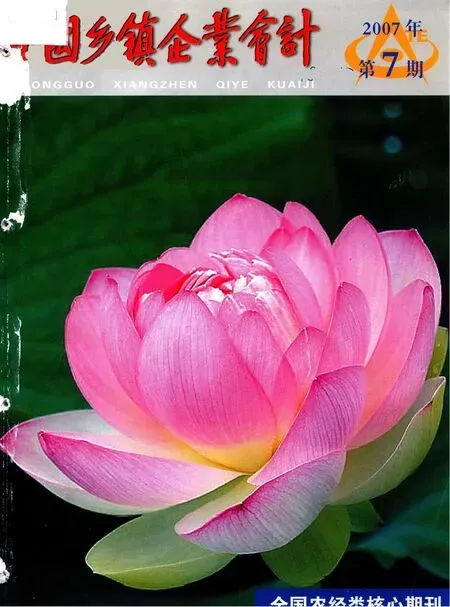財稅體制改革面臨的問題及解決措施
楊貴興
一、為什么要進行財稅體制改革
1.當前的財政稅收體制與經濟發展規律相矛盾
1994年我國從全局出發,為確定中央與地方的事務規劃以及明晰責任,進行了分稅制改革,初步將中央與地方事權以及各自應承擔的責任做出了規劃。要理順中央政府以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政關系,就要對中央和地方事權責任進行合理的劃分,合理劃分事權責任是理順這兩者關系的基礎和前提。但是由于事務劃分的不明確性,使得國家政策目標的推行艱難,影響到各項服務的均等化。更與當前經濟發展的規律相違背,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活力。因此,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中,對于加快中央與地方事權責任劃分的提案被重點討論,同時針對當前的現狀,明確地指出要建立與現代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事權責任制度,加強規范化的事權支出責任體系,推進各級政府明確責任,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2.市場經濟的發展對于當前財稅制度提出新的要求
我國當前需要的是全面規范、透明公平、協調開放的財稅制度,中央與地方事權與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建立市場經濟以來我國的發展有目共睹,國家生產總值連創新高,財政的收入也不斷增加,為我國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財政基礎。這一切成果的取得離不開我們的財稅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好發展離不開規范健全的財稅制度,但是當前的財稅制度不符合我們國家現代治理能力以及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要求,使我國的市場發展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影響到了社會公平。也不適應我國科學發展的要求。
3.要建立公正合理科學稅收結構的要求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黨和國家為加快財稅體制的改革,明確提出要落實“稅收法定原則”。2015年3月人大會議審議通過了立法修正案,為我國的稅制改革做出了明細化的準則。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我們在明細中央與地方事權責任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的基礎之上。按照國家規劃方略構建現代財政制度,在加快事權責任劃分的基礎之上,著力建設稅種科學、征收公平、開放透明的稅收征管體系。
二、我國當前財政收入的現狀
以2017年為例,各級政府部門在國家堅持穩中求進的的工作基調下,深入貫徹落實各項決議,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部署下,不斷改革發展方式加快轉變粗放落后的低效益的生產方式,堅持科學綠色發展的理念,在經濟穩中向好的前提下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全年國內累計的一般性公共預算收入為172566億元,比去年增長7.4%。地方為91448億元,同比增長7.7%。稅收與去年相比增長10.7%,國內增值稅56378億元,同比增長8%。其中,改征增值稅下降5.7%。企業所得稅32111億元,同比增長11.3%,個人所得稅11966億元,同比增長18.6%。
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03331億元,同比增長7.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支出29859億元,同比增長7.5%;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73471億元,同比增長7.7%。從主要支出科目情況看:教育支出30259億元,增長7.8%;科學技術支出7286億元,增長11%;節能環保支出5672億元,增長19.8%;城鄉社區支出21255億元,增長15.6%;債務付息支出6185億元,增長21.9%
在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隨著經濟總量的增加,我們的稅收收入也在增加,但其中有一點可以看到中央的稅收增幅開始減小,而以此同時地方稅收增幅較大。但是中央的稅收還是重頭戲,并且稅收以所得稅與增值稅為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個人以及企業的稅負還是很重,這是我們接下來需要著力改革的地方。
三、我國財稅體制改革所面臨的問題
1.中央與地方分稅制不明晰
首先,在我們原先的分稅制之下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責任劃分就一直處于十分模糊的狀態,這就造成了我們在事權劃分與財政相適合時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雖然對分稅制進行過改革但是兩者矛盾依舊突出,執行的過程中由于多種原因并不理想。其次,我們的財政收入預算等級還未達到規范化標準,國地稅的收、征、管不協調,嚴重弱化地方的稅收權利,地方稅收的空間不斷被壓縮。最后,立法工作的不完善,缺少相關法律的支持與規范使得我們在稅收的征管方面,缺乏有力制度保障,灰色地帶層出不窮。
2.財政稅收征管預算體系不完善
我們的預算體制存在以下幾個問題,首先,預算的覆蓋面小,很多的項目很多的方面都沒有納入預算體系,使得有些地方政府“花錢無度”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還使得財政入不敷出大肆“亂舉債”,其二,我們的預算體系不健全。我們對于政府資產活動缺乏有效的監督,預算體系不健全、預算編制無監督更使得許多政府的資金不透明,資金的分配去向不明晰,使政府在群眾中的權威性降低。我們在執行預算的時候,隨意更改預算方案,嚴重影響到預算的嚴謹性,規范性以及執行效果。同時各級政府自我為主,做出的預算與國家發展的總體方略相違背,科學性嚴重受到質疑。
3.稅制結構不合理
當前我國的稅制還是以營業稅為主,我們實施營改增的試點工作開展以來,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2018年我們的營改增全面推行。但是推行并不會一蹴而就,我們還有很多固有的通病需要解決,我們進入了改革的深水期。稅收種類不完善覆蓋范圍小并且局限于幾個方面,稅收小而窄的現狀長期難以改變。同時很多稅收制度對于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提高效率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尚未納入到稅種體制當中。稅制結構不合理性的突出影響就是使得各種主體稅之間的配合產生極大的阻礙,使得再分配這一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舉措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同時資源稅的計稅依據彈性不足。
4.轉移支付制度缺乏透明性
我們的轉移支付制度是促進我們再分配公平的重要舉措,但是我們現在在這一方面的制度建設還很不合理,設置科目過多過程繁瑣,與國際接軌困難。同時我們一般性的轉移支付規模小,中央與地方相比的差距很大,在我們的專項轉移支付中,不規范不合理的現象突出。基數法的分配方式,使得中央與地方專門支付的對接不合理。
四、財稅體制改革問題的解決措施
1.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破冰”
2016年8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首次系統的提出了事權責任劃分的方向——要求政府公共權力縱向配置以此來推動我們財稅體制的大變革方向,進一步明確了我們改革的目標、劃分的原則、改革的具體事項要求。要求我們在事權責任劃分的基礎之上,形成與此相配的財政體制,財稅體制改革邁入深水期并且有了實質性地指導方案。
2.架構預算管理總體框架,推進多項稅制改革
一個家庭對于收入與支出都會有一個小型的預算,更何況是一個繁榮前進的國家。做好我們的預算就是抓好了我們公共財政的基石,牽牛要牽牛鼻子,做事要抓住主要矛盾事情才會解決,因此要加快我們財稅制度的改革就要從做好預算開始,做好預算是我們深化財政體制改的重要內容。2016年的全國兩會中,讓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國家對于財稅體制改革的決心,國家預算賬本中的四大預算的亮相彰顯了黨中央、國務院對于政府財政資金的把控的嚴格性,只有我們財政資金管理越來越規范,我們才能緊緊地勒緊地方的大肆舉債不可控性風險的發生。我們通過了新的《預算法》,要求我們的政府在財政的收入、支出以及債務的發行都作出具體預算。讓政府資金在陽光下分配支出,預算的公開化法制化架構基本建立。
3.降費減稅是接下來的工作總基調
實體經濟是我們當前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是我們經濟發展的最基本的動力單位,但是從這些年來我們實體經濟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發展后勁不足。國家從綜合因素方面支出要振興我們的實體經濟,為此政府工作報告中不斷提出要為實體經濟降稅減負,負擔輕了發展的動力才足,振興的步伐才會更快。從2012年上海營改增工作試點開展以來,我們的營改增工作取得了重大的進展,開展營改增我們的企業稅負大幅降低,今年的中央決策將營改增全面推展,并且將17%的稅率降到16%,這都體現了我們國家深化稅制改革的決心,助推是團體經濟發展的決心。在個稅的改革上,我們則更加注重稅收的公平性,從各個家庭的實際出發,從家庭的負擔出發,如何減輕家庭不必要的稅負從而提振消費的欲望成為個稅改革的重要方向。
4.加強制度保護,提升轉移支付透明度
首先明確我們在財稅體制改革中要抓住的重點,我們要建立完善的分級財政體制,并以此為我們改革的基點,改革中的頑疾必須徹底革新,同時為防止其再出現我們的立法工作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以法律基礎對財政的支出,稅收都做出詳細的規范積極的探索。我們要充分發揮轉移支付對于貧困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強專項資金的轉移支付。為我們的脫貧攻堅戰建立起完善的財稅制度,為我們的全面小康目標打下堅實的財政稅收基礎,使我們的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
五、結語
財稅體制改革是關乎我們如何以更加完善的上層建筑更好服務于國家發展、服務社會民生的深刻變革。不去改革就會發生革命,改革才是我們正確的道路,現在的改革階段正值深水期,其中的難度與風險不言而喻。但是我們不能停止改革的腳步,近些年來我們的發展有目共睹,暴露的問題也不少。當前制約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上層建筑正在逐步改革,我們當前的財稅制度也是如此,只有改革才能使我們的上層建筑更加適合我們的經濟基礎,才能更好的推動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我們只有更好的改革我們當前不合理的不適合經濟發展的制度才能更好的優化資源配置,才能更好的改變我們現在發展的尷尬境地,才能更好的助推中國夢的實現,讓我們的人民擁有更多的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