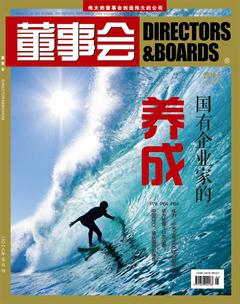公正執法,呵護企業家人身權、財產權
薛峰 羅培新
中共中央、國務院多次發文,明確要求為企業家營造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而其中,“親”“清”政商關系的構建,至為關鍵。正確把握“親”“清”二字,需要政商恪守法治底線、誠信原則、公正標尺和雙贏目標,既要矯正勾肩搭背、過從甚密的官商不分,又要防止談商色變、為官不為的過猶不及,做到有交集不搞交換、有交往不搞交易,攜手共建交往有道、公私分明,廉潔互信、相敬如賓,各盡其責、共謀發展。而所有的這一切,均要以法治的方式來引領和保障。
讓企業家安放自身
企業家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只有安放自身才能兼濟天下。基于過往實踐,特別是借鑒《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的實施意見》的規定,在這方面,必須牢牢把握以下數點:
其一,嚴格執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釋,堅決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嚴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認定標準,嚴格區分正當融資與非法集資、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兼并重組中涉及的經濟糾紛與惡意侵占國有資產等的界限。對于各類經濟糾紛,特別是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的糾紛,要堅持依法辦案,公正審判,堅決防止把經濟糾紛認定為刑事犯罪。此點至為關鍵,因為一旦冤枉入罪獲刑,辛苦數十年打拼的基業,就有可能毀于一旦。人生不可逆,猶如開弓已無回頭箭。冤假錯案,傷害的不僅是當事人,而且是創造財富的熱情與信心。
其二,堅持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從舊兼從輕、疑罪從無原則。嚴格犯罪構成要件,禁止類推解釋,對定罪依據不充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依法宣告無罪。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特別是非公有制企業經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不規范問題,對雖屬違法違規、但不構成犯罪的,應當宣告無罪;對于法律界限不明、罪與非罪不清的,應當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對企業家在生產、經營、融資活動中的創新創業行為,只要不違反刑事法律的規定,不得以犯罪論處。此點同樣非常重要,疑罪從無,從輕處斷,對于企業家的財富創造激勵,善之大者,莫復如是!
其三,嚴格非法經營罪、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防止隨意擴大適用。慎重把握非法經營罪中“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要件,防止隨意擴大適用該要件。對于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產生的民事爭議,如無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符合犯罪構成的,不得作為刑事案件處理。
第四,依法懲治侵犯企業和企業家權益的各類刑事犯罪。嚴厲打擊黑惡勢力尋釁滋事等危害企業家人身安全刑事犯罪;堅決打擊在企業發展、市場競爭中的村霸、行霸、市霸等犯罪活動,為企業家正常經營提供良好的治安環境;嚴懲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向企業索賄、受賄以及市場管理中的失職瀆職等犯罪行為。
第五,依法慎用強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凍結措施,依法適用非監禁刑,最大限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可能造成的不當影響。對確已構成犯罪的企業家,應當綜合考慮行為性質、危害程度等決定適用強制措施的種類。對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應當變更強制措施;對被依法羈押的被告人,依法保障其正常行使企業經營管理權等權利。對犯罪情節輕微的企業家,符合非監禁刑適用條件的,應當盡量適用非監禁刑。確需采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要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為企業預留必要的流動資金和往來賬戶。不得查封、扣押、凍結與案件無關的財產。嚴格依法采取財產保全、行為保全等強制措施,防止當事人惡意利用保全手段,侵害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對于因錯誤實施保全等強制措施,致使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案外人等財產權利受到侵害的,應當及時解除或變更強制措施。
其六,嚴格區分企業家違法所得和合法財產,沒有充分證據證明為違法所得的,不得判決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嚴格區分企業家個人財產和企業法人財產,在處理企業犯罪時不得牽連企業家個人合法財產和家庭成員財產;在處理企業家個人犯罪時,要避免隨意牽連處置企業法人財產和家庭成員財產。按照公開公正和規范高效的要求,嚴格執行、不斷完善涉案財物保管、鑒定、估價、拍賣、變賣制度,對非法占有、處置、毀壞財產的,不論是公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均應當及時追繳,或者責令退賠,依法維護企業和企業家的合法權益。
政府須帶頭守法守信
構建法治化的政商關系,對政府而言,除了法無規定不可為之外,特別重要的一點是,構建誠信政府,做到有令必行,有諾必踐。
政務誠信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對于社會主體之間的橫向信用關系而言,政務誠信記載的是政府行為作用于行政相對人的縱向信用關系。各級政務主體的誠信水平,對其他主體的誠信建設發揮著重要的表率和引領作用。說得通俗一點,要讓老百姓守法守信,政府自己必須帶頭守法守信,特別是,不能新官不理舊賬。對于政府與企業簽訂的合同,如果政府違約,法院應當依法判決政府承擔違約責任。政府拒不執行生效裁決,企業自然是第一受損人,但最終為此埋單的還是政府的公信力,是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擁護和支持。為維護政府公信力,需要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強政務誠信建設的指導意見》的要求,對現行政績考核機制進一步優化,將“政務誠信”納入政績考核中,對政府機關的合同履約率實行考核,增強政府人員的誠信意識,消除地方政府的失信積弊。
法院在審理政府作為一方的合同紛爭時,不能偏倚裁判,而要依法審理,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要依法妥善認定政府與企業簽訂的行政協議效力,依法公正審理行政允諾案件。對因招商引資、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等活動引發的糾紛,要切實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依法監督行政機關履行對企業的各項合法承諾。這對于時下普遍推行的PPP尤具意義。
另外,對于確因政府規劃調整、政策變化導致行政協議不能履行,政府解除行政協議的,依法予以支持;對于企業請求返還已經支付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投資款、租金或者承擔損失補償責任的,依法予以支持。依法審慎處理好企業改制相關糾紛,既要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也要防止超越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不當損害民營企業的正當權利。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法院要合理把握征收征用適用的公共利益范圍,堅決防止公共利益擴大化。遵循及時合理補償原則,對土地征收和房屋拆遷補償標準明顯偏低的,要綜合運用多種方式進行公平合理的補償,借助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妥善處理涉企業家財產征收征用案件。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以法治方式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呵護的不僅是企業家群體,更是呵護社會進步之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