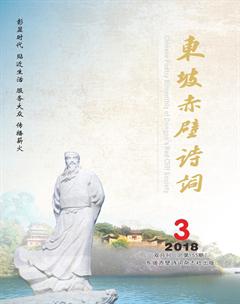路過田園
姚泉名
很多田園詩的研創者認為,要想寫好田園詩,作者要熱愛農村、了解農業、參與農事。言下之意,似乎不做到這幾樣,就不能寫田園詩;就算寫了,也只是旁觀者的吟哦,不是真正的田園詩。個人對此稍有不同看法——田園,不能屬于路過者嗎?
拉開距離,發現田園之美。
美學界有個著名的命題:距離產生美。是說在審美過程中,應該與客體保持適當的距離,否則會影響和削弱審美主體的審美效果。這個距離可以是時間的,也可以是空間的,還可以是心理的。我雖然在農村生活過很多年,但事實上對農村并沒有多少深入的了解,所以手癢了寫田園詩時,只能采取旁觀的姿態,路過的姿態,最多也就是以低烈度參與的姿態:停下腳步,親手采摘。也許我沒有深刻地揭示田園的苦,但是,何妨拉開距離去發現田園的美?正是在這樣的考量之下,我經常會寫“不是真正的田園詩”,去將自己在旅途中發現的田園之美記錄下來。如《癸巳梁子湖藍莓節·采藍莓》:“共拈嘉果野園間,齒惹甜香帶紫斑。張遠村頭忘歸處,寒煙藏竹雨藏山。”這是低烈度參與者的姿態;如《農事》:“花飛花落無心感,犁柄輕扶牛索攬。新耕泥浪水田開,一鞭驚破黃鸝膽。”這是旁觀者的姿態;如《陽新道中》:“看山始到縣之涯,一路輕車似逐蛇。激激溪鳴前夜雨,融融樹綴晚春花。眼前不斷峰遮日,嶺上忽停云覆紗。牽犢田翁含笑指,村名姜福是吾家。”這是路過者的姿態。是的,我沒有“濃墨重彩”地去勾畫農村的新變化,諸如電腦賣菜,書作嫁妝的事,都沒寫,最露骨的也只是“村名姜福是吾家”。但我筆下這些安詳寧靜的田園景象,折射出的不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嗎?
保持童心,發掘田園之趣。
我只是一個田園的路過者,是一個被工作被生活壓彎了腰的生命過客,田園是我的一個夢,是另一種生活的憧憬。我不但陶醉于田園之美,還會留心于田園之趣。有趣,是我對詩的一種追求。古人對于“趣”有很多闡述,我最引為會心的是明代李贄倡導的“童心說”,他重視真情表達,把“趣”作為真情和童心的顯現,他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又在點評《水滸傳》時說:“天下文章當以趣為第一。”他認為,天下至文來自“童心”,而又以“趣”為第一,可見“童心”與“趣”對于詩文的重要性。詩來源于生活,生活中的“趣”,要靠童心去發現,詩人如果沒有一顆童心,其詩作也自當少“趣”。我在創作田園詩時,也是盡量以童心覓趣。如《鶴慶道中》:“路入重巒似蟒纏,幾家村寨半山懸。玉皇不是癮君子,煙草因何種上天?”云南鶴慶一帶山區多梯田,田中多種煙草。這是當地農民致富的手段。旅途中發現這個特點后,我故意以兒童的視角發問,“傻乎乎”地寫出了當地農業的特色。如《西江月·消泗油菜節》的上闋:“大野刷層金漆,長空灑點香精。蜂兒不肯繞桃櫻,都趕菜花歡慶。”以一幅色彩斑斕的兒童漫畫,表現消泗萬畝油菜花的壯觀場景。
不吝關懷,溫暖田園之心。
我的路過者的角色定位,使自己對于田園生活的描繪只能是浮光掠影。但是,這并不表示我對于田園沒有感情,并不表示我對于偏遠農村的貧窮視而不見。九年前,我曾獨自到大冶的金竹尖山采風,原本是賞景,最后卻被山頂上一個名為毛百市的貧困山村所震撼,寫下一首七言古風《毛百市村》。先寫自己歷盡艱辛到達這個偏遠的山村,“……一峰轉過千峰起,巖峽深處無人跡。油門漸松坡漸緩,曲徑拉我到山脊”;再寫自己所見,“……籬外呼人無聲應,鎖銹窗破土灰積。野鳥飛過殘垣靜,似逃兇年避疾疫。更行行到路絕處,小村屋亂秋田瘠”;然后,寫所遇農婦對我講述該村的歷史:由于自古交通不便,村里的青壯年都下山謀生路,山上留守的盡是老弱病殘,“村有耄耋老夫妻,兒孫不歸近十年。翁眼獨明嫗打柴,落崖斷腿破床眠”;最后寫政府對該村的筑路扶貧之舉,“幸得甘霖政府來,一年筑路斥資巨。高山經濟可富民,云間畢竟神仙處。……金竹尖山肯入夢,他年再將新景敘”。對于這樣的田園,詩人自當以詩歌來表達同情,為之鼓呼,給予溫暖,給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