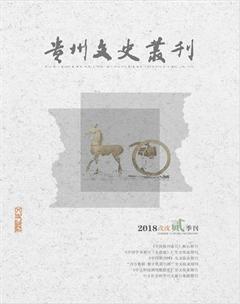啟蒙立場(chǎng)與場(chǎng)域越界
劉楚
摘 要:在藝術(shù)社會(huì)學(xué)視域下,可以發(fā)現(xiàn),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是一個(gè)具有強(qiáng)烈社會(huì)政治指向性的理論命題。在文化場(chǎng)域,蔡元培從啟蒙主義的精神立場(chǎng)出發(fā),通過考察佛教與中國文學(xué)藝術(shù),以及基督教與歐洲文學(xué)藝術(shù)的演變,倡導(dǎo)以純粹之美育取代宗教中的美育原素。但將美學(xué)場(chǎng)域內(nèi)部的理論命題“以純粹之美育取代宗教中的美育原素”極度簡(jiǎn)化為涉及不同的場(chǎng)域“以美育代宗教”命題,這其實(shí)違背了現(xiàn)代性工程的場(chǎng)域倫理,并最終產(chǎn)生了場(chǎng)域越界問題。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一出,林風(fēng)眠、陳獨(dú)秀、梁漱溟等人“以xx(藝術(shù)、科學(xué)、禮樂等)代宗教”的說法隨之而至。事實(shí)上,他們的話語方式不自覺地陷入到蔡元培設(shè)定的“敘述圈套”。
關(guān)鍵詞: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 啟蒙立場(chǎng) 場(chǎng)域倫理
中圖分類號(hào):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0-8705(2018)02-82-87
蔡元培作為中國現(xiàn)代美學(xué)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命題是其美學(xu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語境的及時(shí)發(fā)聲和重要回應(yīng),并對(duì)中國美學(xué)場(chǎng)域、宗教場(chǎng)域乃至是當(dāng)時(shí)的權(quán)力場(chǎng)域產(chǎn)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對(duì)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命題的發(fā)生、內(nèi)核和反響進(jìn)行藝術(shù)社會(huì)學(xué)的考察,從而領(lǐng)會(huì)到蔡元培這一命題所表現(xiàn)出的啟蒙精神,以及在其中產(chǎn)生的場(chǎng)域越界問題。
一、社會(huì)語境:權(quán)力場(chǎng)作用下的文化場(chǎng)
中華民國成立后,臨時(shí)中央政府頒布的《臨時(shí)約法》肯定了公民集會(huì)、結(jié)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在宗教領(lǐng)域也認(rèn)可了公民自由信教的權(quán)利,受此鼓舞,人們的思想逐漸解總體化,自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的思想政策起,在帝制時(shí)代的中國儒家思想一家獨(dú)大、獨(dú)享正統(tǒng)的思想格局被打破,而呈現(xiàn)出思想爭(zhēng)鳴、多元并置的局面。
在《臨時(shí)約法》頒布的這一年,中國孔教會(huì)隨即在文化保守主義者1康有為的組織、倡導(dǎo)下成立,并在各地開設(shè)分會(huì),提出“尊崇孔圣”的口號(hào),企圖將儒教宗教化,并上升為國教2;與此相呼應(yīng),袁世凱當(dāng)政時(shí)期,他提出“尊孔復(fù)古”的政策,他的一些御用文人驅(qū)策康有為等文化保守主義者導(dǎo)夫先路,企圖通過將儒教立為國教,以重新樹立儒教的官方意識(shí)形態(tài)地位。而隨著袁世凱復(fù)辟的失敗,國會(huì)1916年進(jìn)行的投票否決了立孔教為國教的提案。與康有為等人想把本土的儒學(xué)宗教化相對(duì)照,在當(dāng)時(shí)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浪潮中,一些人認(rèn)為宗教對(duì)西方道德、社會(huì)和文化的進(jìn)步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還把中國國衰民弱的緣由歸結(jié)為宗教的缺失,因而試圖將基督教普及到中國大眾中去,這就是蔡元培所說的,當(dāng)時(shí)有人把西方的發(fā)展、進(jìn)步“一切歸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勸導(dǎo)國人”1。此外,還有人在上海成立組織“靈學(xué)會(huì)”,出版有《靈學(xué)叢志》,公然宣揚(yáng)“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的思想。
面對(duì)價(jià)值重估時(shí)期權(quán)力場(chǎng)作用下的文化場(chǎng)所表現(xiàn)出的思想多元、混亂和迷茫局面,柳詒徵曾有感而發(fā):“蓋國事不寧,社會(huì)紊亂,國外之宗教,既挾其國力與其文化,乘我之隙而得我之民心。而迷信中國舊日之神教者,亦竊其法,欲假宗教之力,以弭人心之不安,是皆時(shí)勢(shì)之所造成也。”2以文化場(chǎng)域?yàn)橹行模?dāng)時(shí)的中國思想界各派人士開展了符號(hào)資本、符號(hào)權(quán)力、文化領(lǐng)導(dǎo)權(quán)爭(zhēng)奪的激烈混戰(zhàn)。支持袁世凱的御用文人試圖為其復(fù)辟造勢(shì),利用“尊孔復(fù)古”在思想上造成一元化的集權(quán)統(tǒng)治形態(tài);持文化保守主義立場(chǎng)的康有為力推把本土的孔教立為國教,而持西化立場(chǎng)的其他人則試圖向社會(huì)推廣基督教,這些都可視為文化場(chǎng)試圖利用輿論、話語的方式影響權(quán)力場(chǎng)。正如哈貝馬斯所說:“話語并不具有統(tǒng)治功能。話語產(chǎn)生一種交往權(quán)力,并不取代管理權(quán)力,只是對(duì)其施加影響。影響局限于創(chuàng)造和取締合法性。交往權(quán)力不能取締公共官僚體系的獨(dú)特性,而是‘以圍攻的方式對(duì)其施加影響。”3針對(duì)這種情況,持啟蒙意識(shí)形態(tài)立場(chǎng)的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健將們自然不能等閑視之。他們圍繞宗教的議題,以話語為手段,試圖以市民社會(huì)的啟蒙意識(shí)形態(tài)與專制主義的國家意識(shí)形態(tài)進(jìn)行博弈和對(duì)抗,以輿論圍攻的方式影響權(quán)力場(chǎng),對(duì)袁世凱“尊孔復(fù)古”的政策表達(dá)抗議。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健將看來,美學(xué)就是這樣一種代表市民社會(huì)啟蒙意識(shí)形態(tài)的話語,它既可以用來影響、撬動(dòng)政治場(chǎng)和權(quán)力場(chǎng),又可以用來積累、爭(zhēng)奪文化場(chǎng)上的文化資本和符號(hào)資本。1917年初,有人寫信給高舉“民主”與“科學(xué)”大旗的《新青年》主編陳獨(dú)秀,提議請(qǐng)蔡元培出山闡明“以美學(xué)代宗教之偉論”4,以造福青年人。應(yīng)陳獨(dú)秀的請(qǐng)求,蔡元培 1917年在北京神州學(xué)會(huì)發(fā)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說》的演講,演講稿還刊登在《新青年》第3卷第6號(hào)上。
二、思想淵源:?jiǎn)⒚芍髁x的精神立場(chǎng)
事實(shí)上,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并非單純的“聽將令”,而是有跡可循、淵源有自,可以說不但與其以前的思想一脈相承,而且與他一貫的向社會(huì)大眾推廣美育的初衷一脈相承。而以美育為批判的話語和武器,介入文化場(chǎng)域宗教性議題的討論,也的確可以收到為美學(xué)積累合法化資本,播散其社會(huì)影響力之功效。
中文語境下的“教”字,大概有教化、宗教和思想體系(真理)三種意思5,宗教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一直不占主流位置。在出國留學(xué)前,蔡元培在《佛教救國論》中開宗明義地提出過國不可無教,教須以護(hù)國為宗旨的觀點(diǎn)。在述及中國“教”的起源時(shí),他說:“我國之教,始于契,及孔子而始有教士。”在文化的童蒙時(shí)期,中國文化本有孕育發(fā)展出宗教的可能性,但由于“孔子深循體合之義,乃危行遜言,取舊教之粗跡,略見真理端倪,以告于人人”6,最終,中國文化對(duì)“教”的基調(diào)在軸心期便已奠定:“教”離“宗教”而遠(yuǎn)去,而親近“教化”和“思想體系”(“真理”)之義。由于對(duì)“真理”的堅(jiān)守,實(shí)際上,他對(duì)其視為“非真理”“極無理”1的基督教并無好感。并且,他還認(rèn)為基督教曾以強(qiáng)力侵入印度,占據(jù)以溫和、圓融為表征的佛教的地盤,如今又企圖挾西方之威勢(shì)侵入中國。因此,他對(duì)基督教一直保持有極強(qiáng)的警惕性和戒備心。
受中國文化的浸潤和本人思想的驅(qū)導(dǎo),蔡元培在上述對(duì)“教”的使用上,一直淡化“宗教”義,而凸顯“教化”和“思想體系”義。李澤厚在論及康德的啟蒙思想時(shí),曾提出康德思想的發(fā)育成熟受盧梭的影響甚大的觀點(diǎn):“正是盧梭,使康德看到對(duì)人本身尊嚴(yán)和權(quán)利的信念便可以成為新的形而上學(xué)的根基,而無需神學(xué)和宗教,因?yàn)槿吮旧肀闶悄康摹!?事實(shí)上,康德哲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轉(zhuǎn)向正在于,哲學(xué)由注重神學(xué)和宗教等外在超驗(yàn)事物,轉(zhuǎn)向以人自身作為研究對(duì)象和目的。出國留學(xué)后,他直接受康德等哲學(xué)家的啟蒙思想的啟發(fā),更是對(duì)超驗(yàn)的宗教保持了敬而遠(yuǎn)之的態(tài)度。
基于以上分析,可見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先行結(jié)構(gòu)和后來所受的西方現(xiàn)代啟蒙思想的影響,宗教在蔡元培心目中占據(jù)的位置一直不高。“以美育代宗教”的提法雖然是蔡元培在1917年的演講《以美育代宗教說》中提出的,但在此之前,他的這種思想已見雛形。這也是有人寫信給陳獨(dú)秀邀請(qǐng)蔡先生發(fā)表“以美育代宗教之偉論”的緣由所在。在《對(duì)于新教育之意見》中,蔡元培認(rèn)為,政治追求現(xiàn)世的幸福,宗教超脫于現(xiàn)世的幸福,無論是政治還是宗教,都局限于一端而不能囊括人類精神之全部。實(shí)際上,他認(rèn)為人類生存于現(xiàn)世,既不應(yīng)放棄現(xiàn)世幸福,也不應(yīng)放棄對(duì)現(xiàn)世幸福之外的超越價(jià)值的向往。因而,政治和宗教兩者都不能完成連結(jié)“現(xiàn)象世界”和“本體世界”的任務(wù)。要實(shí)現(xiàn)這種連結(jié),他認(rèn)為非世界觀教育和美育莫屬。由于單純的世界觀過于空泛和枯燥,所以他更看重以感性著稱的美育。通過這樣的論證,他就完成了對(duì)宗教的排斥。而且,他認(rèn)為滿清時(shí)代提倡的與共和精神不合的“忠君”,與信教自由相違的“尊孔”,都是專制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的表征。袁世凱“尊孔復(fù)古”,實(shí)際上就是試圖恢復(fù)專制主義的意識(shí)形態(tài),為其復(fù)辟稱帝的野心做思想輿論準(zhǔn)備,這是蔡元培所不愿看到的。有鑒于此,在中國具體的社會(huì)政治語境中,持啟蒙主義精神立場(chǎng)的蔡元培自然會(huì)一如既往地反對(duì)各種具體的宗教,不管這種宗教是來自中國還是來自西方。因?yàn)樵谒磥恚F(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宗教大多是與現(xiàn)代理性精神相悖,誘導(dǎo)人盲從的制度化宗教:“現(xiàn)今各種宗教,都是拘泥著陳腐主義,用詭誕的儀式,夸張的宣傳,引起無知識(shí)人的盲從的信仰,來維持傳教人的生活.這完全是外力侵入個(gè)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權(quán)的。”3
對(duì)于宗教的現(xiàn)代性改造,在宗教內(nèi)部,他倡導(dǎo)拋卻其制度化的弊病,而保持純正的“信仰心”。蔡元培在《我的人生觀》中寫道:“在法,與李、汪諸君初擬出《民德報(bào)》,后又?jǐn)M出《學(xué)風(fēng)雜志》,均不果。其時(shí)編《哲學(xué)大綱》一冊(cè),多采取德國哲學(xué)家之言,惟于宗教思想一節(jié),謂‘真正之宗教,不過信仰心。所信仰之對(duì)象,隨哲學(xué)之進(jìn)化而改蠻.亦即因各人哲學(xué)觀念之程度而不同。早謂信仰自由。凡現(xiàn)存有儀式有信條之宗教,將來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創(chuàng)之說也。”4在宗教外部,他引入美育,倡導(dǎo)“以美育代宗教”。在1915年1月發(fā)表的《哲學(xué)大綱》中,他就提出“以文學(xué)美術(shù)之涵養(yǎng),代舊教之祈禱,其諸將來宗教之疇范與”5,“宗教為野蠻民族所有,今日科學(xué)發(fā)達(dá),宗教亦無所施其技,而美術(shù)實(shí)可代宗教”6。在此,他是用進(jìn)化論論證說明美術(shù)代宗教的必然性,其中含有野蠻與文明、新與舊的二元對(duì)立式,在這樣的話語運(yùn)作下,話語的等級(jí)秩序油然而生。1916年8月10日發(fā)表的《賴斐爾》在介紹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畫家賴斐爾的畫作時(shí),蔡元培也是運(yùn)用這樣的話語運(yùn)作策略,他說:“教力既窮,則以美術(shù)代之。觀于賴斐爾之作,豈不信哉!”1
三、闡釋策略:祛魅和話語秩序
經(jīng)過長(zhǎng)期的思想醞釀和發(fā)展,1917年在北京神州學(xué)會(huì)發(fā)表的演講中,蔡元培正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題。此后,他又對(duì)這個(gè)命題進(jìn)行了多次的補(bǔ)充和發(fā)揮。2本來他還想以“美育代宗教”為題寫一部專著,遺憾的是他未能完成,從他留下的提綱可見他一直堅(jiān)持“美育代宗教”的思想。究其實(shí)質(zhì),“美育代宗教”其實(shí)是“政治文化論爭(zhēng)性的講辭”3,蔡元培采用的是現(xiàn)代性思想對(duì)宗教進(jìn)行批判。下面,讓我們分析蔡元培運(yùn)用話語闡釋“以美育代宗教”命題的具體策略。
蔡元培話語運(yùn)作策略的第一個(gè)關(guān)鍵詞是“祛魅”。“祛魅”是指宗教對(duì)世界神秘的、總體化的統(tǒng)治與解釋的解體。“祛魅”的過程其實(shí)就是西方國家開始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的過程,即從宗教占據(jù)意識(shí)形態(tài)崇高客體的社會(huì)向世俗化、理性化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社會(huì)生活的各個(gè)領(lǐng)域由宗教包辦向分立自治轉(zhuǎn)型,價(jià)值領(lǐng)域由宗教權(quán)威的一元論向各領(lǐng)域價(jià)值分立轉(zhuǎn)型。蔡元培便講述了人類社會(huì)“祛魅”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歷程。最初,人的心理-精神結(jié)構(gòu)的三要素——“知”“情”“意”都隸屬于宗教。人們對(duì)于宇宙人生的疑問由宗教予以解答,由于欲望而生發(fā)的利己之心由宗教予以勸導(dǎo),由于人們皆有愛美之心,于是宗教便利用美術(shù)來誘人信仰,以上三個(gè)方面便是知識(shí)、意志和情感隸屬于宗教的表現(xiàn)。“知”“情”“意”追求的最高價(jià)值“真”“美”“善”,在這一歷史時(shí)期也都未分化、獨(dú)立,而附屬于總體性的“善”;各門學(xué)術(shù)也都沒有獲得獨(dú)立的價(jià)值,必須服從宗教的需要,因而,神學(xué)在這一階段的學(xué)術(shù)中占據(jù)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蔡元培以現(xiàn)代性的進(jìn)步敘事為依托,稱之為“未開化時(shí)代”。隨著人類的進(jìn)步,科學(xué)的發(fā)達(dá), 知識(shí)與意志逐步脫離宗教并獨(dú)立發(fā)展,成為價(jià)值獨(dú)立的社會(huì)領(lǐng)域——科學(xué)和道德。而情感領(lǐng)域的獨(dú)立相對(duì)于知識(shí)和意志領(lǐng)域則要緩慢一些,宗教仍然利用美術(shù)在情感領(lǐng)域?qū)θ藗兪┘佑绊憽N乃噺?fù)興之后, 美術(shù)在進(jìn)化中也逐漸脫離宗教。自此,蔡元培區(qū)分了兩種不同的美育,一為“純粹之美育”,一為“宗教中的美育原素”,他提倡前者而批判后者,原因有二:其一,“宗教中的美育原素”有激刺人的感情以達(dá)宣揚(yáng)本教、攻擊異教之弊,而喪失陶冶性情的初衷,而“純粹之美育”由于美的普遍性,因此能破除人我之間的差別,而最終達(dá)到陶養(yǎng)性情的目的。其二,“宗教中的美育原素”誘導(dǎo)人脫離現(xiàn)象世界以求本體世界,而“純粹之美育”則能溝通現(xiàn)象世界和本體世界,搭建起跨越二者鴻溝的津梁。由此可見,準(zhǔn)確地說,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說,其要義實(shí)際上是“以純粹之美育取代宗教中的美育原素”。
蔡元培話語運(yùn)作策略的第二個(gè)關(guān)鍵詞是“話語秩序”。福柯說:“在任何社會(huì)里,話語在其產(chǎn)生的同時(shí),就會(huì)依照一定數(shù)目的程序而被控制、選擇、組織和再分配……”4蔡元培依托于現(xiàn)代性的進(jìn)步話語,擅長(zhǎng)于選擇、組織和運(yùn)用一些二元對(duì)立項(xiàng),在構(gòu)成二元對(duì)立項(xiàng)的具體話語中,總是張揚(yáng)、肯定一種話語,貶低、否定另一種話語,因而,這種話語策略其實(shí)是在制造一種厚此薄彼、揚(yáng)此抑彼的等級(jí)秩序。在《以美育代宗教說》中,蔡元培以進(jìn)化論闡釋文學(xué)藝術(shù)和美學(xué)的演變史,提出“美術(shù)之進(jìn)化史,實(shí)亦有脫離宗教之趨勢(shì)”的論點(diǎn),緊接著,以中西方的文學(xué)藝術(shù)和美學(xué)與宗教的關(guān)系分別舉例論證。中國的文藝、美學(xué)與佛教的關(guān)系為:“吾國南北朝著名之建筑,則伽藍(lán)耳。其周雕刻,則造像耳。圖畫,則佛像及地獄變相之屬為多。文學(xué)之一部分,亦與佛教為緣。而唐以后詩文,遂多以風(fēng)景人情世事為對(duì)象。宋元以后之圖畫,多寫山水花鳥等自然之美。周以前之鼎彝,皆用諸祭祀。漢唐之吉金,宋元以來之名瓷,則專供把玩。野蠻時(shí)代之跳舞,專以娛神,而今則以之自娛。”1歐洲的文藝、美學(xué)與佛教的關(guān)系為:“歐洲中古時(shí)代留遺之建筑,其最著者率為教堂。其雕刻圖畫之資料,多取諸新舊約。其音樂,則附麗于贊美歌。其演劇,亦排演耶穌故事,與我國舊劇‘目蓮救母相類。及文藝復(fù)興以后,各種美術(shù)漸離宗教而尚人文。至于今日,宏麗之建筑多為學(xué)校、劇院、博物院。而新設(shè)之教堂,有美學(xué)上價(jià)值者,幾無可指數(shù)。其他美術(shù),亦多取資于自然現(xiàn)象及社會(huì)狀態(tài)。”2在蔡元培看來,中西方的文藝和美學(xué)發(fā)展的特點(diǎn)為,逐漸脫離宗教的影響而獨(dú)立。然后,他又闡述“美育之附麗于宗教者”與“純粹之美育”在功能方面高低等級(jí)上的區(qū)別和差異:
于是以美育論,已與宗教分合之兩派。以此兩派相較,美育之附麗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養(yǎng)之作用,而轉(zhuǎn)以激刺感情。蓋無論何等宗教,無不有擴(kuò)張己教、攻擊異教者殺之。基督教與回教沖突,而有十字軍之戰(zhàn),幾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舊教之戰(zhàn),亦亙數(shù)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圓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學(xué)佛者茍牽教義之成見,則崇拜舍利受持經(jīng)懺之陋習(xí),雖通人亦肯為之。甚至為護(hù)法起見,不惜于共和時(shí)代,附和帝制。宗教之為累,一至于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為之地。鑒激刺感情之弊,而專尚陶養(yǎng)感情之術(shù),則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yǎng)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xí)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蓋以美為普遍性,決無人我差別之見能參入其中。……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復(fù)有人我之關(guān)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關(guān)系。3
蔡元培在上面這段話中評(píng)述了人類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他認(rèn)為宗教都具有張揚(yáng)己教、攻擊異教的弊病。在這個(gè)對(duì)宗教進(jìn)行否定的總前提下,他提出三大宗教又有相對(duì)圓融平和與激烈極端的區(qū)別。他認(rèn)為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相比,佛教的教義和思想相對(duì)圓融平和的特征。但即便如此,佛教徒也無法避免宗教組織化和制度化之后的激刺感情之累。他在對(duì)“美育之附麗于宗教者”與“純粹之美育”這個(gè)總的二元對(duì)立項(xiàng)進(jìn)行具體比較時(shí),又運(yùn)用現(xiàn)代性的分解式理性,將二者并置,但蘊(yùn)含有高低、褒貶的話語等級(jí)秩序和價(jià)值判斷。“美育之附麗于宗教者”與“純粹之美育”,他認(rèn)為前者是自由的,而后者是強(qiáng)制的;前者是進(jìn)步的,而后者是保守的;前者是普及的,而后者是有界的。
四、議題反響: 敘述圈套與場(chǎng)域越界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一出,隨即在文化場(chǎng)引起強(qiáng)烈反響和熱議,同意者有之,批駁者亦有之。陳獨(dú)秀認(rèn)為“在習(xí)于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蔡元培具有難能可貴的“容納異己的雅量, 尊重學(xué)術(shù)思想自由的卓見”4。我們當(dāng)然不懷疑蔡元培所具有的容納異己的雅量及尊重學(xué)術(shù)自由的見識(shí),在“以美育代宗教”這一議題上,只是想提供另一種為別人所忽視的見解。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題之后,林風(fēng)眠提出“以藝術(shù)代宗教”,陳獨(dú)秀提出“以科學(xué)代宗教”,梁漱溟則提出“以禮樂代宗教”……本來林風(fēng)眠、陳獨(dú)秀、梁漱溟等人的上述說法分別具有不同的理論內(nèi)涵和社會(huì)訴求,不同的說法便是向社會(huì)倡導(dǎo)不同的路向,蔡元培向社會(huì)倡導(dǎo)美育,林風(fēng)眠向社會(huì)倡導(dǎo)藝術(shù),陳獨(dú)秀向社會(huì)倡導(dǎo)科學(xué),梁漱溟向社會(huì)倡導(dǎo)禮樂。但吊詭的是,它們不管是同意還是批駁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命題,卻在一點(diǎn)上達(dá)成一致:它們采用的都是蔡元培“以xx代宗教”的句式,在其中,宗教都是被取代的對(duì)象。也就是說,他們的話語選擇、組織和構(gòu)造的程序、語法卻與蔡元培的具有家族相似性,這說明他們的思維方式?jīng)]有超脫蔡元培設(shè)定的藩籬,他們的話語方式不自覺地陷入蔡元培“以xx代宗教”的“敘述圈套”。最終,他們的思想內(nèi)涵和話語表述被含納,轉(zhuǎn)化成蔡元培制造話題的附屬品及其思想、話語的構(gòu)成性要素,為美育在文化場(chǎng)域累積合法化資本,擴(kuò)大影響力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客觀作用。
但存在的問題卻很明顯,由“以美育代宗教”說肇始,“以xx(藝術(shù)、科學(xué)、禮樂等)代宗教”長(zhǎng)期導(dǎo)致美學(xué)、藝術(shù)、科學(xué)和禮樂等領(lǐng)域?qū)ψ诮虄r(jià)值領(lǐng)地的擅自僭越,宗教在中國變成長(zhǎng)期被偏頗對(duì)待的事物以及隨時(shí)可被侵蝕置換的場(chǎng)域。本來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是鑒于當(dāng)時(shí)的中國社會(huì)有人夸大宗教的積極作用,甚至是利用宗教達(dá)到復(fù)辟專制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的目的而提出的具有強(qiáng)烈社會(huì)政治指向性的理論命題,其中夸大了宗教的消極作用,“以美育代宗教”說的口號(hào)式提煉導(dǎo)致人們普遍忽視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對(duì)西方啟蒙主義哲學(xué)的理論誤讀。因?yàn)椴淘唷耙悦烙诮獭闭f準(zhǔn)確地說應(yīng)該限定在美學(xué)領(lǐng)域的,其要義實(shí)際上應(yīng)當(dāng)是“以純粹之美育取代宗教中的美育原素”,并不是如標(biāo)題口號(hào)式地所呈現(xiàn)的“以美育代宗教”。換言之,從理論的準(zhǔn)確性和現(xiàn)代性的場(chǎng)域倫理、價(jià)值分立原則來說,美學(xué)場(chǎng)域并不能也不應(yīng)該取代和僭越宗教場(chǎng)域,審美價(jià)值并不能也不應(yīng)該取代和僭越宗教價(jià)值。事實(shí)上,康德等啟蒙哲學(xué)家使宗教從中世紀(jì)的全能狀態(tài)退回到了拷問人類生存終極意義的純粹精神信仰領(lǐng)域,從而把宗教還給了宗教。在康德等人的理論中,他們雖然批判了宗教在人類社會(huì)各個(gè)領(lǐng)域的肆意擴(kuò)張,以及宗教在人類社會(huì)各個(gè)領(lǐng)域作為意識(shí)形態(tài)崇高客體的壟斷地位,但仍然肯定宗教對(duì)于人類心靈的終極關(guān)懷和精神家園的信仰建構(gòu),從而為宗教保留了存在的合法化空間。于是,美學(xué)在中國落地發(fā)展百年之后,在淡化了文化場(chǎng)輿論混戰(zhàn)和權(quán)力場(chǎng)群魔亂舞的嚴(yán)峻形勢(shì)之后,當(dāng)代學(xué)者潘知常在學(xué)理層面通過較精細(xì)的論證,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乃是“中國美學(xué)的百年迷途”1。
Enlightenment Position and Field beyond the Border:On Cai Yuanpei 's Theor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stead of Religion Education"
Liu Chu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sociology, we can find that Cai Yuanpeis idea of "aesthetics education instead of religion" is a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with strong social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In the cultural field ,starting from the Enlightenment's spiritual standpoint, by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Buddhism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e evolu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art, Cai Yuanpei advocated the substitution of pure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in religion. However, Cai Yuanpei simplified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 the substitution of pure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in religion " with the proposition of " Aesthetic Education instead of Religion ", which was in fact contrary to the field ethics of modernity engineering and eventually produced a field of cross-border issues. After Cai Yuanpei putting forward the idea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stead of Religion," Lin Fengmian, Chen Duxiu, Liang Shuming, et al. advocated "Xx (arts, science, courtesy and music al.) instead of religion." In fact, their discourse unconsciously plunged into the "narrative trap" set by Cai Yuanpei.
Keywords: Cai Yuanpei;"Aesthetic Education instead of Religion";Enlightenment position;Field eth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