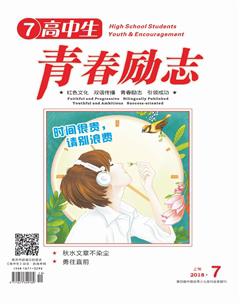作家的黎明與黑夜
2018-07-18 03:54:10姜高蕓
高中生·青春勵志 2018年7期
關鍵詞:習慣
姜高蕓
就寫作習慣而言,作家大致可以分成兩類:展鳥型和夜貓子型。前者喜歡聆聽鳥兒啁啾,在萬物蘇醒時開始思索;后者習慣在夜幕中潛行,享受夜行俠的快樂。
諾貝爾獎得主托妮·莫里森習慣每天黎明時分寫作,先喝一杯熱咖啡,然后遙望晨光越來越亮。她說這時會感覺光明注入她的靈魂,身心都做好了準備。一旦太陽西沉,她的思維就會變得不活躍,文字也變得沉悶。
《愚人船》的作者安·波特也喜歡早起寫作,她說喜歡凌晨的寂靜,不想跟誰說話,也不想見任何人。伊迪絲·華頓寫過《純真年代》,她的所有小說都是在早上完成的。
有人喜歡光明,自然就有人喜歡黑暗,在茫茫黑夜中享受眾人皆睡我獨醒的快樂。
愛倫·坡的諸多驚悚小說在午夜完成,內容也常常是發生在午夜的兇險故事,比如《麗姬婭》《厄謝府的崩塌》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習慣半夜寫作。他回憶說自己年輕時白天要打工,等到年紀大了,應酬又多起來,白天根本沒法寫,每天睡到中午起床,下午訪客如潮,一波接一波,只有到晚上才能靜下心來。
另一個著名的夜貓子是卡夫卡,他的短篇小說《判決》就是在夜晚寫成的。他在日記中寫道:“只有在這樣的時光,我才會感覺身心通透。”
福克納曾經在一家工廠守夜,這對于他創作《我彌留之際》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了。他用幾周的時間完成了這部傳世之作,守夜還可以拿雙倍工資。
普魯斯特的敘述則更有詩意,他寫道:黑暗、寧靜與孤獨如同披風壓著我的肩頭,迫使我用筆去創造光明。
猜你喜歡
中老年保健(2021年7期)2021-08-22 07:43:14
四川文學(2021年6期)2021-07-22 07:50:16
新世紀智能(高一語文)(2020年11期)2021-01-04 00:44:46
新世紀智能(高一語文)(2020年10期)2021-01-04 00:43:52
幽默大師(2019年6期)2019-01-14 10:38:13
文苑(2018年20期)2018-11-09 01:36:02
文苑(2018年19期)2018-11-09 01:30:18
大眾電視(藍天下)(2018年7期)2018-10-08 02:12:02
小火炬·閱讀作文(2014年7期)2018-06-09 00:00:00
中國少年兒童(2017年10期)2017-05-17 06: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