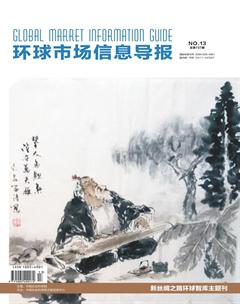社會(huì)融合的制度路徑研究
董向蕓 蔣曉涵
從宏觀意義的融合制度框架到中觀意義的多元融合路徑,不同時(shí)期社會(huì)學(xué)家對(duì)于社會(huì)宏觀結(jié)構(gòu)和發(fā)展的設(shè)計(jì)給社會(huì)融合制度發(fā)展提供了啟發(fā),對(duì)制度的研究是社會(huì)融合政策具體制定、實(shí)施和發(fā)展的重要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
從宏觀意義的融合制度框架到中觀意義的多遠(yuǎn)融合路徑,最后形成相應(yīng)的各種具體制度實(shí)施的實(shí)踐。社會(huì)融合的制度路徑,可以從不同時(shí)期社會(huì)學(xué)家對(duì)于社會(huì)宏觀結(jié)構(gòu)和發(fā)展的設(shè)計(jì)中得到啟發(fā)。
在宏觀層面,馬克思對(duì)于從資本主義社會(huì)轉(zhuǎn)變?yōu)樯鐣?huì)主義社會(huì)到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是對(duì)社會(huì)融合的高度概括。這種的社會(huì)融合狀態(tài)可以描述為“在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高級(jí)階段,在迫使人們奴隸般的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jīng)消失,從而腦力勞動(dòng)和體力勞動(dòng)的對(duì)立也隨之消失;在勞動(dòng)已經(jīng)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gè)人的全面發(fā)展,他們的生產(chǎn)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cái)富的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gè)時(shí)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chǎn)階級(jí)權(quán)利的狹隘眼界,社會(huì)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大多數(shù)情況下,這個(gè)實(shí)現(xiàn)的過程需要經(jīng)歷無產(chǎn)階級(jí)與資產(chǎn)階級(jí)的激烈斗爭,并且需要以無產(chǎn)階級(jí)代替資產(chǎn)階級(jí)作為國家的統(tǒng)治階級(jí)。社會(huì)主義或者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的實(shí)現(xiàn),也是一個(gè)長期漸進(jìn)的建設(shè)過程。同理,無產(chǎn)階級(jí)在取得專政權(quán)之后,需要經(jīng)歷相應(yīng)的步驟才能達(dá)到高度融合的程度:一是從資本主義社會(huì)向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的轉(zhuǎn)變,處于社會(huì)轉(zhuǎn)變時(shí)期這一時(shí)期需要解決社會(huì)沖突的各種矛盾,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來消滅階級(jí)對(duì)立的根源;二是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的初級(jí)階段,以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建立公有制的基本發(fā)展形態(tài);三是共產(chǎn)主義的社會(huì)的高級(jí)形態(tài),達(dá)到共產(chǎn)共有共同勞動(dòng),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全領(lǐng)域的融合。在這里,馬克思所提供的社會(huì)融合的制度路徑是以不同社會(huì)形態(tài)的更替來實(shí)現(xiàn)的,其制度建設(shè)則是以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生產(chǎn)所有制變革為基礎(chǔ),逐步實(shí)現(xiàn)政治領(lǐng)域文化領(lǐng)域等社會(huì)各領(lǐng)域的制度構(gòu)建,從而達(dá)成社會(huì)融合目標(biāo)。該論述不僅為社會(huì)融合提供了具有嚴(yán)密邏輯推理的目標(biāo)設(shè)定,而且為社會(huì)融合的實(shí)踐路徑提供了宏觀指導(dǎo)。
在中觀層面,迪爾凱姆把現(xiàn)代社會(huì)秩序產(chǎn)生危機(jī)的原因歸結(jié)為集體意識(shí)的失效和社會(huì)規(guī)范的喪失,因此,其社會(huì)融合的達(dá)成就以集體意識(shí)和社會(huì)規(guī)范重建為主要路徑。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法人團(tuán)體或是類似于法人團(tuán)體,其組織意識(shí)和職業(yè)規(guī)范都有著極強(qiáng)的約束作用,有利于社會(huì)能夠根據(jù)各種團(tuán)體和群體的特性來調(diào)節(jié)和規(guī)范社會(huì)秩序。在法人團(tuán)體之上,國家作為具有政治強(qiáng)制力量的組織形式,不僅可以通過整體層次上的規(guī)范來調(diào)節(jié)社會(huì)秩序,而且還可以監(jiān)督和節(jié)制各類法人團(tuán)體的行為,從而為個(gè)人在社會(huì)中的自由和發(fā)展提供基本保障。因此,迪爾凱姆的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理論在個(gè)人、法人團(tuán)體和國家之間建構(gòu)出互動(dòng)體系:國家借助于法人團(tuán)體的中介力量來管理和約束個(gè)人,同時(shí)實(shí)施對(duì)法人團(tuán)體的監(jiān)督和制約,以保障法人團(tuán)體正確行使權(quán)利;個(gè)人從法人團(tuán)體那里獲得最直接的生活和工作支持,同時(shí)可以從國家那里獲得對(duì)自己自由和獨(dú)立的保障,避免個(gè)人正當(dāng)權(quán)益受到法人團(tuán)體侵犯;法人團(tuán)體對(duì)上接受國家的管理與指導(dǎo),按照國家的引導(dǎo)實(shí)施對(duì)個(gè)人的管理和道德生活的引導(dǎo),并且從國家那里獲得資源支持,通過國家的力量來實(shí)現(xiàn)在全社會(huì)范圍內(nèi)的協(xié)作與合作的局部管理與協(xié)作合作。最后,通過三者之間這種相互輔助和相互制約的關(guān)系,最終在全社會(huì)形成形成集體意識(shí)和道德約束,消除現(xiàn)代社會(huì)所以面臨的沖突和矛盾。而這個(gè)制度路徑,尤其突出了法人團(tuán)體作為社會(huì)融合的中堅(jiān)力量,在國家與個(gè)人之間所體現(xiàn)的重要作用,使馬克思的宏觀結(jié)構(gòu)建設(shè)在中觀制度層面上得到具體發(fā)展。
帕森斯對(duì)于社會(huì)整合的路徑分析與迪爾凱姆的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思想一脈相承。他將社會(huì)整合定義為社會(huì)均衡發(fā)展的狀態(tài),認(rèn)為社會(huì)系統(tǒng)實(shí)現(xiàn)適應(yīng)、目標(biāo)實(shí)現(xiàn)、整合和維模四項(xiàng)功能方面的協(xié)調(diào),就能實(shí)現(xiàn)系統(tǒng)的和諧發(fā)展。個(gè)人受到系統(tǒng)不同部分功能的規(guī)范而形成相應(yīng)的角色承擔(dān)和文化整合,社會(huì)系統(tǒng)整體依靠于法律、規(guī)范、風(fēng)俗習(xí)慣等不同層面的制度安排,來形成對(duì)于不同部分功能的設(shè)定。整合各個(gè)社會(huì)子系統(tǒng)之間的關(guān)系,可以通過功能協(xié)調(diào)而實(shí)現(xiàn)資源的交流,并推動(dòng)整個(gè)社會(huì)系統(tǒng)的發(fā)展和結(jié)構(gòu)變遷。與迪爾凱姆所提出的法人團(tuán)體的中介作用相類似,帕森斯提出社會(huì)整合的路徑有二:一是通過法律和社會(huì)規(guī)范來避免整個(gè)社會(huì)系統(tǒng)和系統(tǒng)部分受到外來因素影響;二是通過正式制度和傳統(tǒng)習(xí)慣規(guī)范約束人們的行動(dòng)選擇,使其能夠從屬于社會(huì)主流價(jià)值。帕森斯的社會(huì)融合制度路徑設(shè)計(jì)在中觀層面上更加突出了制度的作用,同時(shí)還延伸到了意識(shí)和行動(dòng)領(lǐng)域。
洛克伍德對(duì)于社會(huì)整合理論進(jìn)行了更為細(xì)化的發(fā)展,提供了社會(huì)整合和系統(tǒng)融合兩個(gè)社會(huì)融合考察維度,從內(nèi)外兩種視角來衡量社會(huì)整合程度,對(duì)應(yīng)著社會(huì)整合和系統(tǒng)整合兩種方法。不管對(duì)象是任何的一種社會(huì)群體,企業(yè)、機(jī)構(gòu)、組織或是家庭,都可以衡量它作為整體性的秩序狀態(tài),即靜態(tài)的共場性整合或是動(dòng)態(tài)的時(shí)序性邏輯,在這里,社會(huì)整合是作為關(guān)系性條件而出現(xiàn),系統(tǒng)性整合則是作為制度邏輯的連續(xù)性條件出現(xiàn)的,為社會(huì)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動(dòng)靜結(jié)合的綜合性分析工具。在此基礎(chǔ)上,哈貝馬斯用系統(tǒng)與生活世界二分法的考查框架來分析實(shí)際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程,認(rèn)為現(xiàn)實(shí)世界被協(xié)調(diào)系統(tǒng)的機(jī)制侵入是導(dǎo)致社會(huì)矛盾頻發(fā)的主因。由于各種溝通的媒介殖民了生活世界,人的自由受到極大的限制,因此,社會(huì)融合最主要的路徑是要重建生活世界,包括:通過合理的溝通,實(shí)現(xiàn)生活世界中不同制度領(lǐng)域之間的交流,實(shí)現(xiàn)個(gè)人交往的合理化;關(guān)注生活世界在構(gòu)建時(shí)的結(jié)構(gòu)合理化;通過建立法律的平臺(tái)實(shí)現(xiàn)民主商談與社會(huì)合理化。與此相應(yīng),吉登斯試圖用實(shí)際的交互性來消除社會(huì)整合和系統(tǒng)整合之間的應(yīng)用對(duì)立,相應(yīng)的社會(huì)融合制度設(shè)計(jì)則側(cè)重于,微觀的在場互動(dòng)與跨越時(shí)空的影響延伸能夠形成交互影響,從而實(shí)現(xiàn)對(duì)于社會(huì)融合發(fā)展路徑分析中的制度與行為方法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