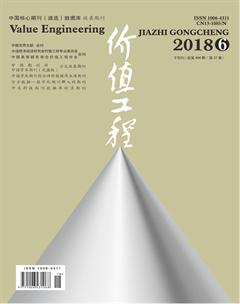新時代國企改革的問題與對策:基于人力資本視角
陳瑋瑜
摘要: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人力資本的地位不斷提升。然而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依然存在人力資本產權不清、治理結構不匹配、人力資本激勵和約束機制低效、人力資本短缺流失等問題。文章探究了上述問題以及背后的原因,并針對性地提出了改善人力資本產權制度,建立有效的治理結構,長效的人力資本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及改善人力資本用人機制和流動機制等對策,以期人力資本能更好地適配國企改革。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structural reforms on the supply side, the status of human capital continues to improve. However, during the proces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there wer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property rights of human capital, mismatch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inefficient human capital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and shortage of human capital still exited.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above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m,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property right system of human capital, setting up an effectiv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long-lasting human capital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mechanism and mobility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so that human capital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關鍵詞: 人力資本;國企改革;人力資本產權;激勵約束
Key words: human capital;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human capital property rights;incentive and restraint
中圖分類號:F27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8)18-0273-03
0 引言
按照中共十九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要求,下一步國企將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如何加快國企改革進程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課題。關于國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標,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完善國企國資改革方案”,“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國有企業結構發生巨大的變化,人力資本的專門化和影響作用也逐漸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力資本理論的創始人是“人力資本之父”舒爾茨,他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投資等活動得來的知識、能力和健康等因素的集合,人力資本比物質資本和非技術性勞動在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1]。除了知識、能力和健康因素,方博(2013)認為人力資本還包括道德、信譽和社會關系等因素的總和,是通過有目的有意識的投資活動所獲得的[2]。人力資本屬于個人所有,是個體在長期的工作生活中通過學習和實踐所積累的。國企可以招募員工來獲得人力資本使用權,但并不等同于擁有其所有權。如果企業增加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就可以提高人力資本存量,而員工較高的知識、能力和技術水平能帶來遠大于物質投資的高收益率[2]。郭棟棟和周禮(2018)也通過較多的文獻研究發現,人力資本作為企業智力資本的最關鍵因素,能直接和間接提高組織整體績效[3]。
我國企業的人力資本產權發生了三次變革,分別從職工持股制到股份合作制,管理層收購,以及從股權分置改革到股權激勵計劃[4]。然而相對西方企業來說,我國國企卻未能很好地運用人力資本來進行企業變革與公司治理,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問題。本文試圖探究在新時代下人力資本在國企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與原因,提出相應的改善對策,為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探索可能的路徑。
1 存在問題與產生原因
1.1 人力資本產權問題
1.1.1 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的配置
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是體制矛盾,關鍵在于所有權(尤其是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的歸屬[5]。我國國有企業成立之初,所有權屬于國家。由于兩權合一、政企不分阻礙了改革開放的發展,因此最初的國企改革是進行兩權分離。兩權分離的結果是剩余索取權歸屬于國家,企業擁有自主的生產經營權,釋放了企業活力。第二階段,國企開始實施股份制改造。由于國企管理者只有控制權,沒有剩余索取權,積極性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在利益不對稱的情況下,部分國企經營者不顧企業發展,以權謀私,不利于國企長久健康地發展[4]。因此,人力資本不參與企業利益分配嚴重影響了管理者的積極性,不利于形成組織公民行為,也降低了績效。優化的企業所有權配置應該是人力資源有權分享企業剩余價值,體現人力資本是企業效益的創造者。
1.1.2 人力資本產權與非人力資本產權
人力資本產權在企業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非人力資本必須通過人力資本的參與才能發揮作用,比如原材料、機器設施等物質資本沒有人力資本的參與無法形成產品和服務[6]。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證券市場環境和公司治理結構依然不成熟,人力資本產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非人力資本產權中的物質資本產權制度具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和認定,但制度卻沒有界定人力資本產權的私有性[6]。因而長期以來,國企員工的人力資本產權利益受到非人力資本的侵占,這是國企激勵制度弊端的根源。因此,最優的所有權結構應該是找到人力資本產權和非人力資本產權在產權結構中的博弈均衡點,明確界定人力資本產權,使其可以一同分享剩余價值。
1.2 治理結構不匹配人力資本產權制度
從計劃經濟時期的“老三會”(即黨委會、職代會和工會)到現代公司制度的“新三會”(董事會、股東會和監事會),國有企業借鑒了國外國企的治理結構,但收效差距較大。西方國家大部分是股權結構決定治理結構,由法人持股,輔以市場機制治理。而我國國企也是采用私法人治理結構,但不同之處在于我國政府的干預更大。水承靜,段萬春,洪潔(2002)通過進行國際橫向比較與中國國企歷史縱向比較,指出我國國企的問題根源在于產權與治理結構之間的匹配問題[7]。他們發現,在國外私法人治理結構中,那些并非國家主導的國企才會獲得較好的績效,而主要由國家控股的國企卻效益低下,原因是經營者的自私自利行為。因此,需要調整產權制度或者治理結構,使兩者達到最優的匹配點。為了改善對管理者的激勵和監管效果,應該將部分所有權賦予給企業家形態的人力資本。國企的經營者是效益的主要創造者,讓他們擁有產權,可以充分激勵他們發揮企業家才能,變成公司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從而提高組織績效。在參與利潤分配后開始新一輪的激勵“反應-刺激”模式,使經營者和國企成為“命運共同體”,人力資本與企業效益呈現螺旋式上升的狀態。
1.3 人力資本激勵和約束機制低效
人力資本產權的最大特點是個人自主性,因此國企不能只憑著控制人力資本來提高個體投資人力資本的積極性。對管理者和員工來說,個體的人力資本是核心競爭力,產權收益應該和經營績效一致。工作績效越高,個體對剩余利潤的期待也會越高。然而在現實中,由于國企改革忽視了人力資本產權的建設,部分國企員工(尤其是高層領導者)獲得的價值收益和職權職級嚴重不對稱,使得國企的激勵約束機制形同虛設[8]。因此,各方開始尋找可以激勵高層人力資本的制度安排,最后決定采用控制權來替代剩余索取權進行激勵。這種激勵機制存在以下的隱患:首先,激勵性不夠誘發自利行為;控制權不能滿足國企經營者對實際利益的需求,他們開始想方設法將職權進行貼現。因此部分國企高層領導在任職期間不惜以身試法濫用職權、謀取私利,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其次,約束性不夠導致機會主義或短期行為;國企經營者的約束機制不夠完善,不必承擔經營失敗而終身追責的風險,因此他們在任職期間不顧企業長期發展而盲目實施短期利益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導致國有資產的自然流失[9]。因此,急需對人力資本激勵約束機制進行調整與優化,從根本上解決國企管理者的激勵問題。
1.4 人力資本短缺流失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企具有比較優越的福利保障條件,包括子女讀書就業、家庭住房和醫療保障等等。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化,工人大規模下崗,國企在計劃經濟時期的整合優勢逐漸消失。又因為國企不重視人力資本產權,高文化高素質人才在現有的分配制度下獲得的收益與付出嚴重不對稱。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民企和外企非常重視人才,他們的人才激勵政策和國企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且隨著互聯網和智能化的發展,很多民營企業(尤其是互聯網公司)的績效薪酬遠遠高于國有企業。在這種情況下,高素質的國企員工紛紛流向高薪酬的民企或者外企,而國企只留下了價值不高的一般員工[8]。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國企混改重組,部分改制國企未能理順關系和整合管理,導致職能錯位、角色沖突,員工產生較高的職業不安全感,紛紛選擇去發展前景更好的民企或外企。另外,由于部分國企合并重組,使得管理者職位減少,傷害到部分個體的利益,導致高層次人才流失。
在當今信息化、知識經濟膨脹的新時代,追求個性和自我價值的90后紛紛進入了就業市場。國企嚴肅認真的企業文化,繁多的規章制度和冗長的流程壓抑了90后的個性和追求,部分年輕的員工由于不適應國企的風格而選擇了離職。
2 改進對策
2.1 改善人力資本產權制度
由于國企人力資本不能分享企業剩余價值,大大降低了管理者和核心員工的積極性和績效。因此,建立和改善人力資本產權制度是國企改革的當務之急。首先,要建立和完善人力資本制度,在法律法規上界定和落實國企關鍵人員的權力利益與責任義務。水承靜,段萬春,洪潔(2002)提出可以參考市場機制,對關鍵崗位價值進行資本化和股權化,讓出部分盈虧分配權和決策權,讓人力資本所有者共享和共擔企業盈虧[7]。經營者離崗時要將剛上任時的與崗位價值等同的貨幣值歸還給企業。換言之,如果經營者想提高人力資本產權價值取得收益,必須努力提高企業績效和效益;同樣的,人力資本所有者也需要為企業的虧損承擔責任,扣除在任職期間造成虧損的股權或貨幣值,構建“人力資本與組織發展的命運共同體”。
其次,要找到產權結構中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博弈均衡點,使前者產權可以向后者轉化。國企人力資本可以采用期權估價法、現金流量貼現法等方式將其量化為貨幣單位,為人力資本產權向非人力資本產權轉化提供基礎 [10]。法律應該對人力資本產權予以承認和界定,人力資本產權和非人力資本產權一同分享企業的剩余利潤索取權和控制權、表決權,并共同承擔企業虧損。
2.2 建立有效的治理結構
為了有效激勵人力資本所有者,解決他們與非人力資本所有者的矛盾,必須建立一套雙方制衡、互相控制和競爭的國企法人綜合治理結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國企本質上是由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按照契約精神結合的經濟實體。按照契約,人力資本必然要求共享剩余價值,然而長期以來這份權益卻沒有得到承認,人力資本份額也未得到量化[10]。因此,亟需建立一套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共同管控的治理機制,形成“命運共同體”。
建立國企法人綜合治理結構的同時,還應該考慮多方利益相關者在當中的作用。國企的利益相關者牽涉面廣泛,除了人力資本產權主體的內部員工,還包括政府主管監管部門,消費者,供應商和融資機構等等。國企法人綜合治理結構應該由各方參與,形成多方利益相關者相互制衡、有效調控的治理狀態。熊云飚(2003)提出可以設立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與調控的運作機制,即把國資法定代表設為最高權力機關,將股權代表、外部專家和員工代表設為執行機構,將政府監管代表、工會代表、消費者和債權人設為監察會進行管理[8]。同時建立內外部雙渠道監控機制,外部通過質量聽證會、投資項目評價系統和金融監測系統等等來進行監管,內部通過監事會進行過程監督和績效評估,以激勵和約束人力資本運作。
2.3 建立長效的人力資本激勵和約束機制
人力資本激勵機制是通過貨幣獎勵、職位晉升和授權等方式來激發人力資本建設企業的積極性。長效的人力資本激勵機制應該包括人力資本存量激勵,增值量激勵以及輔助性激勵三部分。關鍵要將人力資本納入企業利潤分配體系中,分配要注意兼顧效率與公平。第一部分是人力資本存量激勵,比如通過支付薪資獎金來保全人力資本價值,尤其要保證人力資本收益與人力資本存量、投資成本成正比[11]。國企也可以使用技術股、創業股、經營股等分紅權或所有權來進行存量資產索取權的激勵。第二部分是人力資本增值量激勵,根據人力資本在價值創造中的成效來進行利益分配。對經營者可以采取特定目標激勵計劃,股票期權或增值權計劃等激勵方式;對技術人員可以分配技術股份;對生產運營員工可以實施員工持股制度等[11]。第三部分是輔助性激勵,根據人力資本的運作情況適當配以改善工作條件,進行培訓開發,組織關懷和輪崗晉升等方式來激勵人力資本創造更高的績效。為了保障人力資本激勵機制的有效運行,要配套做好相關的制度安排。首先,要建立體現人力資本價值的收益分配制度(比如股票期權和員工持股制度等)。理順人力資本所有者與國企的關系,把握好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股份比例等問題。其次,要改善制度環境。尤其要完善和規范人力資本市場、股票期權市場和經理市場的管理[11]。
人力資源是把雙刃劍,在建立激勵機制的同時也要重視約束機制的實施。約束機制必須能有效地督察和約束人力資本,提高責任意識,防范其采取非道德行為、違法行為或侵犯其他資本的合法權益。具體地,約束機制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著手實施。在宏觀層面上,一是要規范人力資本市場的管理,二要明確法律制度的規定,三是可以通過媒體跟蹤報道充分發揮社會輿論的監督作用[10]。在公司微觀層面上,要從企業的章程、治理條例、財務核算體系等方面落實好約束內容,并充分發揮監事會的監督約束作用。
2.4 改善人力資本用人機制和流動機制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國企改革從“管資產和人、事”變為主要“管資本”[12]。良好的人力資本用人機制可以提高人才利用率,解決人才短缺問題。首先,要進行人才盤點,根據組織發展的需要和人力資本現狀建立人才九宮格。其次,根據崗位要求對關鍵工作崗位建立勝任力素質模型,然后結合人才盤點的結果建立人才供給梯隊和多渠道職業發展路徑,形成一個能快速補給人才的全方位用人機制。另外,人力資源工作人員要追蹤員工在每一次培養實訓和績效考核后的成長,及時更新人才素質能力維度圖,要將晉升和獎勵等激勵措施落實到位。在用人機制的實施過程中,要注意程序公平和結果公平,防止用人唯親的現象發生。
此外,為了優化市場資源配置,必須要保障人力資本的可流動性。一方面要打通社會人力資本市場與企業內部的通道,通過勞動力市場公開招聘或競聘的方式來廣納賢才。招聘過程中可以通過人力資本產權的收益性來吸引高素質高技能人才,形成內外部暢通的人才流動機制。另一方面要優化企業內部的流動渠道,通過激勵措施來維持現有人力資本。由于人力資本具有自我增值性和成長需求,因此國企必須要配套設計好相關的人才培養方案、職業晉升通道和崗位輪換方案,滿足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流動需要和自我增值需求。同時,要規范約束人力資本的流動。通過制度安排來保護國企與人才雙方的合法權益,防范其中一方違反契約精神或采取不正當行為。
3 結語
在新時代下,新經濟激發新動能,人力資本在其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國企混改重組實質上是不同利益集團人力資本的“大洗牌”。新階段的國企改革亟需找到長期以來阻礙國企發展的問題根源,并進行針對性的改進,尤其要創新人力資本運營,充分發揮人力資本的價值,才能有效提升國企整體競爭力,從而更好地建設美麗中國!
參考文獻:
[1]肖焰,蔡晨.基于能力理論的人力資本研究綜述[J].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3(06):21-26.
[2]方博.中國企業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3(7):150-151.
[3]郭棟棟,周禮.智力資本:基于組織績效關系的研究綜述[J].經營與管理,2018(01):46-50.
[4]李寶元.中國企業人力資本產權變革三次浪潮評析[J].財經問題研究,2007(7):66-72.
[5]路璐,盛宇華,董洪超.供給側改革下國企改革與創新效率的制度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18,37(01):32-40.
[6]丁棟虹.人力資本視角下的國有企業性質與改革研究[J]. 財經研究,2003,29(7):3-9.
[7]水承靜,段萬春.人力資本產權化——國企改革的根本途徑[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2,23(10):67-70.
[8]熊云飚.人力資本產權與國有企業制度改革[J].經濟問題探索,2003(7):60-63.
[9]馮朝軍.新時期我國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徑探索[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7(12):42-46.
[10]劉天明.深化國企人力資本制度改革, 促進國企健康穩定發展[J].經濟問題探索,2002(4):84-86.
[11]衛玲.人力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收益分配的制度安排[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35(5):141-145.
[12]李炳堃.國資改革與混合所有制——基于委托代理理論視角[J].經濟問題,2017(12):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