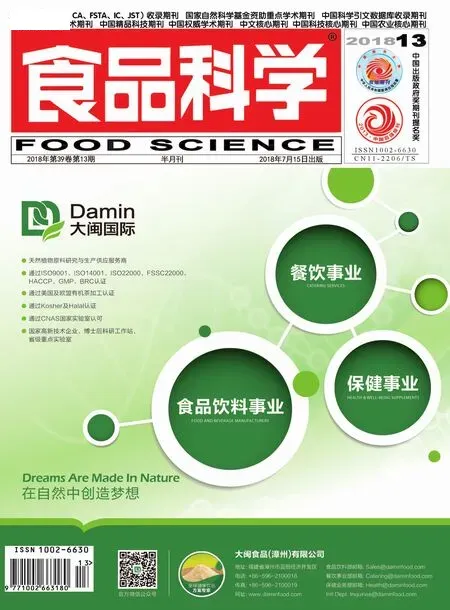益生菌補充改善吡嗪酰胺致大鼠肝損傷及腸道菌群紊亂的效果
李園園,郝海波,劉加洪,葛 冰,馬愛國,
(1.青島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山東 青島 266021;2.青島市中心醫院肺病研究所,山東 青島 266042)
抗結核藥物所致藥物性肝損傷是最常見和最嚴重的不良反應[1],吡嗪酰胺是最常見的誘發肝損傷的一線抗結核藥物[2]。由于“肝腸軸”的存在,肝損傷可以改變腸道微生物組成,破壞腸上皮細胞的完整性[3]。益生菌是一類對宿主有益的活的微生物,具有維持腸道內環境穩態、抑制有害菌的生長、調節腸道微生物組成等作用。自1907年Metchnikoff提出乳桿菌屬于有益菌之后,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乳桿菌可以通過改善腸道微生物組成、抑制有害菌生長及維持腸道內環境穩定而發揮有益作用[4-6]。目前,已有研究發現補充益生菌在抑制酒精性肝損傷、肝癌等方面具有明顯的效果[7-8],但關于益生菌補充對抗結核藥藥物性肝損傷及腸道菌群紊亂影響的研究鮮有報道。本研究根據干酪乳桿菌(Lactobacillus casei,LcS)在人群中表現出明顯改善作用的劑量,設置了低劑量和高劑量LcS組對服用吡嗪酰胺的大鼠進行干預,把益生菌補充與吡嗪酰胺藥物性肝損傷和腸道菌群紊亂結合起來,通過檢測大鼠肝臟組織學變化、血清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和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水平及腸道菌群代表菌株的改變,初步探討益生菌改善吡嗪酰胺藥物性肝損傷及腸道菌群紊亂的效果,為將來更深入的益生菌與抗結核藥藥物性肝損傷及腸黏膜屏障損傷的相關研究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動物、材料與試劑
SPF級雄性SD大鼠40 只,體質量為180~220 g,購于山東魯抗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動物生產許可證號:SCXK(魯)20130001。
活菌型乳酸菌乳飲品,菌株為活性LcS(活菌濃度為108CFU/mL),由天津養樂多乳品有限公司提供。
吡嗪酰胺片(產品批號1507041) 沈陽紅旗制藥有限公司;ALT、AST試劑盒 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糞便基因組DNA提取試劑盒、逆轉錄實時定量聚合酶鏈反應(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PCR)試劑盒 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2 儀器與設備
BX60型光學顯微鏡 日本Olympus公司;Adventurer通用型分析天平 美國Ohaus公司;高速冷凍離心機、Realplex4型qPCR儀 德國Eppendorf公司;RM2135型石蠟切片機 德國Leica公司;12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 日本TOSHIBA公司。
1.3 方法
1.3.1 實驗模型建立及分組
將40 只SPF級雄性SD大鼠適應性喂養1周后,隨機分為4 組,每組10 只。正常對照組(NC組)給予生理鹽水4 mL/(kg·d)灌胃,1 h后給予生理鹽水10 mL/(kg·d)灌胃;吡嗪酰胺組(L0組)給予吡嗪酰胺溶液200.0 mg/(kg·d)灌胃[9-10],1 h后給予生理鹽水10 mL/(kg·d)灌胃;低劑量LcS組(L1組)給予吡嗪酰胺溶液200.0 mg/(kg·d)灌胃,1 h后給予LcS 10 mL/(kg·d)灌胃;高劑量LcS組(L2組)給予吡嗪酰胺溶液200.0 mg/(kg·d)灌胃,1 h后給予LcS 20 mL/(kg·d)灌胃,將開始干預記為第0周,連續干預10 周,實驗期間動物自由進食及飲水。每組隨機抽取5 只大鼠,分別在干預前、干預第6周末、干預第10周末(末次灌胃),采用代謝籠收集各組大鼠糞便各3~5 粒,超低溫冰箱保存備用。末次灌胃后,禁食12 h,水合氯醛麻醉,腹主動脈取血,離心分離血清待測,采集相應器官組織進行實驗檢測。
1.3.2 肝臟組織形態結構觀察
于干預第10周末采集大鼠肝左葉中部組織(0.4 cm×0.4 cm×0.3 cm),體積分數為10%的中性甲醛溶液固定,常規石蠟包埋,進行蘇木精-伊紅染色,中性樹膠封片,在光學顯微鏡下(200 倍)采用盲法觀察各組大鼠肝臟組織形態結構,隨機觀察10 個視野,并按照Knodell等[11]的評估標準進行肝臟組織學評分。
1.3.3 大鼠的肝功能血清學指標檢測
血清ALT和AST均采用120型全自動生化分析儀進行檢測,方法為速率法,檢測時均進行室內質量控制,所有數據采集在控后,再嚴格按照操作規程進行。
1.3.4 大鼠糞便腸道菌群代表菌株定量分析
取待測糞便樣品,采用糞便基因組DNA提取試劑盒提取大鼠糞便樣品中腸道菌群基因組總DNA,操作步驟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操作。采用特異性引物對大鼠糞便中乳酸桿菌、雙歧桿菌和大腸桿菌等優勢菌進行分析。乳酸桿菌上游引物序列:5’-AGCAGTAGGGAATCTTCCA-3’,下游引物序列:5’-CACCGCTACACATGGAG-3’;雙歧桿菌上游引物序列:5’-GGGTGGTAATGCCGGATG-3’,下游引物序列:5’-TAAGCGATGGACTTTCACACC-3’;大腸桿菌上游引物序列:5’-GTTAATACCTTTGCTCATTGA-3’,下游引物序列:5’-ACCAGGGTATCTTAATCCTGTT-3’。
采用qPCR技術對糞便乳酸桿菌、雙歧桿菌及大腸桿菌16S rDNA V3可變區進行定量分析并制作標準曲線,將待測糞便樣品中提取的基因組總DNA進行以上3 種菌株16S rDNA V3可變區qPCR,25 μL PCR體系包括:1 μL DNA(100 ng)、0.75 μL上游引物(10 μmol/L)、0.75 μL下游引物(10 μmol/L)、12.5 μL SuperReal PreMix Plus(2×)、10 μL ddH2O。反應條件:預變性95 ℃,15 min;變性95 ℃,10 s;最佳退火溫度(雙歧桿菌61 ℃、乳酸桿菌55 ℃、大腸桿菌51 ℃),20 s;延伸72 ℃,30 s;共50 個循環,反應完畢后將系統軟件Mastercycler ep realplex自動分析的Ct值代入標準曲線,從而得出以上3 種菌株在待測糞便樣品中的含量。
1.4 數據統計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肝臟組織病理學變化

圖1 干預10 周后各組大鼠肝臟組織蘇木精-伊紅染色(×200)Fig. 1 Liver tissues stained with HE after 10 weeks of intervention (× 200)
由圖1可知,NC組大鼠肝小葉結構清晰,肝索呈放射狀排列,肝細胞胞漿均勻,肝細胞無明顯水腫及脂肪變性;L0組大鼠肝細胞中度水腫,胞漿疏松化,出現明顯的氣球樣變,肝索結構及竇周隙消失,伴有炎性細胞浸潤;不同劑量的LcS組大鼠肝小葉結構均較L0組得到明顯改善,肝小葉結構清晰,肝索呈放射狀排列,肝細胞胞漿均勻,其中L1組大鼠肝細胞輕度水腫,胞漿疏松化;L2組大鼠接近NC組大鼠。

表1 干預10 周后各組大鼠肝臟組織病理學評分(n=10)Table1 Pathological scores of rat liver tissues after 10 weeks of intervention (n= 10)
根據觀察結果對各組大鼠進行病理學評分,由表1可知,L0組大鼠分數明顯高于NC組,經過不同劑量的LcS干預后,評分接近NC組,較L0組顯著下降。
2.2 肝功能血清學指標

表2 干預10 周后各組大鼠血清ALT和AST水平Table2 Serum ALT and AST levels of rats after 10 weeks of intervention U/L
由表2可知,L0組大鼠血清中ALT和AST水平明顯升高,均達到了NC組的1.3 倍左右(P<0.05);補充不同劑量的LcS后,大鼠血清中ALT及AST水平較L0組均明顯降低(P<0.05)。
2.3 糞便腸道菌群分析結果
2.3.1 樣品熔解曲線

圖2 樣品各菌株qPCR熔解曲線圖Fig. 2 qPCR melting curve for three strains
由圖2可知,各qPCR完畢后可見熔解曲線均為單峰,說明擴增產物單一,產物均為目的DNA片段,結果真實性較好。
2.3.2 定量分析結果
2.3.2.1 雙歧桿菌

表3 干預前后各組大鼠糞便內雙歧桿菌定量分析結果Table3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Bifidobacteria in feces of ra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拷貝/g濕糞
由表3可知,在實驗干預前大鼠各組間及組內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大鼠經過不同分組及干預時間的延長,其組間及組內均具有統計學差異(F=2 567.562,P<0.05;F=5.490,P<0.05)。從分組來看,在干預第6周末,L0組大鼠較NC組雙歧桿菌的數量明顯降低;L1組和L2組大鼠雙歧桿菌的數量較L0組均明顯升高,分別達到了L0組的1.24 倍和1.44 倍(P<0.05);在干預第10周末,L2組大鼠與L0組相比,雙歧桿菌的數量明顯升高,達到了L0組的1.46 倍(P<0.05);從干預時間上,與干預第0周相比,L2組在干預第10周末雙歧桿菌的數量明顯升高。
2.3.2.2 乳酸桿菌

表4 干預前后各組大鼠糞便內乳酸桿菌定量分析結果Table4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actobacillus in feces of ra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拷貝/g濕糞
由表4可知,在實驗干預前大鼠各組間及組內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大鼠經過不同分組及干預時間的延長,其組間及組內均具有統計學差異(F=3 568.368,P<0.05;F=6.515,P<0.05)。從分組來看,在干預第6周末,L0組大鼠較NC組乳酸桿菌的數量明顯降低,降低了10.8%(P<0.05);L2組大鼠乳酸桿菌的數量較L0組與L1組均明顯升高,分別達到了1.17 倍和1.14 倍(P<0.05);在干預第10周末,L2組大鼠與L0組相比,乳酸桿菌的數量明顯升高,達到了L0組的1.08 倍(P<0.05)。從干預時間上,L0組及L1組大鼠在干預第6周末,乳酸桿菌的量較干預前均顯著降低;L0組及L1組大鼠在干預第10周末,乳酸桿菌的量較第6周末明顯升高,接近干預前水平;L2組大鼠在干預第10周末,乳酸桿菌的量較干預前明顯升高。
2.3.2.3 大腸桿菌

表5 干預前后各組大鼠糞便內大腸桿菌定量分析結果Table5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scherichia coli in feces of rat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拷貝/g濕糞
由表5可知,在實驗干預前大鼠各組間及組內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大鼠經過不同分組及干預時間的延長,其組間具有統計學差異(F=3 534.307,P<0.05)。從分組來看,在干預第6周末,L0組大鼠較NC組大腸桿菌的數量明顯升高(P<0.05);L1組和L2組大鼠大腸桿菌的數量較L0組均明顯降低(P<0.05);在干預第10周末,L0組大鼠較NC組大腸桿菌的數量明顯升高(P<0.05)。從干預時間上,L0組大鼠在干預第6周末,大腸桿菌的量較第0周顯著升高;在干預第10周末,大腸桿菌的量較第6周末明顯降低,接近干預前水平。
3 討 論
結核病作為一個全球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其治療方案為標準短程化療,主要采用利福平、異煙肼、吡嗪酰胺、乙胺丁醇4種藥聯合治療6~8 個月[1]。研究表明約有2%~28%的患者在抗結核治療過程中出現藥物性肝損傷[12]。吡嗪酰胺作為抗結核治療過程中重要的一線藥物,其肝毒性比其他一線藥物強[13]。因此,尋找能夠減緩結核藥物性肝損傷的物質是非常必要的。益生菌可以通過調節腸道菌群,改善腸道微生物的生態環境及提高機體的免疫功能而發揮作用[5-6],本研究通過益生菌干預服用吡嗪酰胺的大鼠,初步研究益生菌對大鼠肝功能指標及腸道菌群紊亂的改善作用。
ALT和AST是反映肝細胞膜穩定性最敏感的指標[14],ALT主要分布在肝細胞漿內,AST主要分布在肝細胞漿和肝細胞的線粒體中,這兩種轉氨酶在肝細胞內的濃度是血清中的1 000~3 000 倍。在肝損傷的情況下,肝細胞膜通透性增加,轉氨酶被釋放到血液中[14],其在血清中的含量與肝細胞受損程度呈正比。肝臟組織病理學觀察是評價肝臟損傷程度的金標準,在各類動物肝損傷模型中廣泛應用。本研究結果發現較NC組相比,L0組ALT和AST均顯著升高了1.3 倍,肝細胞中度水腫,胞漿疏松化,出現明顯的氣球樣變,肝索結構及竇周隙消失,并伴有炎性細胞浸潤,病理學評分達到3.20 分,這一結果表明,吡嗪酰胺致大鼠肝損傷模型建立成功,提示吡嗪酰胺會引起大鼠肝細胞水腫及炎性細胞浸潤,肝細胞膜通透性增加,使肝細胞膜及肝細胞線粒體損傷;補充不同劑量的LcS后,大鼠血清中ALT及AST水平較L0組均明顯降低,肝小葉結構清晰,肝索呈放射狀排列,肝細胞胞漿均勻,病理學評分均接近NC組,與Wang Yuhua等[15]研究結果相似,提示益生菌能夠通過保護肝小葉結構、肝細胞膜及線粒體膜,起到保護肝臟的作用。
Marshall[16]1998年第一次提出了“肝腸軸”,肝臟和腸道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兩者具有相同的胚胎起源,肝臟70%的血液供應來源于腸道,腸道是防御病原菌的第一道防線。正常腸道菌群具有阻斷病原微生物定植的作用[17],而腸道菌群失調會引發一系列的疾病[18]。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腸道菌群在肝臟疾病的發病中起重要作用[19-20],腸道菌群紊亂會引起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6等促炎性細胞因子及內毒素含量升高,腸道通透性增加,促炎性細胞因子及內毒素透過腸道黏膜進入血液,通過門靜脈作用于肝臟,引起肝臟損傷[15,21-22]。因此,腸道菌群的穩定對預防肝損傷具有重大意義。
人體腸道是一個復雜且龐大的微生物生態系統,定居著數以萬億的微生物,已確定的基因數達到990萬[17,23]。人體腸道菌群主要由厚壁菌門、擬桿菌門、變形菌門和放線菌門等構成[24]。本研究選取3 種腸道菌群代表菌株作為研究對象:大腸桿菌(變形菌門、革蘭氏陰性菌)、乳酸桿菌(厚壁菌門、革蘭氏陽性菌)、雙歧桿菌(放線菌門、革蘭氏陽性菌),采用16S rDNA熒光實時定量技術,對大鼠糞便檢測大腸桿菌、乳酸桿菌與雙歧桿菌的定量變化。結果顯示,大鼠經過不同的分組及干預時間的延長,3 種代表菌株在不同組間及同組內不同時間上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在干預第6周末,L0組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的數量相對于NC組及干預前均明顯降低,大腸桿菌的數量均明顯升高(P<0.05),提示L0組出現腸道菌群失調的情況。可能與抗結核藥的長期使用,使菌群發生改變有關[25];到干預第10周末,大腸桿菌數量雖較NC組明顯升高,但組內比較結果顯示,3 種菌株與干預前差異均無意義,提示腸道菌群失調情況好轉,但仍處于失調狀態,由于抗菌藥不同的處理方案,腸道菌群失調恢復的時間有所不同[26],在本研究中隨著干預時間的延長,機體具有自我修復能力,使腸道菌群失調得以緩慢恢復。研究表明,補充益生菌可以增加腸道內有益菌的含量,減少有害菌的含量,調節腸道菌群[6,22],發揮腸道菌群阻斷有害微生物定植的作用[17]。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干預第6周末,益生菌補充組相對于L0組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數量明顯升高,大腸桿菌的數量明顯降低,且L2組與L1組相比,乳酸桿菌的數量明顯升高(P<0.05)。在干預第10周末,L2組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的數量相對于L0組及干預前均明顯升高(P<0.05)。這與Schneider等[27]研究結果一致,當補充LcS后,腸道內益生菌數量顯著增加。一方面乳桿菌本身作為腸道的有益菌,可平衡腸道菌群種類和數量的改變[28];另一方面乳桿菌可以在腸道中釋放一些對有害菌起作用的抗菌素,也可以釋放有益于雙歧桿菌等有益菌生長的物質,增加腸道內益生菌的數量,增強有益菌的生命力[29]。另外,益生菌必須達到充足的水平才能在腸道中發揮有益作用[30],由于腸道細胞的正常生理代謝或藥物的作用,會使腸道益生菌從腸道排到糞便,因此長期每天連續攝取益生菌才能保證益生菌發揮有益作用[30]。在干預第6周末,L1組乳酸桿菌數量明顯低于干預前,而L2組乳酸桿菌數量高于干預前,且明顯高于L1組;到干預第10周末時,L1組乳酸桿菌的數量較第6周末又明顯升高,接近干預前水平,而L2組乳酸桿菌數量明顯高于干預前,且高于L1組,說明在干預第6周末L1組中LcS在腸道中未達到充足水平且干預時間不夠長,不足以調節由吡嗪酰胺引起的乳酸桿菌數量的減少,而隨著長期每天連續補充益生菌,腸道中乳酸桿菌的數量逐漸升高,這與王然等[6]的研究結果一致,LcS發揮了益生作用,進而調節由吡嗪酰胺引起的乳酸桿菌數量的減少。以上結果提示益生菌能夠抑制大腸桿菌等有害菌的繁殖,促進乳酸桿菌及雙歧桿菌等有益菌的生長,調節腸道菌群的平衡狀態,且隨著干預時間延長及補充劑量的增加,效果更明顯。
綜上所述,長期服用吡嗪酰胺會造成大鼠肝臟損傷及腸道菌群紊亂;益生菌通過調節腸道菌群,對吡嗪酰胺造成的大鼠肝損傷及腸道菌群紊亂具有保護作用,且延長干預時間及增加補充劑量使保護作用更明顯。本研究初步探討了益生菌對吡嗪酰胺藥物性肝損傷及腸道菌群的影響,為將來更深入地研究益生菌與結核藥藥物性肝損傷的關系提供理論支持,為減緩或降低結核病患者藥物性肝損傷和胃腸道不良反應提供新的改善措施和科學依據。益生菌作為一種活性微生物制劑,值得在抗結核治療中進一步研究和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