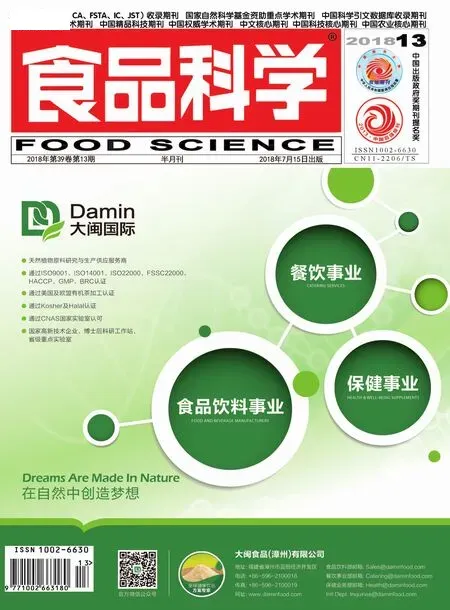對蝦原肌球蛋白不同致敏途徑對BALB/c小鼠致敏性的影響
傅玲琳,謝夢華,王 翀,王海燕,王彥波,
(1.浙江工商大學食品與生物工程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食品質量安全工程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食物過敏是對無害食物蛋白質產生的不良反應,分為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E和非IgE介導、IgE和非IgE混合介導,其中IgE介導最為常見。近些年來其發病率在全球范圍內急劇上升,約8%的兒童及4%的成人對某種或多種食物有過敏現象,食物過敏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1]。目前除了避免接觸過敏原及服用一些可能會產生副作用的藥物外,對食物過敏還沒有有效的預防及治療手段[1]。我國東部地區水產豐富,消費群體龐大。因此,作為全球八大主要食物過敏原之一的甲殼類水產品在我國引起食物過敏的發病率居高不下。研究表明,甲殼類水產品中引起過敏現象的主要過敏原為原肌球蛋白(tropomyosin,TM),且氨基酸序列檢測結果表明,多種甲殼類水產中的TM具有高達95%~100%的同源性[2-3]。但目前對于甲殼類水產品過敏原在分子及免疫學水平的研究還很匱乏。
食物過敏預防及治療的研究大多會借助動物構建食物過敏原致敏模型,基于此模型可以評估食物過敏原致敏性,研究過敏相關免疫反應及機理,研發預防及治療食物過敏的藥物及治療手段[4],其中小鼠是最常采用的實驗動物。小鼠模型根據給藥途徑不同分為兩大類,即口服致敏和局部或表皮致敏,局部致敏常采用腹腔注射(intraperitoneal,IP)[5]。過敏原的口服給藥符合實際生活中食物蛋白經口攝入的情況,但易誘導產生口服耐受,若僅給藥過敏原,則需要大量的過敏原才能引起免疫反應,因此必須借助黏膜佐劑以克服口服免疫耐受,降低過敏原劑量,使小鼠更容易致敏,其中最常用也是公認的最強佐劑是霍亂毒素(cholera toxin,CT)[3,5]。CT是一種AB5型蛋白毒素,由1 個帶有毒性的A亞基(CTA)和5 個無毒的B亞基(CTB)組成,可誘導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4、IL-5顯著升高,而IL-2與干擾素-γ(interferon gamma,IFN-γ)水平無明顯變化,而且還可選擇性誘導以輔助性T細胞(helper T cells,Th)2為主的免疫反應[6]。過敏原腹腔注射作用部位接近黏膜,更易引起黏膜免疫反應,致敏效果好,但食物蛋白不經胃部消化,不能很好地反映其實際進入機體的情況。目前,這兩種給藥方法均被廣大研究者采用,如利用腹腔注射模型或口服灌胃(intragastric,IG)模型評估膳食纖維、中草藥、益生菌、海洋藻類、T細胞多肽等物質緩解食物過敏的效果、探究其生理學及免疫學水平機理[7-11]。Chen Chen等[12]為構建一個能全面評估食物過敏的BALB/c小鼠模型,采用腹腔注射,分別用花生凝集素(peanut agglutinin,PNA)、β-乳球蛋白(β-lactoglobulin,β-LG)和馬鈴薯酸性磷酸酶(potato acid phosphatase,PAP)3 種蛋白致敏小鼠,再采用口服灌胃或腹腔注射相應蛋白進行激發,通過測定血清特異性IgE(specific IgE,sIgE)、IgG1、組胺、臨床癥狀及肺部炎癥細胞浸潤等指標水平,發現3 種蛋白的致敏性強弱為PNA>β-LG>PAP,且腹腔注射激發更易誘發系統性食物過敏。然而,目前關于甲殼類水產品的口服致敏模型研究有限,其致敏的具體機制也尚鮮有闡明。
本研究以甲殼類水產品主要過敏原TM為研究對象,對比口服灌胃與腹腔注射兩種給藥方式對BALB/c小鼠的致敏效果,尋求TM致敏動物模型的最佳給藥途徑,以便建立有效的TM致敏動物模型,并初步探究兩種給藥方式產生不同致敏效果的分子及免疫學機理,既為其他食物過敏原的動物模型構建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也便為后期研究食物過敏預防及治療提供一定的模型及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與試劑
南美白對蝦購自杭州蕭山養殖場;SPF級BALB/c小鼠購自浙江中醫藥大學實驗動物中心,雌性,6 周齡,體質量為(16±2) g,共80 只,隨機分組,每組8 只。
喹啉甲酸(bicinchoninic acid,BCA)蛋白質量濃度測定試劑盒 江蘇凱基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小鼠組胺酶聯免疫吸附測定(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試劑盒 杭州百細生物有限公司;大鼠抗小鼠IgE單克隆抗體(rat monoclonal 23G3 anti-mouse IgE epsilon chain)、大鼠抗小鼠IgG2a單克隆抗體(rat monoclonal SB84a anti-mouse IgG2a heavy chain) 美國Abcam公司;小鼠細胞因子IL-4、IL-5、IL-13、IL-10、IFN-γ ELISA試劑盒,Anti-mouse CD4 FITC、Anti-mouse CD25 PE、Anti-mouse CD127 APC單抗 美國eBioscience公司;RNA提取試劑盒 美國Omega公司;反轉錄試劑盒及熒光定量聚合酶鏈式反應(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PCR)試劑盒 南京諾唯贊生物公司;十二烷基硫酸鈉-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so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SDS-PAGE)相關用品 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其余常規化學試劑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儀器與設備
Mini protein III垂直板電泳儀 美國Bio-Rad公司;Alpha化學發光凝膠成像儀(配有Alphaview SA電泳圖像分析軟件) 美國Proteinsimple公司;VersaMax型酶標儀 美國Molecular Devices公司;LightCycler Nano qPCR儀 瑞士Roche公司;CytoFLEX流式細胞儀美國Beckman Coulter公司。
1.3 方法
1.3.1 TM的提取
參考傅玲琳等[13]的方法提取對蝦肉中的TM。將對蝦除去頭、尾、蝦線和外殼,蝦肉浸泡于預冷的緩沖液A(50 mmol/L KCl、2 mmol/L NaHCO3)中,均質30 min后置于冰上浸提20 min并不斷攪拌。4 ℃、10 000 r/min離心20 min,棄去上清液,將沉淀重懸于緩沖液A中,再次浸提后離心,重復浸提、離心5 次。沉淀浸泡于預冷的丙酮中,不斷攪拌后經紗布過濾,用丙酮反復沖洗,直至沉淀完全變為白色,將制成的丙酮粉置于通風櫥中,過夜風干。將風干的丙酮粉浸泡于緩沖液B(0.02 mol/L Tris-HCl、1 mol/L KCl、0.1 mmol/L二硫蘇糖醇,pH 7.4)中抽提72 h,4 ℃、10 000 r/min離心30 min,將上清液轉移至沸水浴中加熱煮沸10 min,再經8 000 r/min離心15 min,取出上清液,加入30%(質量分數,下同)的硫酸銨,置于4 ℃孵育1 h,拿出后4 ℃、8 000 r/min離心15 min,將沉淀復溶于磷酸鹽緩沖液(phosphate buffer saline,PBS,pH 7.2~7.4)中。用BCA蛋白質量濃度試劑盒測定蛋白質量濃度。
1.3.2 SDS-PAGE分析
配制12%的分離膠與5%的濃縮膠,厚度為1.0 mm。取少量溶于PBS的TM,用PBS稀釋至1~3 ng/μL,與4×蛋白質SDS-PAGE上樣緩沖液混勻,置于沸水浴中加熱5 min后取7 μL上樣。濃縮膠80 V電泳10 min后,分離膠120 V電泳60 min。
1.3.3 BALB/c小鼠致敏模型
口服灌胃致敏模型[14-16]:共5 組,分為正常對照組(PBS1)、霍亂毒素對照組(CT)、低劑量組(IG-L)、中劑量組(IG-M)、高劑量組(IG-H)。小鼠普通飲食飼養1 周后,實驗組每只灌胃與10 μg CT充分混勻的相應劑量的TM(100、300、600 μg)進行致敏,PBS1組灌胃等體積PBS,CT組灌胃等體積含10 μg CT的PBS,每周2 次,連續4 周。之后灌胃對應致敏劑量6 倍的TM進行激發,每周1 次,連續2 周。在致敏前和致敏后、第一次激發以及第二次激發后1 d取血,具體方案見圖1a。
腹腔注射致敏模型[9,11]:共5 組,分為正常對照組(PBS2)、弗氏佐劑對照組(F)、低劑量組(IP-L)、中劑量組(IP-M)、高劑量組(IP-H)。小鼠普通飲食飼養1 周后,實驗組每只腹腔注射與弗氏佐劑(第一次致敏時使用弗氏完全佐劑,之后均為弗氏不完全佐劑)充分乳化的相應劑量的TM(100、300、600 μg)進行致敏,PBS2組注射等體積PBS,F組注射等體積的弗氏佐劑與PBS混合液,每周1 次,連續4 周;之后灌胃對應致敏劑量3 倍的TM進行激發,每周1 次,連續2 周。在致敏前、致敏后、第一次激發以及第二次激發的后1 d進行眼眶靜脈取血,具體方案見圖1b。

圖1 BALB/c小鼠TM免疫方案Fig. 1 Experimental design of in vivo sensitization with shrimp TM in BALB/c mice
1.3.4 小鼠臨床過敏癥狀評分
在第二次激發后的30 min~2 h內觀察小鼠的癥狀,根據評分標準進行評分,本實驗中臨床過敏癥狀評分標準如表1所示。

表1 小鼠臨床過敏癥狀評分標準[7,9]Table1 Scoring criteria for clinical anaphylactic symptoms in mice[7,9]
1.3.5 血清中TM特異性抗體IgE、IgG2a的測定
小鼠血清中TM特異性抗體IgE、IgG2a抗體反應均采用雙抗體夾心間接ELISA法檢測。EIA/RIA 96 孔板包被10 μg/mL純化的TM,4 ℃孵育過夜;用PBS+0.05%吐溫20溶液洗滌3 次后,用5%牛血清白蛋白封閉,37 ℃孵育1 h;洗滌3 次后加入小鼠血清樣品(稀釋5 倍用于IgE抗體,稀釋20 倍用于IgG2a抗體),37 ℃孵育2 h;洗滌5 次后加入辣根過氧化物酶(horseradish peroxidase,HRP)標記的二抗(HRP-大鼠抗小鼠IgE單克隆抗體或HRP-大鼠抗小鼠IgG2a單克隆抗體),37 ℃孵育1 h;洗滌5 次后加入3,3’,5,5’-四甲基聯苯胺底物,37 ℃避光孵育20 min后加入終止液,在490 nm波長處測定各孔的OD值。
1.3.6 血清中組胺質量濃度的測定
血清中的組胺采用小鼠組胺ELISA試劑盒測定。在微孔酶標板中加入標準品或小鼠血清(稀釋5 倍),再加入HRP標記的檢測抗體,用封口膜封住反應孔,37 ℃孵育1 h;洗滌5 次后,加入底物A、B,37 ℃避光孵育15 min。加入終止液,在450 nm波長處測定各孔的OD值,根據標準曲線得到每組樣品的組胺質量濃度。
1.3.7 脾臟共培養上清液中IL-4、IL-5、IL-13、IL-10、IFN-γ細胞因子質量濃度的測定
在第46天,將處死的小鼠浸泡于體積分數75%乙醇溶液中,于超凈工作臺中解剖取出小鼠脾臟,加入少量PBS,用無菌注射器研磨過200 目篩,將濾液轉移至無菌15 mL離心管中,4 ℃、4 000 r/min離心5 min,加入紅細胞裂解液,室溫反應5 min后4 ℃、4 000 r/min離心3 min,再用PBS洗滌2 次后制成單細胞懸液,最后用RPMI-1640培養基重懸細胞,計數后調整細胞數目為106~107個/mL。取1 mL加入24 孔板中,加入已經過0.22 μm濾膜的TM(終質量濃度100 μg/mL),于37 ℃、5% CO2細胞培養箱中培養72 h。再經4 000 r/min離心5 min,取上清液。IL-4、IL-5、IL-13脾臟共培養上清液細胞因子質量濃度的檢測均采用ELISA法,按照試劑盒說明書操作。
1.3.8 結腸中Th17相關轉錄因子IL-17A、IL-23 mRNA相對表達量的測定
無菌條件下解剖小鼠,剪下結腸部位,放入凍存管,迅速置于液氮中冷凍,后轉移至-80 ℃冰箱保存。實驗時取出樣品,立即置于液氮中研磨,按照RNA提取試劑盒說明書提取RNA,用NanoDrop 2 000測定RNA質量濃度及純度后,用反轉錄試劑盒及qPCR試劑盒進行RNA的反轉錄和IL-17A、IL-23 mRNA相對表達量的測定,內參基因為β-actin。各基因引物設計如下:IL-17A上游引物:AGGGAGAGCTTCATCTGTGG,下游引物:AGATTCATGGACCCCAACAG;IL-23上游引物:TGCTGGATTGCAGAGCAGTAA,下游引物:GCATGCAGAGATTCCGAGAGA;β-actin上游引物:CGCAAAGACCTGTATGCCAAT,下游引物:GGGCTGTGATCTCCTTCTGC。
1.3.9 流式細胞儀測定脾臟中Treg細胞比例
小鼠脾臟組織的單細胞懸液的制備方法同1.3.7節,用無菌PBS重懸細胞,計數后調整細胞數目為107~108個/mL。各組分別取100 μL單細胞懸液于流式管中,每管分別按照流式抗體說明書加入Anti-mouse CD4 FITC、Anti-mouse CD25 PE和Anti-mouse CD127 APC,室溫下避光孵育30 min。1 000×g離心5 min后棄上清液,以100 μL無菌PBS洗滌2 次后,用PBS重懸細胞并混勻。同時設定空白組(只加細胞細胞懸液)以及陰性對照組(加入細胞懸液及各抗體單染組)用于流式細胞儀補償的調節。混勻樣品使用流式細胞儀檢測,并設門測定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Treg)(CD4+CD25+CD127Low)比例。
1.4 數據統計分析
實驗得到的所有數據使用軟件GraphPad Prism 7.00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以的的形式呈現,以P<0.05表示差異顯著,以NS表示差異不顯著(P>0.05)。
2 結果與分析
2.1 TM的SDS-PAGE分析結果

圖2 純化TM的SDA-PAGE分析Fig. 2 SDS-PAGE analysis of purified TM
不同批次的南美白對蝦肉通過硫酸銨沉淀、PBS復溶后的SDS-PAGE分析見圖2。其中灰度最深的條帶在36.1 kDa,與理論計算值相同[17],因此可以確定所提蛋白為TM,利用AlphaView SA 3.4.0電泳圖像分析軟件分析可知,TM純度大于95%,其他分子質量位置雖有少量雜蛋白,但含量極低,不影響后續實驗進行。
2.2 食物過敏評價指標的結果分析
過敏原穿透皮膚或者黏膜屏障后,由樹突狀細胞等抗原遞呈細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收集并遞呈給淋巴結中的初始輔助性T細胞Th0,激活的Th0在IL-4的存在下分化為Th2,行使T細胞功能,并促使B細胞表面的B細胞受體結合過敏原,從而激活B細胞。激活的B細胞和Th2效應細胞通過表達的組織特異性歸巢受體,由胸導管和血液循環再回到過敏原進入的組織中,此時,Th2會產生豐富的IL-4、IL-5和IL-13,使活化的B細胞發生IgE類型轉換,從而產生抗原sIgE。這些抗體一部分與抗原直接結合,一部分能與抗原穿透部位的肥大細胞所表達的高親和力IgE-Fc段受體I(FcεRI)結合,其余的抗體則通過淋巴系統進入人體循環,與血液中的嗜堿性粒細胞和遠隔組織中的肥大細胞相結合,使機體致敏。當致敏機體再次次攝入過敏原后,抗原會迅速與致敏肥大細胞或嗜堿性粒細胞表面的sIgE結合,使肥大細胞脫顆粒,釋放組胺、白三烯、5-羥色胺、趨化因子等,而嗜堿性粒細胞分泌大量IL-4、IL-13等細胞因子,從而產生過敏反應組織特異性癥狀[18]。
2.2.1 食物過敏癥狀評分結果
致敏機體再次攝入過敏原后,會快速引發身體多個部位不同癥狀反應,如皮膚瘙癢、紅腫、蕁麻疹、哮喘、咳嗽、惡心、嘔吐、腹瀉等[5]。因此,臨床過敏癥狀評分是評價食物過敏是否產生以及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腹腔注射模型組小鼠臨床過敏癥狀評分結果見圖3,而口服灌胃模型組小鼠基本未有明顯癥狀,因此沒有顯示數據。腹腔注射模型組中,IP-L組只有少數小鼠產生輕微的過敏癥狀,而隨著過敏原劑量的增加,小鼠的過敏癥狀逐漸增強。IP-H組中小鼠的過敏癥狀評分已出現4 分及5 分,即肌肉抽搐和死亡,表明腹腔注射過敏原劑量已接近小鼠最大耐受量,致敏效果顯著。

圖3 腹腔注射模型組小鼠第二次激發后過敏癥狀評分Fig. 3 Anaphylaxis scores of intraperitoneal sensitization model after the second challenge
2.2.2 不同致敏方式導致小鼠血清中TM特異性抗體IgE含量變化分析


圖4 兩類致敏模型小鼠血清中TM-sIgE含量變化Fig. 4 TM-sIgE levels in serum samples of two BALB/c mouse models
血清中sIgE的產生是評估食物過敏的重要指標,且大量研究表明食物過敏的嚴重程度與機體內特異性抗體水平密切相關[11-12,15,19]。在I型超敏反應動物模型中,攝入高濃度過敏原可能會導致小鼠產生免疫耐受,從而降低小鼠的致敏性[1,4,20-21],如胡德建等[20]通過對不同劑量致敏原對小鼠過敏性哮喘模型血清特異性抗體IgE、IgG2a和IL4、IL-5、IL-12、IFN-γ等炎性細胞因子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不同劑量的卵清蛋白(ovalbumin,OVA)可能影響小鼠過敏性哮喘模型所產生的細胞因子類型,低劑量OVA造模的效果最為顯著,高劑量OVA可能導致小鼠發生免疫耐受。根據圖4a可知,口服灌胃模型組TM-sIgE的OD490nm變化范圍大多都在0.2以內,差別很小,只有IG-M組在第一次激發后IgE含量急劇上升,OD490nm達到0.5左右。但所有組別基本變化趨勢相同,在第一激發時,IgE含量均有所上升,但在第二次激發后,IgE含量均下降。在第二次激發后,與CT組相比,僅IG-M組差異顯著,其他兩組均無顯著性差異。根據文獻[20]報道,第二次激發后IgE含量不升反降的原因可能是:在39 d第一次激發時過敏原劑量為致敏時的6 倍,過敏原劑量的突然增大使小鼠體內產生耐受性,因此在第二次激發后sIgE的含量發生下降,此結論在后續實驗中將進一步研究確認。而腹腔注射模型組小鼠在致敏結束后的IgE含量就已明顯高于口服灌胃模型組,且在激發后IgE含量逐漸上升。IP-H組在第二次激發時IgE的OD490nm超過0.6,IP-L和IP-M組的OD490nm也超過0.3,且與F組相比,IP-L、IP-M、IP-H 3 個劑量組均有顯著性差異,尤其是IP-H致敏效果最顯著。
2.2.3 不同致敏方式導致小鼠血清TM特異性抗體IgG2a含量變化分析
IgG是血清中含量最高的免疫球蛋白,占血清中抗體Ig的70%~75%。當正常機體接觸或攝入過敏原,也會觸發一些免疫反應,但產生的是無害IgG,而非IgE。研究表明,在多個利用小鼠模型研究抗過敏物質及其機理的實驗中,小鼠體內的過敏原特異性免疫應答會偏向Th1誘導的同型IgG2a轉換,而sIgE水平顯著下降[11,15]。Rupa等[11]將T細胞表位肽應用于雞蛋過敏原卵類黏蛋白建立的BALB/c小鼠的口服免疫治療中,發現sIgE含量顯著下降,而特異性IgG2a(specific IgG2a,sIgG2a)含量顯著提高。本研究中兩種致敏模型小鼠血清中TM-sIgG2a含量如圖5所示。

圖5 兩類致敏模型小鼠血清中TM-sIgG2a含量變化Fig. 5 TM-sIgG2a levels in serum samples of two BALB/c mouse models
腹腔注射模型組中,TM-sIgG2a含量雖有輕微上升趨勢,且第二次激發時IP-H組與F組相比有顯著性差異,但口服灌胃模型組中IgG2a變化更為顯著,第二次激發后,口服灌胃IG-M組sIgG2a的OD490nm高達1.8,而腹腔注射的IP-H組的OD490nm只達到0.22。因此,口服灌胃模型組中sIgE含量較少,可能是因為機體自身免疫調節使免疫應答趨向于Th1型,從而產生大量IgG2a,降低了致敏效果。
2.2.4 血清中組胺質量濃度變化分析
在食物過敏反應的效應期,由肥大細胞和嗜堿性粒細胞釋放的組胺會與支持血管的平滑肌細胞的特異性受體結合,使血管舒張、通透性增加,并且能誘導分泌細支氣管黏液,導致哮喘。除此之外,組胺還能作用于感覺神經末梢,誘發濕疹部位瘙癢和花粉熱打噴嚏等癥狀[18]。因此,組胺質量濃度也是評估食物過敏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

圖6 兩類致敏模型小鼠第二次激發后血清中組胺質量濃度Fig. 6 Histamine levels in serum samples of two BALB/c mouse models after the second challenge
如圖6所示,在第二次激發后,口服灌胃模型組中IG-L組和IG-H組小鼠血清中組胺質量濃度與CT組相比均無顯著性差異,僅IG-M組差異顯著;而腹腔注射模型組中IP-L、IP-M、IP-H組與F組相比均有顯著性差異,特別是IP-H組,組胺質量濃度達到37 ng/mL,接近F組的2 倍。
2.2.5 小鼠脾臟細胞上清液中細胞因子IL-4、IL-5、IL-13、IL-10、IFN-γ的質量濃度分析
由于Th0所處微環境中各種細胞因子及其他因子的存在,Th0主要分化為兩類不同的效應細胞:Th1和Th2。目前認為,Th1/Th2平衡紊亂、Th0向Th2分化、IgE含量增加是I型超敏反應發作的關鍵環節[20,22]。Th2分泌IL-4、IL-5等多種細胞因子,而IL-4可誘導B細胞的Ig類別轉化,導致IgE含量增加;IL-5具有趨化嗜酸性粒細胞聚集的作用,而嗜酸性粒細胞是參與炎癥浸潤的主要效應細胞,可加速相關組織結構的破壞,這些炎癥細胞和促炎性細胞因子共同引發或促進I型超敏反應的發生和發展。Th1及調節性T細胞則可分泌IFN-γ、IL-10等細胞因子,抑制Th2型細胞因子的促炎作用及致敏原引發的過敏作用[20,23-24]。Th1和Th2這兩類效應細胞通過各類細胞因子相互交叉調節彼此的分化和活性,有相互拮抗的作用。根據上述指標,兩類模型中各自致敏效果最好的一組的Th1及Th2型細胞因子質量濃度見圖7、8。

圖7 兩類致敏模型小鼠脾臟細胞培養上清液中Th1型細胞因子的質量濃度Fig. 7 Th1 type cytokine concentrations in spleen cell culture supernatants from two BALB/c mouse models


圖8 兩類致敏模型小鼠脾臟細胞培養上清液中Th2型細胞因子的質量濃度Fig. 8 Th2 type cytokine concentrations in spleen cell culture supernatants from two BALB/c mouse models
根據圖7、8可知,與CT組相比,IG-M組的IL-5、IL-13質量濃度有所增加,IL-4質量濃度無顯著性差異;而IP-H組與F組相比IL-4、IL-5、IL-13質量濃度均顯著升高;IG-M組IFN-γ質量濃度顯著升高,IL-10質量濃度無顯著性差異,但與腹腔注射模型組相比質量濃度顯著上升。IL-10并不是由Th1特定產生,幾乎所有的淋巴細胞都能合成,因此可能是CT使某些其他淋巴細胞分泌IL-10使之質量濃度增加[24]。IG-M組的IL-5、IL-10及IFN-γ質量濃度均高于IP-H組,而IL-4、IL-13則低于IP-H組。分析可得:口服灌胃組Th2型細胞因子質量濃度大多低于腹腔注射組,而Th1型細胞因子則高于腹腔注射組,口服灌胃致敏效果不佳可能是由于機體產生耐受,影響Th1/Th2平衡,使得Th1細胞因子分泌增多,從而抑制了Th2型效應細胞的分化與活性,降低了Th2細胞因子的分泌[22,25]。
2.2.6 小鼠結腸中Th17相關轉錄因子IL-17A、IL-23 mRNA相對表達量分析

圖9 兩類致敏模型小鼠結腸中Th17轉錄因子mRNA相對表達量Fig. 9 Relative expression of Th17 type transcription factor in colon of two BALB/c mouse models
Th17是一類分化及細胞因子分泌都與Th1和Th2不同的促炎癥效應細胞,最早在小鼠的自身免疫病研究中被發現。Th0在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TGF-β)和IL-6存在下會分化為Th17,然后依靠IL-23維持生存和增殖,并分泌IL-17、IL-6,其中分泌IL-17是這類細胞獨特性質[26]。研究證明,Th17與食物過敏的發生也存在相關性,當食物過敏反應發生時,機體會誘導產生強烈的Th17型免疫應答并釋放大量IL-17、IL-6和IL-23等炎性細胞因子[27-29]。由圖9可知,分別與佐劑組相比:IG-M組的IL-17A mRNA相對表達量未有顯著變化,而IP-H組則顯著增加,且IG-M組與IP-H組相比也有顯著性差異;IG-M組與IP-H組的IL-23 mRNA相對表達量均顯著增加,且IG-M組與IP-H組相比無顯著性差異,可能是由于IL-23是Th17存活、增殖、功能維持的主要因子,并不能促進Th17分化,因此在Th17達到一定量后即維持在此含量,但IL-17A是Th17的效應因子,其含量的多少決定下游過敏效應的強弱。綜上,IP-H組的Th17的轉錄因子相對表達量高于IG-M組,其致敏效果更好,這也與上述sIgE、Th2型細胞因子的測定結果相對應。
2.2.7 小鼠脾臟中Treg細胞比例分析
Treg細胞是一類調控機體免疫功能的細胞群,能維持免疫系統對自身成分的耐受,使機體保持免疫穩態。Treg細胞在口服免疫耐受的產生、食物過敏及其他過敏性疾病的防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分為來源于胸腺的天然型Treg細胞和胸腺外的誘導型Treg細胞(induced regulatory T cells,iTreg)兩種類型。口服耐受的形成依賴于iTreg的分化,而iTreg可以在黏膜表面調節Th2引起的免疫反應[19]。腸道、皮膚、呼吸道和口腔黏膜均可生成功能性Treg細胞并誘導免疫耐受的產生[30-32]。Treg細胞可通過分泌IL-10、IL-35、TGF-β等免疫抑制因子和/或上調IL-2受體的表達抑制其他T細胞與IL-2受體結合,從而抑制其他T細胞的分化與增殖,如抑制抗原特異性Th2的激活,進而抑制其介導的過敏反應[33-36]。由圖10e可知,與對照組相比,IG-M組的Treg細胞比例顯著上升,而IP-H組雖有增加,卻無顯著性,且IG-M組與IP-H組相比也有顯著性上升。Treg細胞與Th17之間有密切關系,兩者分化均需要TGF-β,但高濃度的TGF-β會抑制Th17細胞分化,且促進Treg細胞分化的IL-2會抑制Th17細胞分化,這可能是導致IL-17A mRNA相對表達量未上升的原因之一[25,37]。


圖10 兩類致敏模型小鼠脾臟細胞中Treg細胞比例Fig. 10 Ratio between Treg cells and CD4+ cells in spleen cells from two BALB/c mouse models
3 討 論
近10 年,隨著全球對蝦消費量的增加,對蝦過敏現象日益普遍。研究表明,對蝦中主要過敏原TM的氨基酸序列在多類動物中具有很高的同源性,高同源性使得TM易發生交叉反應,一些對蝦過敏的患者也會對環境中的螨蟲、蟑螂等動物過敏,這也是近些年對蝦過敏現象劇增的原因之一[3]。因此,針對TM建立小鼠致敏模型為研究食物過敏原致敏機制及其體內免疫調節提供了較好的工具,從而為臨床上預防及治療食物過敏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本研究通過臨床過敏癥狀評分、TM-sIgE、組胺、Th1及Th2型細胞因子、Th17型轉錄因子mRNA相對表達量等指標的測定,證明腹腔注射TM比口服灌胃更易使小鼠致敏,其Th1/Th2平衡被打破,Th2反應占據優勢。而根據TM-sIgG2a、Th1型細胞因子IFN-γ以及Treg細胞比例的上升可知,雖有黏膜佐劑的作用,但口服灌胃致敏小鼠仍可能誘導口服免疫耐受的產生,使機體免疫應答偏向Th1型,產生大量無害的IgG2a。此外,本研究結果也顯示,TM過敏受Th1、Th2、Treg、Th17這4 類細胞相互作用調控,但其確切的調控機理還需要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