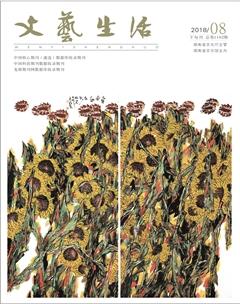談舞臺美術設計的時空認識
劉鏑
摘要:舞臺空間既是舞美工作者進行創造的廣闊天地,也是演員表現劇情的用武之地。這個空間設計得如何,直接影響整個綜合藝術的整體效果。讓舞臺美術以強烈的藝術形式出現于戲劇舞臺上,讓想像縱橫于我們的藝術創作道路之中,讓這股春風時時地吹醒我們的心靈,用智慧積累和艱苦的勞動為舞臺綜合藝術增光添彩。
關鍵詞:舞臺美術;設計;認識
中圖分類號:J8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8)24-0187-01
由于時空決定著藝術的體裁和樣式,決定著作品中人的形象的表現,因此,需要從時空構造的特性上來把握和理解其藝術規律。對于戲劇這種特殊的藝術體裁樣式來說,這一點就顯得尤為必要。因為,作為一種典型的時空藝術,戲劇作品中其藝術表現的假定性、人物性格與命運的展示乃至整個作品的情節結構、情境場面、意象體驗等都無不與其時空構造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西方戲劇藝術的傳統中,時空機制歷來都有著一種組織結構成分、統攝其他結構因素的功能。
西方古典戲劇講述一個故事,主要是通過邏輯嚴密、順序連貫的情節安排來展開的,往往能在觀眾頭腦中留下一個相對完整的時空印象。
由于情節發展是在井然有序的時間和空間中進行的,因此,不僅戲劇的時空觀念很強,而且在劇情展開過程中對時間和空間都有明確的限制;從觀眾欣賞角度來看,劇中明確的時間和具體的空間也一般都有著相應的“具象化”的表現,而力求避免時間不清、地點不明,給人帶來模糊不定的印象。
所以說,時間和空間,在戲劇藝術的表現中原本是不可分離、相關一體的。
戲劇舞臺上的時間在本質上就是一種“主觀時間”。維戈茨基在談到《哈姆雷特》所遵循的時間觀念時指出:觀眾所領會的并不是現實的時間,而劇作家所使用的總是假定的舞臺時間,其縮尺和比例同現實時間迥然不同。
因此,莎士比亞的悲劇始終是一切時間縮尺的巨大變形;通常事件的時間延續,必要的日常期限,每個行為和動作的時間范圍——這一切都完全失真了,并被舞臺時間作了某種通分。
這里所揭示的一個重要事實是:舞臺時間不僅有其假定性,而且舞臺時間“其縮尺和比例同現實時間迥然不同”;也就是說,舞臺時間有它自己的運行、構造的規律,有它自己的節奏。它雖然和現實時間的節奏迥然不同,卻又不是劇作家隨心所欲地臆造出來的,而必須適應觀眾審美心理的規律。
而舞臺時間的假定性之所以能夠為觀眾所接受,也足以說明:這種“主觀時間”在戲劇審美活動中不僅存在,而且對于特定的、屬于某種文化傳統的觀眾群體來說更是一種“我們的”約定俗成的主觀時間。
或者說,戲劇中“主觀時間”的運行節奏先驗地存在于觀眾群體的審美心理結構之中;而對于這個群體之外的、屬于另一種文化傳統的觀眾群體來說,則往往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
比如,在中國戲曲中,幾個龍套在臺上一個圓場,象征著跑了幾十里、幾百里,時間當然也隨之過了多少時辰、多少天。但是對于一個初次看到中國戲曲的西方觀眾來說,也許根本不會產生這種時空變化的感覺。其原因就在于西方心目中并不存在這種先在的文化和審美的心理結構,他不明白戲曲假定的舞臺時間所特有的節奏,也就是維戈茨基所說的藝術時空“縮尺和比例”。
彼得·布魯克曾把戲劇藝術的空間稱之為“空的空間”。這種“空的空間”顯然不僅是指一個空無所有的舞臺,而是指需要利用這個舞臺而創造出具有鮮活的觀演交流、豐富精神內蘊與多樣的人生境界的“審美的空間”。
因為有了這樣的空間,戲劇就有了表達的場所,觀眾也就有了可以聚集的地方;觀眾在觀看時的態度與反應,就會積聚在這個空間里,逐漸形成一種氛圍,再反饋給演員。并且正是有了這種觀演之間的具體而又無形的交流,才足以成為一出完整的戲劇演出。
戲劇中的“空間”,我們可以稱之為“劇場空間”。這個“劇場空間”可能是專為進行戲劇演出活動而準備的建筑場所,也可能是現在被用來進行戲劇演出活動而原本是為其他用途的建筑場所,還可能是一個室外場所或自然曠地。無論是什么樣的場所,當在其中進行戲劇演出活動時,它的原始的空間意義便被“劇場空間”之中建立一個出自特定的戲劇情境的時空結構,演出的內在邏輯只能在這個結構中發揮作用,而這個結構就是“戲劇空間”。
總之,“戲劇空間”在形態上又可分為可以被觀眾的視覺、聽覺甚至觸覺所直接印證其真實存在的“直接的戲劇空間”,以及在感知界限之外需要觀眾利用想像聯想在虛幻中建立起來的“間接的戲劇空間”;而在涵義上則可分為遵循生活邏輯的、具象性的“物理戲劇空間”及非生活邏輯的、抽象性的“心理戲劇空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