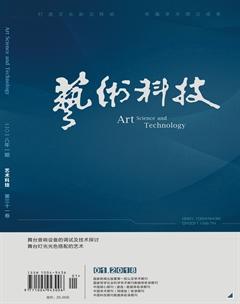梅里亞姆“模式分類”原則的課堂教學與田野實踐
摘 要:梅里亞姆“模式分類”原則能較好地從局內人和局外人的兩種視角對音樂進行分析,如將其在課堂教學中推廣,關鍵在于在課堂理論的學以致用,教會學生以研究者的角度,在一種適當的對話過程中把自己和被研究者有效地綜合起來。
關鍵詞:梅里亞姆;儀式;田野調查
在梅里亞姆(Alan Merriam)對儀式音樂一般性分類原則的評述中,他強調了一個基本的觀念:“民間評價(folk evaluation)是人們對自身行為的解釋,分析評價(analytical? evaluation)則是外來者(或局外人)在對異文化的體驗的基礎上建立的,意在認識人類行為的規律性的更廣闊的目標。”[1]在此基礎上,國內民族音樂學學者們歸納了既符合漢學人類學總體要求,又滿足中國本土文化信仰與經驗的儀式音樂分類原則:“其一,從局內人和局外人的不同角度,對音樂的音聲內容所攜帶的體裁分類因素及不同的劃分可能性進行探討,這是對儀式音樂具有的信仰文化內容進行符號性闡釋的必要前提。其二,對于儀式中的音聲內容里音樂與非音樂因素,以及二者之間存在的符號——結構性關系進行討論和分析。”[2]有鑒于此,筆者在對洞庭湖的“巫教”音樂和“搬郎君”儀式及音聲進行前期調查、資料整理與整體分析基礎上,基于“模式分類”原則對洞庭湖區的“伴郎君”儀式與音聲進行整體闡述。
“模式分類”原則。某些分類方法是以儀式內容的表現形式來確定其模式特征。例如,陶思炎將中國祈禳文化劃分為4類:語言型、圖像型、動作(行為)型和器物型。其中語言型主要表現為重語言表達的祈禱,包括口頭行為,如誦讀、歌唱和祝禱等。這種分類方法相對于“局內人”來說,帶有某種“局外人”的眼光。[2]
在“模式分類”原則的基礎上,為了更細致地展現民族音樂志文本的具體方式與過程,在筆者作為研究者對“伴郎君”儀式與音聲進行系統化采集時,將本儀式受訪的對象分成兩類。
第一類受訪者為長期生活在洞庭湖區的“師公”從業者,這一批受訪者普遍年齡較大,年紀介于60歲至80歲之間。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主要職業為漁民、農民、商販或手工業者;以“巫師”“師公”“師公子”等身份為人做法事多屬于半職業性質,主要為當地人進行還愿、祈福、沖儺儀式或醫治一些疑難雜癥。這一類人一般不參與當地的婚喪儀式,其師承關系多為家族性的父兄傳承,少部分為師徒傳承,傳承譜系在口述史與文字史之間都有一部分盲區,很難找到超過四代的傳承關系。這一部分人所受的宗教知識較為完整,書本知識相對較少,對操持儀式的禮儀與音樂有較扎實的功底。
第二類受訪者為洞庭湖各區縣從事群文工作、非遺研究與整理工作的從業者以及一部分地方高校的儀式研究學者。這一部分人普遍年紀較輕,年齡介于30歲至50歲之間。已經接受過相對完備的宗教學、音樂學、民俗學與儀式學的系統學院式教育,并長期深入洞庭湖區各類儀式場域進行田野資料整理與調查工作,也具備一定的實踐經驗。由于受到過專門性的理論訓練,對于“師公”們講述不清的事項,他們提出了較為理性的補充,并給予筆者對于“伴郎君”儀式體系問題上較為清晰、完整的提示。
田野調查實例:何謂“郎君”?
在“搬郎君”儀式里,主客體關系比較明顯,“搬”為接請之意,接請的神祇,統稱為“郎君”。此“郎君”神是指代一位還是數位;指代關系為行業祖師、還是祖先,或是神祇。
師公觀點:“郎君”神指代多位,其中既有行業祖師,也有神祇,還有湖區公眾信仰歷史人物如姜女、伏波等。民間有單獨的唱段,如“搬先鋒”“搬八郞”“搬開山”“搬鐘馗”“搬梁山土地”“搬橋梁土地”“搬判官”“請催生娘娘”“請十州和尚”“搬小鬼”等,皆是儀式中所接請的“郎君”神。其接請指代關系不以人物、行業、身份為依據,而以事件所求為主。如需造房建宅,則搬開山、搬橋梁土地;如需除病驅疫,則搬鐘馗、搬八郞;如需祈福還愿,則搬娘娘、搬姜女。儀式中可以一事請一位,也可以一事請多位。
學者觀點:“郎君”崇拜與洞庭湖區的多神信仰相承,如果橫向地研究,“搬郎君”儀式與洞庭湖流域的土地戲、請七姑娘、開桃源洞、接孟姜女等小戲在早期可能都是一體的。如“土地戲”最早叫作“搬梁山土地”,是“搬郎君”儀式里最后接請的一位神仙。過去把“搬梁山土地”放在儀式的最后,是因為這一出戲最詼諧幽默,大家都喜歡看。在演出的時候,“土地戲”由一人戴面具扮土地出場,接請出他的3個老婆,每一個都分配有任務,最后工作完成后順利地回家,師公與觀眾一同下場。又如“請七姑娘”“開桃源洞”“接孟姜女”之類的風俗歌舞,也是以接請神仙為主,過去都是儺愿戲的一個種類,湖區冬季常演的《孟姜女尋夫》《孟郞教學》《孟郞祭棒》,還有西洞庭湖區的師道戲《孟姜女哭長城》《搬師娘》等,也都屬于接請神仙的小戲,名稱雖然不同,形式卻是差不多的。
總結上述觀點,洞庭湖區的“郎君”通常被視為神的象征性建構,由特定的行業性群體與地緣性群體供奉,借此來集聚或辨識“圈內人”或“圈外人”。洞庭湖區的“郎君”由想象的社群創造,如同中國的許多宗教人物一樣,既有與社會親族相關的神祇,也有溯源于真實歷史人物的原型,湖區的社群合理地接納與保留與之相關的血統、地位與才德,建立形成完整的儀式體系,借以辨識、凝聚、強化社區群體的地緣性與血緣性,在此基礎上形成完整的春祈秋報的理念,進一步鞏固家族倫理與道德精神的一致性。
上述調查模式是一種嘗試,較好地將兩種視角加以結合并在課堂教學中推廣,其關鍵在于在課堂理論的學以致用,教會學生以研究者的視角,在一種適當的對話過程中把自己和被研究者有效地綜合起來。
參考文獻:
[1] Merriam,Alan P .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M]. EvanstonⅢ: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32-33.
[2] 楊民康.貝葉禮贊:傣族南傳佛教節慶儀式音樂研究[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219.
作者簡介:曾娜妮(1977—),女,湖南文理學院藝術表演與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