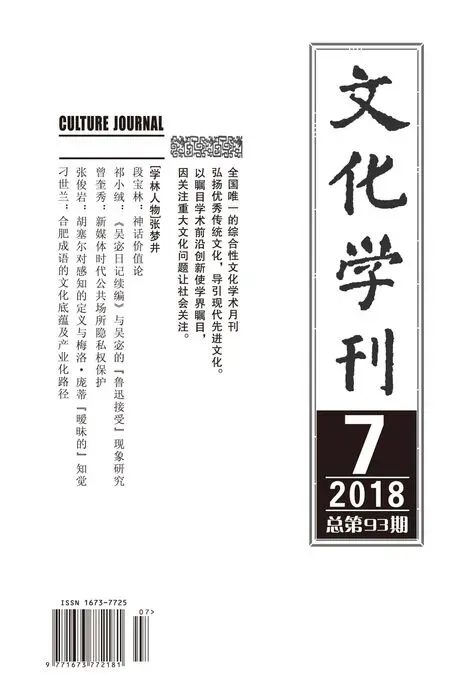新嚴而致精
——馬健《文化規制論》讀后
張 鵬
(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北京 100048)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自序》中談到:“近今史學之進步有兩特征。其一,為客觀的資料之整理。……其二,為主觀的觀念之革新。”不止史學,大凡人文之學術,皆要以觀念(包括問題)和材料為根底,而對前人涉足未多之新領域,尤其如是。讀完吾友馬健博士的新著《文化規制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此般體會益徹。全書言簡思贍,蘊藉堂奧,籠統觀之,大略有“新”、“嚴”、“精”三端,依次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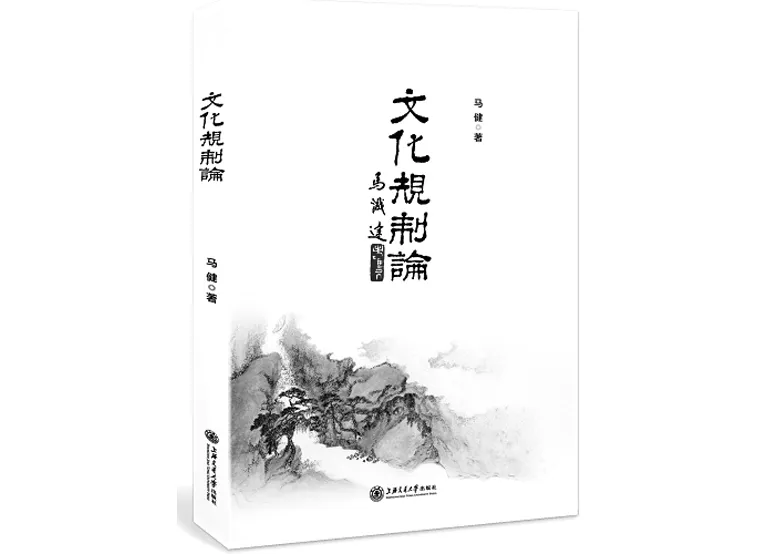
馬健著《文化規制論》立體書影
一為“新”。研究對象方面,盡管作為歷史存在現象之“文化規制”,于中西都現世甚早,但將其作為宏觀文化學中的一個獨立問題或學術領域而深入探究的,此著確為濫觴之作。作者將之定位為與社會規制、經濟規制處于同等地位的“第三種規制”,衡較了文化規制與此兩者的差異,初步建構起“文化規制”理論體系,足見其裨補學術空白之價值。在方法上,緣于規制問題本就涵蓋了法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多學科,因而對規制的研究必須統攝若干學科方能獲取真義。作者綜合了社會學、管理學、心理學、藝術學等多個角度,開展多維文本的通讀與互證,保障了觀點和結論在切實有據之上呈現喜人之新意。
二為“嚴”。本書作者曾治科學技術哲學,經歷過周詳而扎實的思辨訓練,故在本書的行文推理、設問析疑中都展露出鮮明的謹嚴之風。此前關于“文化規制”的論述片鱗只爪,零散無序,對這些復雜材料和其中隱匿的學術脈絡的細致爬梳,亟需作者在開闊的視野內持守清晰的邏輯思路,還需兼備史家的深雋與論者的高卓,它們凝集為嚴謹的文理結構及其背后的治學態度。書中對重要命題逐本溯源,對同一概念作兩方或多方的對比檢討,力將其中的繁復關系層層解析,如第二章首先引入“規制”概念,包括不同學科領域對“規制”與其他相近名詞的判別,緊接著考察了“文化”的不同定義;又回顧了國內外關于“文化規制”“文化管制”或“文化監管”等近似概念的研究,從共時、歷史性、靜態性和動態性等四個維度對“文化規制”進行釋義,即:“狹義的文化規制僅指的規制者依據法律授權對微觀文化主體實施的文化控制;廣義的文化規制則包括規制者對微觀文化主體實施的一切文化控制。文化規制既不同于普通法的間接司法干預,也不同于宏觀調控的間接參數干預,而是直接的行政干預。”在如此縝密而系統的推衍、析理之后,該定義具備了客觀而嚴整的品格。另,在書中多處論證中,都大量援引了經典案例和圖表數據,施論歸理,以嚴勝人,等等這些都透射出作者嚴謹的求真精神。
三為“精”。如前文所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是問題和材料,而問題有竑微,材料有廣狹,在此之上生成的敘述和結論亦有精粗之別。本書的問題非常集中,關于“文化規制”中心命題的內涵探賾和細部考索是其最關鍵核心所在,還自然延展到外部若干重要問題,以及由此生發了對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深度觀照。如第六章詳述了“文化規制”的中國范式,從對文化自由度的探討入手,追溯新中國建立以來該問題與社會、政治、文化的內在關聯,并呼應了之前與古代、與日本等縱橫比較坐標之內的討論,歸納了目前中國的文化規制存在的諸如權責不清、獨立性弱、無章可循、隨意性強、透明度低、問責性差等問題,最后提煉出中國的文化規制改革必須尋找的新的規制哲學——文化善制。如此這些論述,初看頗感宏大,但細讀便隨處可見作者的精深立意。
作者的博士導師胡惠林先生在為本著作序中說:“這其中的許多問題、命題都是很少有人認真探究過的,已有的關于中外文化管理的研究基本沒有達到這個深度和高度。這樣說,并不意味著馬健的博士論文已經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但是,他比迄今為止研究中外文化管理的那些論著更深刻。”平實的言語間賞譽了此書在該領域的開創意義,同時也指明此書的撰寫僅是這項研究的起步,尚有更為深廣的空間等待墾殖,誠為知者之論。馬健博士是時下文化藝術管理學界穎秀特出的青年學者,篤志問道,勤讀敏思,雖學路迢艱,卓拔之境可在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