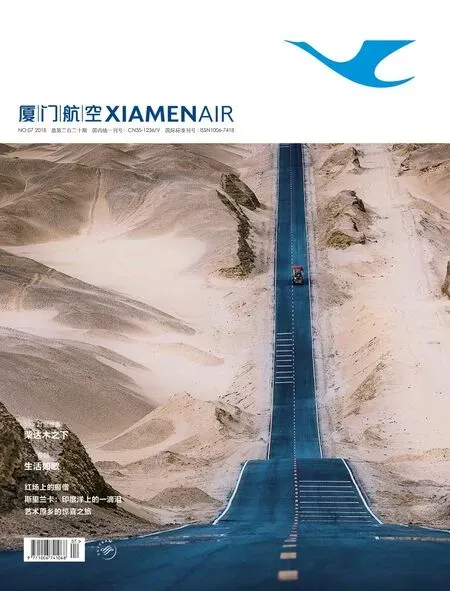一切都是從生活出發(fā)
撰文_慕橋
把民歌比喻成“生命的歌”,那么現(xiàn)代民謠則可看作“生活的歌”,它是生命落地后又在塵土中再騰起的數(shù)個(gè)瞬間。
2013年的奧斯卡最佳紀(jì)錄片頒給了一部制作簡陋、畫面粗糙的小成本電影《尋找小糖人》。電影雖然簡陋,卻不妨費(fèi)些筆墨描述下這部好電影中講述的故事。一名美國民謠歌手羅德里格斯默默無聞,在20世紀(jì)70年代初,他一共出了兩本唱片,在本國大概只賣出了6張。他成了徹頭徹尾的“失敗者”,正如他自己歌里唱的那樣:“I wonder how many times you've been had.And I wonder how many plans have gone bad.(我不知道你經(jīng)歷過多少次,我想知道有多少計(jì)劃已經(jīng)失敗了。)”在圣誕節(jié)前兩周被唱片公司解約。出身底層的他回到了自己的軌跡,一個(gè)普通的墨西哥移民后代在底特律繼續(xù)從事體力工作,拆棚子,打零工,因時(shí)運(yùn)和生計(jì)而不得不放棄夢想,過著再平凡不過的生活。
但這一切都只是行進(jìn)到中段,無論是電影還是羅德里格斯的人生。在不知道哪一艘渡洋的大船上,哪一個(gè)熱愛音樂的廉價(jià)錄音機(jī)里,命運(yùn)這般鬼使神差,羅德里格斯其中一張唱片被人帶到遙遠(yuǎn)的南非。隔著一整個(gè)大西洋,他的歌聲和歌曲描寫的故事成為反抗種族隔離制度年代的南非民眾追求自由生活者的啟蒙藝術(shù),打動(dòng)了無數(shù)人。在南非有超過50萬張的銷量且知名度可與滾石樂隊(duì)相提并論。但與其他知名的美國歌手不同,南非的歌迷得不到任何一點(diǎn)關(guān)于羅德里格斯的信息,除了專輯歌曲之外唯一能了解的只有專輯封面上一張并不清晰的相片。兩張專輯后,他好像也就此銷聲匿跡。一位忠實(shí)的歌迷鍥而不舍地踏上了尋找“小糖人”(羅德里格斯的成名曲《Sugar Man》)之路。新晉導(dǎo)演本德讓勞爾在了解了全部故事后花費(fèi)6年時(shí)間,完成了這部電影,導(dǎo)演數(shù)次受困于資金斷裂,捉襟見肘之下,突發(fā)奇想地用iPhone 5和8mm的老式相機(jī)完成了最后場景。片子的結(jié)尾,羅德里格斯被問到對自己在另一個(gè)國家成為巨星有什么想法,他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這個(gè)問題。當(dāng)然,由于這部片子,這位歌手在垂老之年得到了應(yīng)該得到的尊重,演唱會(huì)門票在歐美一售而空。
平凡是多數(shù)人的狀態(tài),貧乏卻是可以改變的。對忠實(shí)的歌迷來說,追尋一個(gè)自己喜歡歌手的下落只是平凡生活之外的一種樂趣,它是生活的一味調(diào)料——它讓平凡的生活并不顯貧乏。對于羅德里格斯而言,做一名歌手曾經(jīng)是他的夢想,夢想無法落地時(shí),他必須回到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去,但這一切并不能阻止他所想要對生活表達(dá)的一切唱成歌。這大概就是民謠的魅力和精髓所在。


國內(nèi)一名知名鍵盤手寫過一條段子:在東直門吃飯,一個(gè)包間里,有一個(gè)彈琴賣唱的哥們兒,拿著箱琴推門進(jìn)來了,說:“哥,聽歌嗎?”一推開門看里面坐著李志、東野、萬曉利、郝云、臧鴻飛、謝強(qiáng),一愣,轉(zhuǎn)身出去了。”賣唱人遇到了歌曲的原唱者。這個(gè)段子的真實(shí)性有待考究,但這份真實(shí)與詼諧,在民謠歌手的生活中,絲毫不缺。早些年當(dāng)民謠歌手李志還沒有從原單位離職時(shí),他成天背著他的吉他穿著破舊的紅色帶帽衫全中國找演出機(jī)會(huì),周末唱完歌回去繼續(xù)上班。深圳的梁穎還一邊在公司做著財(cái)務(wù)算賬的工作,晚上把上周認(rèn)識(shí)的姑娘寫進(jìn)新歌里。這兩年我們所感受到的“中國民謠的復(fù)蘇”,某種程度上僅僅可以看作是音樂市場工業(yè)化的成熟。有樂評人認(rèn)為華語樂壇已陷入原創(chuàng)絕境,紅起來的歌屈指可數(shù),創(chuàng)歷史新低,而綜藝與選秀依然在不斷地消費(fèi)著老歌遺產(chǎn)。歌曲選秀的綜藝節(jié)目就這樣牽起一連串默默無聞藏于民間的民謠歌手,提供給他們一次次亮相在大眾面前的機(jī)會(huì)。但當(dāng)今許多民謠歌手,甚至是大部分獨(dú)立音樂人,也自覺又自動(dòng)地進(jìn)入一種“工業(yè)化人生”的自我設(shè)定軌跡中。養(yǎng)生,商演,只談小情小愛。“獨(dú)立”變得只剩下“自我”。總有人源源不斷地輸出雷同的音樂,又源源不斷地有人埋單,并為之“感動(dòng)到熱淚盈眶”。

民謠是最接地氣的音樂。它與民歌的區(qū)別是首先不關(guān)乎民族和傳統(tǒng),而是基于民間和當(dāng)下。當(dāng)一個(gè)人覺得只有非唱不可時(shí),他已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一名民謠歌手。它更是一種表達(dá)方法。它沒有嚴(yán)格的劃分和標(biāo)準(zhǔn),它甚至可以沒有樂器,也可以是任何曲風(fēng)與語言。一切實(shí)質(zhì)源自歌手對自身成長經(jīng)歷和生活環(huán)境的忠實(shí)。這是一首好民謠的前提:誠懇而敏銳。民謠,離我們最近的藝術(shù),我們最聽得懂的藝術(shù),是生發(fā)于真情,總是戳中我們內(nèi)心最柔軟地方的那道光束。而當(dāng)下這種雷同,小情小愛的自憐與感懷,是否反映的也恰恰是當(dāng)下真實(shí)年輕的心呢?在中國臺(tái)灣,并沒有民謠一說,人們將之統(tǒng)稱為“民歌”。回顧臺(tái)灣流行音樂史,會(huì)發(fā)現(xiàn),20世紀(jì)80、90年代和20世紀(jì)臺(tái)灣流行音樂的輝煌是建立在60、70年代民歌運(yùn)動(dòng)基礎(chǔ)之上的,這場民歌運(yùn)動(dòng)幾乎改變了臺(tái)灣流行音樂的面貌。今天,我們的民謠又可以唱出怎樣的我們?
在我們年復(fù)一年的平淡歲月里,民謠就像是從十二個(gè)月中可以出走的一個(gè)月,想從生活提煉與萃取的一個(gè)“月”;想在田野、路上、鄉(xiāng)村、人間把我們的生活“哼唱”出來。
在這個(gè)充滿偽詩意、自我陶醉的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我們對于詩和遠(yuǎn)方的向往,大部分時(shí)候都只能投影于聽一首民謠來帶給我們慰藉。而所謂遠(yuǎn)方和詩,是精神的寬慰與向往,是躁動(dòng)的少年心氣,是暗涌澎湃的中年時(shí)間。是歌的故事,也是時(shí)間的故事。這世間需要年輕的心,一代代地把《關(guān)雎》的歌謠唱下去。不管江山如何易容,總會(huì)有春暖花開,這是江山的道理,它總會(huì)給年輕的心一處可以寄托的夢土,一杯可以邀月的醉酒,一柄敢于劃開虛偽的利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