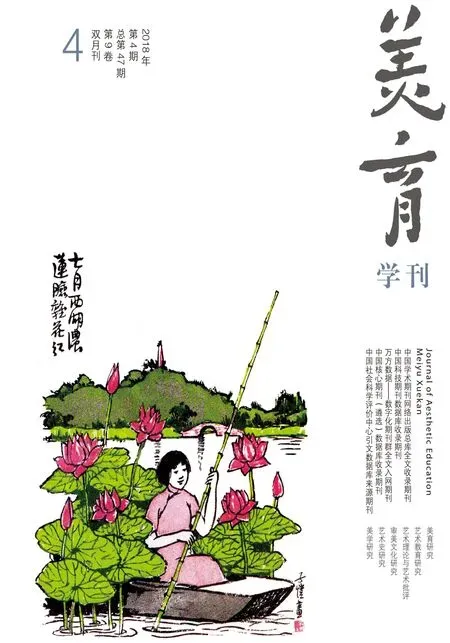深度介入音樂(lè)
——《音樂(lè)批評(píng)的五種哲學(xué)視角》評(píng)介

如果說(shuō)伴隨舞蹈、詩(shī)歌、宗教崇拜的音樂(lè)作品其意義顯而易見(jiàn)的話,那不伴隨姿態(tài)、不附加詩(shī)詞、不寄托宗教情懷的純音樂(lè)作品還具有意義嗎?如果有,那它的意義又是什么?我們(包括音樂(lè)學(xué)家、音樂(lè)專業(yè)人士以及非專業(yè)的音樂(lè)愛(ài)好者們)究竟該怎么聽(tīng)音樂(lè)?用什么樣的語(yǔ)言來(lái)評(píng)論音樂(lè)?我們又批評(píng)什么?
五位當(dāng)代美國(guó)音樂(lè)學(xué)家圍繞著這些問(wèn)題在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xué)舉辦的第六期塔爾海默系列講座(Thalheimer lectures)中各抒己見(jiàn)。美國(guó)哲學(xué)家、批評(píng)家金斯利? 普萊斯將系列講座匯編成《音樂(lè)批評(píng)的五種哲學(xué)視角》(On Criticizing Music: Fiv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981)一書(shū),并撰寫了導(dǎo)論部分。
有趣的是,我們可以看到五位學(xué)者在觀點(diǎn)上的相似與延伸,也能捕捉到他們言語(yǔ)中的隔空交鋒。查爾斯?羅森在《影響:剽竊抄襲與靈感啟示》中指出音樂(lè)批評(píng)的兩種路徑:第一,針對(duì)模仿痕跡明顯的“抄襲剽竊”作品要立足于“起源性理解”,即從節(jié)奏、音高組織、結(jié)構(gòu)思維等元素來(lái)看它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對(duì)經(jīng)典作品進(jìn)行了模仿與改變,由此進(jìn)行價(jià)值判斷。第二,針對(duì)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靈感啟示”作品則要立足于“構(gòu)造性理解”,即訴諸于音樂(lè)內(nèi)在構(gòu)造的分析來(lái)實(shí)現(xiàn)對(duì)經(jīng)典作品的價(jià)值判斷。羅森的“構(gòu)造性理解”觀念在約瑟夫? 科爾曼的講座《學(xué)術(shù)性音樂(lè)批評(píng)的現(xiàn)狀》中得到進(jìn)一步延伸。科爾曼認(rèn)為音樂(lè)批評(píng)首先要從音樂(lè)分析出發(fā),著重關(guān)注藝術(shù)作品是如何獲得內(nèi)聚性或有機(jī)統(tǒng)一性的,但這只是起步之基,音樂(lè)批評(píng)應(yīng)走向更為寬廣的審美價(jià)值判斷。蒙羅? 柯蒂斯? 比爾茲利在《理解音樂(lè)》中基于符號(hào)理論提出理解音樂(lè)的三種類型:“因果性理解(或稱起源性理解)”“構(gòu)造性理解”和“語(yǔ)義性理解”。盡管比爾茲利的觀點(diǎn)表面看似是對(duì)羅森、科爾曼觀點(diǎn)的一種延續(xù),但他對(duì)其他四人的批判也是顯而易見(jiàn)的,他強(qiáng)調(diào)音樂(lè)作品是情感意涵和人性特質(zhì)的符號(hào)外化。羅斯? 羅森加德?蘇博特尼克的《作為后康德批判的浪漫主義音樂(lè)》闡述了針對(duì)不同音樂(lè)風(fēng)格的作品,音樂(lè)批評(píng)的關(guān)注點(diǎn)應(yīng)有所不同,即音樂(lè)批評(píng)應(yīng)結(jié)合特定歷史語(yǔ)境。卡爾? 阿申布萊納的《音樂(lè)批評(píng):踐行與瀆職》則強(qiáng)調(diào)了音樂(lè)批評(píng)所應(yīng)有的中立態(tài)度和評(píng)判職責(zé)。可以看到,這些講座展現(xiàn)了學(xué)者們各自的學(xué)術(shù)旨趣、研究立場(chǎng)和語(yǔ)言風(fēng)格,他們所探討的分析與批評(píng)的關(guān)系、音樂(lè)批評(píng)的理論與方法等問(wèn)題值得探討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