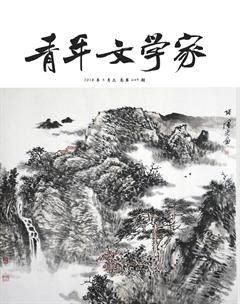狂野的東非
沈海濱
我到過(guò)世界上很多地方,看過(guò)不少繁華的都市和美麗的風(fēng)景,雖然都不可復(fù)制,但隨著時(shí)間流逝,有些地方的輪廓會(huì)逐漸模糊,甚至相互重疊,逐漸淡出腦海。而我這次東非大草原之旅,相信將會(huì)永遠(yuǎn)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我個(gè)人覺(jué)得,在有生之年,能走進(jìn)一次東非大草原看看,確實(shí)是一個(gè)終身難忘的地方。在這里你能體會(huì)到最真實(shí)的世界和自己,人和動(dòng)物的關(guān)系令人著迷,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讓我們驚奇……
夢(mèng)開(kāi)始的地方——塞倫蓋蒂大草原
我從坦桑尼亞乞力馬扎羅山下的莫西出發(fā),經(jīng)過(guò)阿魯沙到達(dá)恩格勒自然保護(hù)區(qū)和賽倫蓋蒂東非大草原上,每天很長(zhǎng)時(shí)間都在車(chē)上,所到之處,我的心靈深處就受到了一次痛快淋漓的洗禮。坦桑尼亞恩格勒自然保護(hù)區(qū),像一個(gè)平底鍋一樣,中間是草原,四周是陡峭山坡。進(jìn)入公園首先出來(lái)迎接我們的是成群的狒狒,小狒狒騎在大狒狒身上,紅紅的屁股好可愛(ài)。還有多種動(dòng)物在里面有吃有喝,好多動(dòng)物和諧相處,一派生機(jī)勃勃景象。我還看到兩個(gè)羚羊在一個(gè)獅子前面幾米遠(yuǎn)故意穿過(guò),獅子理也不理……這里的動(dòng)植物種類(lèi)繁多,數(shù)量驚人,被譽(yù)為“非洲伊甸園”。
塞倫蓋蒂自然是無(wú)與倫比的,她廣博、浩瀚、狂野而不失嫵媚,每一個(gè)見(jiàn)到她的人,都會(huì)由衷地感嘆一聲“震撼”。塞倫蓋蒂也堪稱(chēng)非洲最壯麗的地方。的確,你很難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如此平坦浩瀚的草海,數(shù)百萬(wàn)野生動(dòng)物在這片土地上來(lái)回遷徙,逐水草而居,新陳替代,生生不息,一百多萬(wàn)年以來(lái)沒(méi)有什么變化。
在塞倫蓋蒂大草原,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非洲大草原的壯闊。還看到了美麗的斑馬,在一大群黑壓壓的角馬前用它性感的條紋展示自己的魅力。深夜無(wú)眠,象吼獅叫仿佛就在耳邊,在探險(xiǎn)的刺激和不安中逐漸入夢(mèng)。
清晨被清脆的鳥(niǎo)叫和奔跑聲驚醒,走出帳篷外,成群成群的瞪羚和黑羚圍繞在屋前屋后,一旦發(fā)現(xiàn)人走近便一躍回歸了叢林。我看到了成群結(jié)隊(duì)的水牛在過(guò)河,笨拙的大象在污泥中洗澡,性感的斑馬和丑陋的角馬像好朋友一樣共飲一河之水,呆萌的長(zhǎng)頸鹿三三兩兩地覓食,還有叢林之王戲耍野豬,森林里一片和諧安詳?shù)木跋螅瑒?dòng)物們各司其職,各占其位。
中午的陽(yáng)光太火辣,動(dòng)物們也都找到納涼的地方隱藏起來(lái)了。于是小憩之后,晚上四點(diǎn)夕陽(yáng)下近距離看到了雄獅,和早上的母獅相比,不怒自威,森林之王的氣勢(shì)可見(jiàn)一斑。我最?lèi)?ài)的長(zhǎng)頸鹿在夕陽(yáng)的映襯下顯得更加優(yōu)雅。
一整天的塞倫蓋蒂雖說(shuō)對(duì)所有人最激動(dòng)的時(shí)刻是看到大貓,但是在沒(méi)有大貓的時(shí)候更多的時(shí)光是這些食草動(dòng)物陪伴我們的。今天的游覽讓人十分滿意!我的住地是一個(gè)在山頂?shù)亩燃俅濉V苓呌袧M山遍野層層疊疊的植物景色優(yōu)美,山間的風(fēng)聲伴隨著鳥(niǎo)鳴還有植物的清香,酒店雖小但卻非常有特色。這里簡(jiǎn)直是我心目中最佳世外桃源。
東非大草原的明珠——馬賽馬拉
肯尼亞的馬賽馬拉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區(qū),是東非最大的動(dòng)物保護(hù)區(qū),面積達(dá)1670平方千米,幅度相當(dāng)廣大。對(duì)于習(xí)慣了現(xiàn)代生活的都市人來(lái)說(shuō),坐上一輛老式的吉普車(chē)一路顛簸著觀光,的確是一種全新的體驗(yàn)。在離你那么近的地方,三三兩兩地停著些斑馬,很閑適地咀嚼著青草或是別的什么。一群長(zhǎng)頸鹿慢慢地靠過(guò)來(lái),靜默著,似乎瞥了我們一眼,同樣也是淡淡的。不多久又看見(jiàn)了犀牛,狒狒和其他一些動(dòng)物。有意思的是它們都很安靜的。面對(duì)這目不暇接的近在咫尺的野生動(dòng)物群場(chǎng)景,大家紛紛埋頭用手中的各式相機(jī)拍照。
東非草原上的旅游專(zhuān)用車(chē)都安裝了功率強(qiáng)大的對(duì)講機(jī),方圓幾百里路都可以聽(tīng)到對(duì)講機(jī)的通話,當(dāng)司機(jī)們開(kāi)車(chē)在草原上尋找并發(fā)現(xiàn)食肉猛獸時(shí),便互相通知一聲,以便司機(jī)趕去得以讓本車(chē)游客觀賞到草原猛獸。畢竟猛獸不是隨處可見(jiàn)的呀。不一會(huì)兒,汽車(chē)慢慢駛近一處緩坡地停了下來(lái),我抬眼望去,前方呈圓弧型包圍狀已經(jīng)停了幾輛汽車(chē),在包圍圈的中心有幾只獅子,它們正旁若無(wú)人地在一個(gè)小河邊飲水。平生頭一次如此近距離觀看獅子這種猛獸,非常興奮,還有些莫名的緊張。想想在國(guó)內(nèi)去動(dòng)物園看動(dòng)物,動(dòng)物們都是被關(guān)在籠子里,而游客們則是自在地在園內(nèi)觀賞。而現(xiàn)在則完全相反,游客們把自己關(guān)在鐵皮汽車(chē)?yán)铮瑒?dòng)物們則自由自在地草原上生活,完全視人類(lèi)如無(wú)物。那幾頭雌獅和幼獅仔們對(duì)形成包圍圈的汽車(chē)以及車(chē)內(nèi)的游人毫不理睬,不慌不忙地低著頭飲水。它飲水的方式就與我們?nèi)粘K?jiàn)的小貓喝水差不多,伸出舌頭舔著喝。它飲了幾口水之后,抬頭向附近的灌木叢林慢慢走去,有的側(cè)倒頭就趟在大樹(shù)下睡覺(jué)了。
一路上隨處可見(jiàn)的各種動(dòng)物都平靜地在草地上吃草,到處是一片寧?kù)o、和平的景象,完全沒(méi)有看到電視《動(dòng)物世界》中的草原上猛獸獵殺水牛以及弱小動(dòng)物的血腥場(chǎng)景。導(dǎo)游給我們解釋道,草原上所有動(dòng)物之間維持著大體上的平衡,當(dāng)然“森林法則”仍舊主導(dǎo)著動(dòng)物世界。食草動(dòng)物處于生物鏈的中低端,食肉動(dòng)物處于高端但數(shù)量很少,而且只有在饑餓時(shí)它們才覓食獵取食物,現(xiàn)在是臨近傍晚時(shí)分,獅子、豹子等食肉猛獸基本躲藏在蔭涼處休息,很少再去捕食。
非洲火烈鳥(niǎo)的家園——博格利亞湖
博格利亞湖國(guó)家保護(hù)區(qū)位于肯尼亞裂谷省巴林戈縣,東非大裂谷的邊緣,是大裂谷眾多咸水湖泊中的一個(gè),常年吸引大量火烈鳥(niǎo)來(lái)此棲息。火烈鳥(niǎo)體型大小似鶴,高約80-160厘米,體重2.5-3.5千克。雄性較雌性稍大,通身為潔白泛紅的羽毛,翅膀上有黑色部分,覆羽深紅,鍺色相襯。體態(tài)優(yōu)美,亭亭玉立。全身的羽毛主要為朱紅色,特別是翅膀基部的羽毛,光澤閃亮,遠(yuǎn)遠(yuǎn)看去,就像一團(tuán)熊熊燃燒的烈火,因此叫火烈鳥(niǎo)。
該物種的體型長(zhǎng)得也很奇怪,身體纖細(xì),頭部很小,鐮刀形的嘴細(xì)長(zhǎng)彎曲向下,前端為黑色,中間為淡紅色,基部為黃色。黃色的眼睛很小,與其龐大的身軀相比,顯得很不協(xié)調(diào)。火烈鳥(niǎo)用梳子一樣的嘴在湖面尋覓食物,它們將鳥(niǎo)緣倒過(guò)來(lái),避免湖水打濕頭部,這是生物進(jìn)化的奇跡。 紅色不是火烈鳥(niǎo)本來(lái)的羽色,而是來(lái)自其攝取的浮游生物。火烈鳥(niǎo)通過(guò)食用以小魚(yú)、小蝦、藻類(lèi)、浮游生物等傳遞ASTA(中文叫蝦青素),而使原本潔白的羽毛透射出鮮艷的紅色。紅色越鮮艷則火烈鳥(niǎo)的體格越健壯,越吸引異性火烈鳥(niǎo),繁殖的后代也更優(yōu)秀。
火烈鳥(niǎo)主要棲息在溫?zé)釒}水湖泊、沼澤及礁湖的淺水地帶,喜歡結(jié)群生活。博格利亞湖位于肯尼亞裂谷帶邊緣,是碳酸鈣湖,面積大約有30萬(wàn)平方公里。博格利亞湖沿岸為樹(shù)林、干旱的矮樹(shù)林和草地覆蓋,每年都吸引了數(shù)十萬(wàn)只火烈鳥(niǎo)聚集于此,湖面常如鋪展開(kāi)來(lái)的粉紅色地毯般美麗動(dòng)人,這些火烈鳥(niǎo)也為博格利亞湖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fēng)景線。這種粉紅色的狂歡是非洲最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之一。
我此次來(lái)博格利亞湖就是為了拍攝火烈鳥(niǎo)的。我前幾天在坦桑尼亞的恩戈羅恩戈羅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區(qū)也看到了二處火烈鳥(niǎo)生活的湖泊。山腳下的湖面上生活著火烈鳥(niǎo)湖泊的左邊藍(lán)色的彎道里有許多紅點(diǎn),那就是火烈鳥(niǎo)。在肯尼亞的博格利亞湖上卻生活著一眼望不到邊的火烈鳥(niǎo)群,據(jù)說(shuō)這里是非洲族群最大、數(shù)量最多的火烈鳥(niǎo)棲息地。湖邊的地勢(shì)過(guò)于平坦,周邊沒(méi)有制高點(diǎn),拍攝的照片都是平視的,沒(méi)有氣勢(shì)!可惜我沒(méi)帶無(wú)人機(jī),所以沒(méi)有拍到在空中俯拍的照片其氣勢(shì)、壯觀的視覺(jué)效果。
壯觀的馬拉河生死之渡
馬拉河之渡即是每年隨著旱季的來(lái)臨,數(shù)以百萬(wàn)計(jì)的角馬、斑馬等食草野生動(dòng)物就會(huì)組成一支遷徙大軍,浩浩蕩蕩從非洲坦桑尼亞的賽倫蓋蒂國(guó)家公園,向肯尼亞的馬賽馬拉國(guó)家自然保護(hù)區(qū)進(jìn)發(fā),尋找充足的水源和食物。這是一段3000公里的漫長(zhǎng)旅程,途中不僅要穿越獅子、豹埋伏的草原,還要跨越布滿鱷魚(yú)、河馬的馬拉河,有大批的角馬將死在路上,但同時(shí)也將有大批小角馬在途中誕生。因此,這也是自然界最偉大的遷徙旅程。當(dāng)在遷徙季節(jié)您有機(jī)會(huì)來(lái)到馬拉河畔,就有可能看到馬賽馬拉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區(qū)內(nèi)發(fā)生的成千上萬(wàn)頭角馬前赴后繼,從鱷魚(yú)張開(kāi)的血盆大口中橫渡馬拉河的壯觀場(chǎng)面。
馬拉河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壯闊,但河岸陡峭,河里鱷魚(yú)、河馬密布,恐怖之極。在馬賽馬拉一望無(wú)際的大草原和藍(lán)天白云之下,數(shù)百萬(wàn)計(jì)的角馬和斑馬浩浩蕩蕩,追隨著雨水和嫩草長(zhǎng)途遷徙至此,滾滾而來(lái)的蹄聲和漫天揚(yáng)起的塵土,萬(wàn)“馬”奔騰的壯觀場(chǎng)景最好的詮釋了它們對(duì)于生命的渴望。
橫渡馬拉河絕對(duì)是整個(gè)大遷徙過(guò)程中最最蔚為壯觀,令人振奮的場(chǎng)景,每一個(gè)親眼目睹渡河過(guò)程的游客都會(huì)極其興奮的告訴你太值得了,太驚奇了。馬拉河是在馬賽馬拉草原靠西部的一條河流,將整個(gè)馬賽馬拉草原一分為二,而遷徙隊(duì)伍為了能夠到達(dá)馬賽馬拉草原食物更豐盛的另一側(cè),不得不橫渡馬拉河。在6-9月份大遷徙的季節(jié)中,幾乎每天都會(huì)在馬拉河的若干點(diǎn)有橫渡的隊(duì)伍,所以是否能夠看到角馬斑馬橫渡馬拉河就靠運(yùn)氣了。
首先馬拉河很長(zhǎng),蜿蜒在馬賽馬拉草原上,而且距離大部分酒店比較遠(yuǎn),所以一般游客需要安排一整天的準(zhǔn)備。一般情況下在哪里看到大規(guī)模角馬斑馬聚集的場(chǎng)景,這里肯定就有戲了。不過(guò)耐心是必須的,絕對(duì)不能去打擾遷徙隊(duì)伍,而且就算看渡河也要離的遠(yuǎn)遠(yuǎn)的,否則角馬隊(duì)伍會(huì)因?yàn)槭艿襟@嚇而停止。一般情況下動(dòng)物們只要不受干擾,角馬隊(duì)伍很快就會(huì)渡河,瞬間河邊塵土飛揚(yáng),萬(wàn)馬奔騰,我們也是熱血沸騰,快門(mén)聲一片。拍攝渡河最容易入手也很重要的是拍攝大場(chǎng)景。整個(gè)藍(lán)天白云之下,馬拉河上,千百頭角馬同時(shí)橫渡,拍的就是氣勢(shì)!渡河開(kāi)始之后,有一個(gè)場(chǎng)景很精彩的,那就是拍攝角馬奮勇跳入河水中的瞬間。不知道角馬怎么想的,渡河就渡河吧,沒(méi)事往里跳什么呢?又不是懸崖邊,河水也不深,多此一舉。不過(guò)可以看出它們的決心,義無(wú)反顧啊。
不過(guò)有時(shí)候河水比較深,渡河難度就增加了。有些河段還需要奮力游過(guò),否則還搞不好被水沖走。還好角馬和斑馬天生會(huì)游泳,事實(shí)上大多數(shù)草原哺乳動(dòng)物都會(huì)一點(diǎn)。渡河過(guò)程并非一番風(fēng)順,如果這么容易倒好了。最大的威脅之一就是馬拉河中的鱷魚(yú)。東非的鱷魚(yú)都是大大號(hào)的尼羅鱷,塊頭3米以上,體重1噸左右,差不多就是一小轎車(chē)。別看它們?cè)诤舆叺臅r(shí)候呆呆傻傻,動(dòng)也不動(dòng),可是在馬拉河水里,絕對(duì)是它們的天下。對(duì)于鱷魚(yú)來(lái)說(shuō),沒(méi)有吃不到的,只有不想吃的。能否看到鱷魚(yú)獵殺,那就更看運(yùn)氣了。
當(dāng)時(shí)角馬的渡河動(dòng)靜太大,驚醒了河邊休息的鱷魚(yú)們。鱷魚(yú)其實(shí)也聰明,守在幾處角馬渡河必經(jīng)之處。鱷魚(yú)很快潛入水中,不見(jiàn)蹤影,再次看到的時(shí)候,它嘴里已經(jīng)死死咬住角馬頭。鱷魚(yú)不是蛇,無(wú)法將角馬整個(gè)吞入;它也不像獅子獵豹等獵食動(dòng)物,沒(méi)有可以咬碎撕裂的犬齒,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guò)大力甩動(dòng)動(dòng)物尸體,進(jìn)行快速的死亡翻滾,使之分開(kāi),然后再一塊塊吞入。這種鏡頭就是沒(méi)到過(guò)非洲的人也時(shí)常會(huì)在電視中偶爾看到的。
經(jīng)過(guò)一番生死搏斗,遷徙部隊(duì)絕大部分順利到達(dá)彼岸,開(kāi)始新的征程。
東非大草原之子——馬賽人
在馬賽馬拉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區(qū)內(nèi)還生活著土著人,讓我們可以一睹非洲真正主人的真實(shí)生活。馬賽人住在用紅土和牛糞建成的小房子,房子很低,一般沒(méi)有窗子。當(dāng)?shù)氐穆糜伟l(fā)展起來(lái)以后,馬賽人就不再以狩獵為生,改為飼養(yǎng)牛羊,有時(shí)牛羊和人就住在同一間屋子里。這種相處雖然對(duì)人和動(dòng)物來(lái)說(shuō)也許是最自然的。與其他旅游地不同的是,東非大草原馬賽馬拉的馬賽人還不會(huì)用一些顯而易見(jiàn)的小伎倆招徠顧客,他們就是那樣自顧自地生活著,無(wú)視那些好奇的目光,就如同千百年生活的一樣。那里的生活節(jié)奏十分緩慢,衣食無(wú)著的人們并沒(méi)有太多可以努力的對(duì)象。矮矮的屋棚外倚著的老婦人,歲月的侵襲使得她的黑皮膚看著都有些發(fā)灰了,只是那雙眼依然是清明的,她并不理睬來(lái)來(lái)往往的人群,就那么定定地看著一個(gè)方向,凝固了,或者多年來(lái)就沒(méi)有移動(dòng)過(guò)。看著那目光,一時(shí)便不知心里的哪一個(gè)地方有了什么觸動(dòng)。
以畜牧為生的馬賽人是完全的游牧民族,終年成群結(jié)隊(duì)流動(dòng)放牧,幾乎全部依靠牲群的肉、血和奶為生。他們的村莊用帶刺灌木圍成一個(gè)很大的園形籬笆,環(huán)繞一圈泥屋構(gòu)成,可容納4~8個(gè)家庭及其牲畜。走進(jìn)馬賽馬拉保護(hù)區(qū)外的一個(gè)馬賽村莊,映入眼簾的是獨(dú)特的馬賽人民居。枯樹(shù)枝圍起一個(gè)籃球場(chǎng)大小的小院,幾座由樹(shù)枝、牛糞和泥巴堆起的小屋前站著十幾個(gè)村民。男人們裹著被稱(chēng)為“束卡”的紅色披風(fēng),手持一頭細(xì)一頭粗、用來(lái)趕走野生動(dòng)物的馬賽木棍。女人們穿著色彩絢麗的“坎噶”裙裝,戴著精細(xì)彩珠串成的頭飾和項(xiàng)圈。馬賽男人的披風(fēng)之所以選擇紅色,是為了趕走獅子等野生動(dòng)物,保護(hù)他們賴以生存的牛群。牛在馬賽人的傳統(tǒng)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不吃蔬菜,只喝牛奶、牛血,吃牛肉。每天晚上,村民們會(huì)把村子的大門(mén)用枯樹(shù)枝堵嚴(yán),讓牛群聚集在村子中央。他們自己在窄小的泥屋里守著小牛,睡在牛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