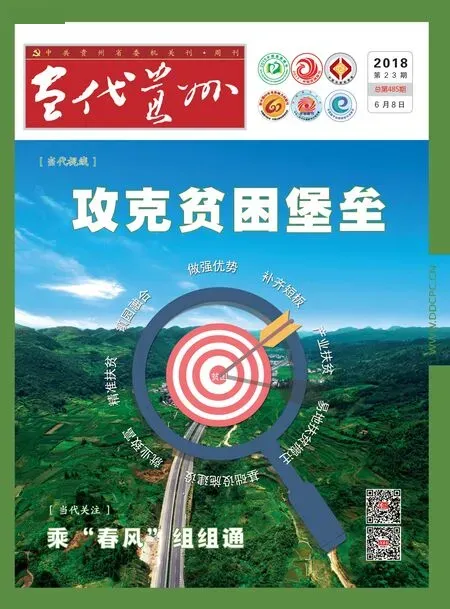傳儺雕技藝 存一方文脈
文_當代貴州全媒體記者 / 汪梟梟
儺面具是安順屯堡地戲的核心載體。隨著社會的發展,儺雕已發展成為安順的支柱性文化產業,從事儺雕技藝的民間藝人達上千人。然而在產業繁榮的背后,地戲文化的傳承也應引起重視。
5月31日,記者走進安順市西秀區劉官鄉周官村屯堡儺雕文化博物館,館內形態各異的安順地戲面具——仡佬族、苗族、彝族等民族的儺戲面具、陽戲面具、撮泰吉面具讓人目不暇接。博物館的主人,安順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儺雕傳承人秦發忠說:“說起儺雕,就不得不說安順地戲。”他耐心地向記者講述起每一個面具背后的歷史故事。
秦發忠告訴記者,在安順有很多村落被稱為“屯”或“屯堡”,如天龍屯堡、云峰屯堡、周官屯、鮑家屯、云山屯……屯堡中婦女的裝束,和貴州少數民族地區十分相似,上前一問,卻是漢族。據《安順府志·民風》所載,他們身上所穿的衣服“皆鳳陽漢裝也”。
這里的建筑和習俗,都與鄰近的村子不同。而這些,都要追溯到600年前明太祖朱元璋“調北征南”,數十萬大軍揮師西南并留守于此,以軍屯的形式駐扎下來,且“家人隨之至黔”,江南的服飾、飲食、娛樂習俗也隨之而來。
自江淮而來的古老戲種
歷經600多年的歲月洗禮,當年的屯軍和移民依然恪守著其世代傳承的明朝文化習俗和服飾特點,他們的習俗也逐漸演變,形成了今天獨具特色的“屯堡文化”。
地戲是屯堡文化的重要載體,俗稱“跳神”,是屯堡人獨有的一種頭戴木刻假面的民間戲劇。這些人來自安徽、江蘇、江西、浙江、河南等地,他們把從內地帶來的戲劇形式與當地文化相融合,逐漸發展成為安順地戲。
據《續修安順府志》記載,地戲的由來與屯堡人的生存選擇有關:“當草萊開辟之后,人民習于安逸,積之既久,武事漸廢,太平豈能長保?識者憂之,于是乃有跳神戲之舉。借以演習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農之深意。”
“我們都是軍人的后裔,祖先都是征南人,永遠要記住精忠報國、忠孝仁義。”秦發忠說,“因為是軍人之戲,很多地戲講述的都是征戰之事,以歌頌精忠報國、尚武精神為主題。”
地戲不需要舞臺,在村野曠地就能進行演出,而且只演“正史”,不演龐雜劇目;只有武戲,沒有文戲。演出者首蒙青巾,腰圍戰裙,戴假面于額前,手執戈矛刀戟之屬,隨口而唱,應聲而舞。其演唱有弋陽老腔余韻,其舞主要表現征戰格斗的打殺,雄渾粗獷,古樸剛健。
安順地戲為研究戲劇發生學、人類學、宗教學、民俗學等學科不可多得的活材料。2006年,安順地戲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看著頭罩黑紗、戴著臉譜、手執兵器的人在臺上舞蹈,時光仿佛倒流了幾百年。
“特定的時代與特定的社會環境,使屯堡人區別于其他地區的漢族,也有別于當地的少數民族。”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朱偉華將屯堡定義為“大山與歷史深處的漢民族族群”,地戲是屯堡精神文化形態的重要載體。
儺雕產業背后的文化危機
“地戲演出時佩戴的面具,屯堡人稱其為‘臉子’。看過地戲的人都知道,沒有臉子就演不成地戲,所以臉子是安順屯堡地戲的核心載體。”秦發忠說,“臉子屬于儺面具藝術,更是安順地戲的重要載體。一個村寨要跳演地戲,首先要請雕匠制作面具。一面臉子的制作通常要經過下料、細雕刻、雕耳翅、彩畫、上光等15個流程。”

當年朱元璋“調北征南”,數十萬軍隊和家眷把從江淮等地帶來的戲劇形式與當地文化相融合,逐漸發展成為屯堡人獨有的一種頭戴木刻假面的民間戲劇。圖為安順屯堡地戲表演。(貴州圖片庫供圖)
秦發忠生在“儺雕之鄉”西秀區周官屯、長在屯堡村寨,一邊搞儺雕,一邊關注和收集與地戲有關的資料,長年累月與雕匠、地戲演員摸爬滾打在一起,既熟悉臉子雕刻的制作流程,也了解地戲演出的民俗儀式。
為了讓儺雕有一個展示的地方,秦發忠花了300多萬把自己家建成了安順市首座屯堡儺雕藝術博物館,館內擺放了數百個形態各異的儺雕面具,有安順地戲面具、仡佬族、苗族、彝族等民族的儺戲面具、陽戲面具、撮泰吉面具等等,既能讓群眾在這里參觀了解,也可以供學者研究學習。
“當初有人出資讓我把這個博物館建在北京,但我覺得本土的文化還是要在本地才有生命力。”秦發忠十分自豪地告訴記者:“儺雕的全稱是‘儺面具藝術雕刻’,這個名稱是我創立的,如今我帶出來的徒弟有600多人,還有兩個博士生和五個研究生跟著我學習。”
自豪的同時,秦發忠也在為儺雕技藝的未來感到擔憂:“隨著社會的發展,儺雕已發展成為貴州安順的支柱性文化產業,從事儺雕技藝的民間藝人達上千人。貌似繁榮,實則存在著嚴重危機。”
隨著“文革”中大批面具作品被焚燒殆盡和近年來一批老藝人的去世,依靠口傳身授的儺雕面臨著傳承乏力的嚴峻形勢。雖然目前有上千人從事屯堡儺雕藝術,但能掌握核心技藝者少之又少。盡管旅游帶動了當地儺雕產業的發展,卻很少有人關注面具背后所隱藏的文化符號和民俗寓意。
鄉村旅游助力地戲傳承
“這些臉子刻工精細而不繁瑣,寥寥數鑿,看似隨意刻畫,實則爛熟于胸。”秦發忠說,幾百年來,當地民間藝人以木為紙,以刀為筆,憑著精湛的雕刻技藝,制作出了一件件雄渾粗獷、神色各異的面具。
通過簡略的五官變化和花哨的裝飾,面具被賦予了生命活力,民間神話中的神靈、鬼怪及傳說中各類人物的豐富表情和鮮明性格,無不各盡其態,令人嘆為觀止。秦發忠告訴記者,每一個臉子都有一個故事,每一種臉子都是一種不同的跳法。如今儺雕的匠人雖多,但懂得其中文化內涵的人少,懂得地戲中每一個面具的跳法的更是少之又少。
儺雕和地戲相依為命,二者依靠的是手把手教學和口耳相傳,沒有公式,沒有曲譜,一旦傳承人消失,技藝和文化也將隨之消失。
家住安順市西秀區舊州鎮詹家屯的詹學彥是安順地戲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他9歲開始學習跳地戲,不僅多次參加本地舉辦的大型文化活動,還多次為德、美、英、法、日、韓等國友人表演。看上去雖然風光無限,但在詹學彥的眼里,卻透著淡淡的憂傷。
“再這樣下去,5年后、10年后,我們這班老者走了,安順地戲怕也就不復存在了。”詹學彥所擔心的,正是安順地戲不容樂觀的現狀。在多元型現代文化的沖擊下,地戲逐漸萎縮,演員年齡偏大且隊伍人數逐年減少。很多有地戲隊的村寨已停鑼息鼓多年沒有演出,保護這一古老劇種,已到刻不容緩之期。
近年來,安順市在儺雕技藝人才梯隊的培養上下足了功夫,集教育、研究、展示、銷售等為一體的儺雕傳習發展中心逐漸成立。但是秦發忠認為,還需要結合鄉村旅游的發展,形成產購銷一條龍服務,讓游客購買到富有深厚文化內涵的儺雕旅游商品。“只有這樣,才能讓有幾百年歷史的地戲面具世代傳承,保存一方文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