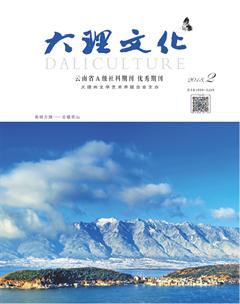閑幾硯中窺水淺
李樹華
在眾多描寫硯臺的詩句中,我最喜歡這句“閑幾硯中窺水淺”,它說的是在無事的時候觀察硯臺中水的深淺,由此很容易讓人想到人生的沉浮,想到歷史的起伏。我想不到小小的一方硯臺,競蘊含著無窮的哲理:更讓我意想不到的是,一方好硯竟然價值連城,硯臺的制作更是一門復雜的、需要代代相承的手藝。在云南省大理州洱源縣鳳羽鎮(zhèn)一個叫起鳳村的地方,生活著一位年近古稀的祖?zhèn)鞒幣_制作手藝的傳承人,他的名字叫段臻然。
一方硯臺傳家
“李老師,你是怎么找到我這里來的?”段臻然老師傅對我的突然來訪顯得有些吃驚。“我早就聽說你在1999年昆明世博會時代表當?shù)卣o世博園捐贈了一方價值近百萬的大硯臺。有這么一回事嗎?”我反過來問他。“有有有……不過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呵呵呵……”段臻然笑瞇瞇地回答我。“段老師傅,我對硯臺可是一竅不通,今天是專門來向你請教的。”我一臉真誠地對段臻然說道。“李老師,你謙虛了,我們互相學習嘛。”段臻然謙虛地應道。
說話之間,我對段臻然的采訪便在輕松的氣氛中開始了。
段臻然出生于1948年6月,屈指算來。到今年已有69歲了。可是從他身上,我卻看不出來歲月的痕跡,這讓我不禁想起了白居易《早夏游宴》中的詩句:“雖慵興猶在,雖老心猶健。”
段臻然告訴我,他的硯臺制作技藝是從父親段漢炳手上傳下來的,而父親的手藝又是從爺爺手上傳下來。“這么說,到你手上,已經傳了三代了?”我語氣肯定地問他。“不是,是四代了。因為到我爺爺?shù)臅r候就已經傳到第二代了。”段臻然笑著回答我,“我的兩個兒子也都從我手上傳承下來了。”如此算來,段家的硯臺制作手藝已傳承五代之久。
段臻然一邊喝茶,一邊和我閑聊。向我說起了他的過去。在家庭的熏陶下,段臻然從小就對雕刻產生了濃厚興趣。由于家庭貧困,小學畢業(yè)段臻然就跟著父親開始學起了硯臺制作,那一年他才14歲。在他小的時候,還沒有改革開放,大家都要通過參加生產隊的勞動,苦工分,所以家里人只能在農閑的時候制作硯臺。改革開放以后,國家政策好了,開始鼓勵群眾大膽經營,于是他們全家就發(fā)揮個人祖?zhèn)鞯奶亻L,放開手腳,搞起了家庭經營。那時候,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段家制作的硯臺都是拿到昆明去賣的。我好奇地詢問原因,段臻然解答道,那時在昆明有人幫忙代銷產品,不用自己跑,昆明工藝品美術公司和云南文物商店都在幫他們代銷產品:此外還直接銷售給來家中購買硯臺的人。
通過段臻然的講述,我深深體會到當初段家人以硯臺為生的苦中有樂的生活。由于那時的市場很不景氣,段家制作硯臺的收入很微薄。辛苦一年下來,也只能勉強維持全家人的日常生活開銷。當時村里農閑時節(jié)很多人家都要乘機做一些硯臺,三月街時好上街去賣,一方五六塊錢。如果哪一方賣了十塊,那就算賣上好價錢啦,因為當時勞動一天的工分,分到的錢還不足一塊錢。段臻然自豪地告訴我,在過去。他們家就靠著一方硯臺養(yǎng)家糊口,日子雖然艱難,可還算過得去。其實,在段臻然的青少年時期,他只知道靠制作硯臺過日子,并不懂其中包含的文化含義。
“只有到了改革開放以后,通過和許多文化人的交流。我才慢慢知道了這一方硯臺里面所包含的文化意義。”段臻然嘆道。我心想的確如此啊,當初為了養(yǎng)家糊口而制作硯臺,把硯臺當作一種謀生工具;而今日子好過了,也才有心思研究硯臺的文化內涵。
我欣賞著段臻然雕刻出的硯臺,被上面精妙絕倫的圖案深深吸引了,不禁問道:“段老師傅,我想知道你是怎樣在這么一塊石頭上雕刻出這么多栩栩如生的圖案來的?”“這個嘛,會者不難。我現(xiàn)在就做給你看看。這是第二次雕刻了,很快就會完工的。”段臻然一邊說一邊倚在木桌上,聚精會神地對案桌上已經初步完工的一方硯臺雕刻打磨起來。
我抬頭環(huán)顧段臻然的作坊,只見里面堆滿了石材、電線和各式刻刀、手錘。我注視著眼前這個老人,從他1962年開始接觸硯臺制作算起,竟然堅持了50多年,不由得在心里對他的這一份虔誠和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守暗自佩服起來。在這幾年的采訪中,我知道許多傳承人都有一股與眾不同的“倔脾氣”,他們一旦認定了做一件事,就是九頭牛也拉不回來,也許段臻然也是這樣的人吧。
也許是被我灼熱的目光吸引了,段臻然笑著說道:“李老師。我其實就是一個人們平常所說的‘匠人,在遇到困難時比較倔強罷了。”這句話把我的思緒一下子就拉了回來。說話之間,一方硯臺已在段臻然的手里完工了,他親手遞了過來。我小心地接過段臻然遞過來的硯臺,仔細地觀賞起來。生怕漏掉每一處細節(jié)。這是一方以“祥云”為主題的硯臺。上面雕刻著繚繞的祥云,宛如仙境,美不勝收。像這樣的硯臺,過去段臻然一個月至少要出一方。
段臻然告訴我,制硯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工藝,整個制作過程都離不開傳統(tǒng)文化。如梅蘭竹菊、祥云牡丹、龍騰起舞、福祿禎祥、龜賀壽年這些傳統(tǒng)圖紋飾都是石硯設計理念中經久不衰的主題。近年來,在《中國當代名硯鑒賞》《中國文房四寶》雜志和《鑒賞名家硯》中收錄及被名家收藏的高檔石硯中,主流作品仍是以傳統(tǒng)文化和民俗文化為主的作品。
在段臻然的制作理念中。他認為如果石材的硬度較軟,硯石顯空隙率就會小,硯石的礦物也細,石粒間間隙小,可以達到很好的發(fā)墨效果。反之,如果石材硬度較高,則比礦物較軟者稍粗,粒間間隙稍大,從而可以達到很好的下墨效果。下墨與發(fā)墨本身是矛盾體,好的硯質要恰好能夠調和矛盾,就是要細而不滑,澀而不粗。怪不得大文學家歐陽修在《硯譜》中評價:“歙萬出于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fā)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為貴,其石理微粗,以其手摩之,索索有鋒芒者尤佳。”
一張木桌,一盞臺燈。幾把刻刀,這便是段臻然制硯的全部工具。
讓我頗為震撼的是段臻然案上的那十多把刻刀。那些形似小鐵棒,直徑不到5毫米的刻刀,長度或長或短,刀鋒或尖或圓。這些沒有任何花紋雕飾,樸實無華的小刀,卻可以變換出深刀、淺刀、斜刀和細刻、線刻、縷空這些絢麗的雕法,讓人嘆為觀止。行云流水、刀走龍蛇,一方方價值不菲的硯臺就在制硯師傅手中誕生。盡管如此,一個刀功了得的老師傅,一個月也就出品一方硯臺而已。
在大理,最集中的石硯制作地位于鳳羽鎮(zhèn)的起鳳村,這是一個以農耕為主的傳統(tǒng)村落。“以前我們這個村子里有五六家人在制作硯臺,現(xiàn)在只有我們家和旁邊的楊世昌家了,可惜楊老師傅不久前逝世了,還好他兒子傳承了他的工藝。”說到這里,段臻然臉上有些茫然。“是啊,許多人想不到,在這個偏僻的地方,竟然會有人做硯臺。這也說明我們大理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文化名邦。”我感嘆地說道。
精雕細琢施藝
通過采訪,我也大致熟悉了制硯的工序和細節(jié)。從選料、維料、開璞、設計,到雕刻、打磨、洗滌、過蠟、配盒,一方硯臺的出品總共需要12道十分復雜的手工制作工序。如此精細的手藝活還考驗眼力,為了保證光線充足,制硯臺一般要放在有充足光源的窗邊,每張桌子上還要配備一盞臺燈。
通過段臻然的詳細介紹,我得知硯臺制作的第一步是采石。采石時往往只能蹲著、坐著或斜躺著采石,所用開采工具按石材所處環(huán)境而制。硯石是硯臺制作的基礎,坑洞不同,硯石的石質會有很大差別,起鳳村使用的硯石自古以來都用手工開采。在開采中,要看清石壁,根據(jù)石脈走向去尋找石源。在山上采石只是粗選,而第二道工序則是細選,去粗留精,去除硯石表面的瑕疵、裂痕和廢料,剩下適合制硯的“石肉”。選料的人要懂石,只有發(fā)現(xiàn)好的石品花紋,才能將硯石制成硯胚。接下來就是設計,這個環(huán)節(jié)可以說是將硯升華為一種綜合性藝術品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拿到硯石后,要先設計后雕刻。設計的目的是將硯石中的瑕疵變成無瑕,以達到錦上添花的目的,增加其藝術價值。除了傳統(tǒng)硯形硯式外,還要充分利用天然石皮,匯集文學、歷史、繪畫、書法、金石于一體,才能制成一件構型巧妙的硯臺工藝品。
除了上述工藝以外,還有雕刻、磨光和配盒。雕刻是制作過程中一道很重要的工序。要使一塊天然樸實的硯石,成為一件精美的工藝品。需要認真設計和雕刻。這個過程處理得當可以說是錦上添花。但如果處理不當就會畫蛇添足。所以雕刻藝人要因材施藝,因石構圖,還要根據(jù)璞的石質,去粗存精,認真構思,并考慮題材、立意、形制以及雕刻技法,如刀法、刀路。雕刻工具則因硯石的硬度、雕刻的技巧和題材需要而制。20世紀70年代前,這些工具多由采石工或硯匠自制。采石工具主要包括粗細不等的尖口鐵鑿、鐵筆、鐵錘、炮鑿及燈等,雕刻工具主要包括錘、鑿、鑿卡、木鉆、鋸、滑石及工夫臺等。雕刻要線條清晰。玲瓏浮現(xiàn)。一目了然。雕刻主要有高深雕的“深刀”雕刻和低浮雕的“淺刀”雕刻。還有細刻、線刻,適當?shù)溺U空通雕。采用什么雕刻技法和刀法,要看題材和硯形、硯式而定。如要表現(xiàn)剛健豪放的,多以深刀雕刻為主,適當穿插淺刀雕刻和細刻,要表現(xiàn)精致古樸,細膩含蓄的,則以淺刀雕刻,細刻、線刻為主。總之,細刻和線刻都屬于精巧部分,細刻要求雕刻精細、準確、生動,線刻則要線條細膩、流暢,繁而不亂,繁簡得當。
最后還有磨光。首先要粗磨,磨去鑿口和刀路,然后再用滑石、幼砂紙反復細磨到手感光滑為止。有些硯臺要染墨,隔一天后再退墨,另外還要上蠟。過后又要退蠟。最后還要配盒。也就是說,在制好以后,還要配備木盒,硯盒可以保護硯臺,它自身也是一件藝術品,可以使硯臺顯得更加古樸凝重。
在交談中,段臻然還告訴我一個“秘密”。他對我說,品鑒硯石的品質其實是有一番講究的。簡單說就是。一靠“摸”,二看“品”。如果摸上去細膩、溫潤如玉者為上品。“如秋雨乍晴,蔚藍無際”的是天青;“白如晴云,吹之欲散”的是魚腦凍;“凈嫩如柔肌,如凝脂”的是蕉葉白;“如細塵掩明鏡”的是青花,以及珍稀的石眼、金銀線等,如果擁有這些石品就可堪稱硯石中的極品。
在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中。段臻然通過大膽創(chuàng)新,將雕刻和雕塑有機結合,打造出了極具特色的庭院景觀藝術。硯臺所代表的硯文化,溯古通今,源遠流長,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化產生、發(fā)展、傳承的重要載體,更是促進中國文化傳播、交流和發(fā)展的重要工具。這輩子讓他最驕傲的作品就是1999年捐贈給昆明世博園的那一方大硯臺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段臻然想到要給昆明世博園捐贈代表大理傳統(tǒng)文化的作品,想來想去,他覺得還是硯臺比較合適。主意一定,他便帶著幾個徒弟辛辛苦苦干了幾個月,終于把一方長1米,寬0.9米的大硯臺給做出來了,為家鄉(xiāng)洱源,為大理,甚至為國家爭了一口氣。如今,這一方大硯臺還靜靜地立在世博園的綜合展館中,而誰又能想到,這一方大硯臺竟然出自云南大理洱源小山村里的一個祖?zhèn)鞒幣_制作的世家。
在起鳳村,今年69歲的段臻然在人們眼中看起來一點都不顯老。作為有著精湛技藝的老匠人,在談到技藝傳承時,他不免有些憂心:“做這行一定要能吃苦。”他告訴我,幾十年來,前前后后有近百人來找他學藝,但堅持下來的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幾人。在他的徒弟中,讓他最為得意的是紅河州有一個叫李紹學的徒弟。“這個徒弟跟著我學了3年,本來就是紅河州美術學校畢業(yè)的,有扎實的基礎,所以很快就出師了,現(xiàn)在已經小有名氣了。”說到這里,段臻然有些欣喜。他跟我說:“不能讓石雕技術失傳,否則就太可惜了。除了傳統(tǒng)的‘師傅帶徒弟,還有其他辦法嗎?這幾年,我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段臻然認為,盡管硯臺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收藏價值和人文價值,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機械生產沖擊著手工制硯和傳統(tǒng)技藝的傳承方式,導致工匠后繼乏人,只有認真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切實保護和延續(xù)傳統(tǒng)硯臺制作技藝,讓古老的制硯技藝散發(fā)生機。
說到技藝的傳承,段臻然告訴我,盡管他的兩個兒子都已經參加工作,但在工作之余,他們還是傾心投入祖?zhèn)鞯某幣_制作工藝,使這一門技藝得以傳承下來,這讓他感到很欣慰。“不僅是我的兩個兒子。就是我老伴,也是一個制作硯品的高手呢,呵呵呵……”段臻然笑瞇瞇地對我說。
我從段臻然口中得知。50年多年來。他帶領妻子、兒子在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道路上不斷前行,開發(fā)出了上百種的硯系列產品,開拓了更廣闊的市場。同時,他致力于傳承弘揚歷史文化,注重打造文化產業(yè)新品牌,使“鳳羽硯”這一傳統(tǒng)歷史文化產品歷久彌新,美名遠揚,客觀上也填補了大理硯臺生產的一大空白。
段臻然對我說:“50多年來,從學徒到師父,我前后收過近百名徒弟,四個兒女都會制硯。我們‘鳳硯坊所制作的硯臺先后獲得過‘金花獎“少數(shù)民族創(chuàng)意旅游商品大賽金獎等獎項,作坊一年制硯兩三百方,喜歡的人都會找到村子里來買。一方硯臺,價格低的在上百塊錢,高的在上千塊錢甚至更高。”
據(jù)了解。除了段臻然。起鳳村中還有五六戶人家在制硯,較有規(guī)模的有楊躍堂和楊世昌家,但只有楊世昌和段臻然是“鳳羽硯”的省級傳承人。
民族密碼傳承
一塊石頭,經過段臻然之手。竟然能夠以文脈傳世,讓我不得不驚奇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傳承的密碼所在。
段臻然出生于歷史悠久的大理洱源鳳羽白族古鎮(zhèn)。從西漢開始。鳳羽就是著名的古南方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古代云南的主要產鹽地云龍五井的食鹽絕大部分都是經過鳳羽運往省外及東南亞各國,許多外來文化也通過鳳羽向四方傳播。在幾千年的風雨歲月中。因地處交通要道,位置險峻,鳳羽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一直都十分發(fā)達,在滇西地區(qū)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唐南詔時,鳳羽設過縣,宋大理國時改設鳳羽郡,明洪武年間又設巡檢司。直至今日,這里一直都是滇西有名的四大鄉(xiāng)村商品集散地之一。相傳鳳羽這一鎮(zhèn)名即因“鳳轂于此,百鳥集吊,羽化而成”而得名。當年徐霞客路經鳳羽時曾駐足7日,使之成為其行程中停留時間較長的地方。由于地理位置的優(yōu)越,商品經濟和文化的發(fā)達,明、清、民國時期,鳳羽建起了許多極富特點的民宅,一躍成為繼喜洲之后,全國第二大白族建筑群。目前全鎮(zhèn)保留有完整的白族民居一千多幢,年代最遠的可溯及明朝。
據(jù)段臻然介紹,鳳羽硯的取材非常講究,一般都要用鳥吊山北麓的硯石。北麓背陰,硯料質地柔軟、細膩、水分飽和度高,寫出來的字有自然的光澤,歷久不變。在硯中倒上墨,合上硯蓋,可保數(shù)月不干。硯石黑色,紋理清晰,質地細膩,均為純手工雕刻,雕刻講究,制作精細,造型別致。
鳳羽硯石是制作硯臺的上好的特殊石料,其石質細膩,硯石黑色,條理順直,有溫潤似“壽山”,細膩如“田黃”之稱。其制作的硯臺產品。在使用中,冬不結霜,夏不蒸發(fā),無異味,四季保水又易于研墨。年輕的白族硯石匠師張躍康是制硯名家楊世昌的兒子。據(jù)他介紹,硯石鳳羽硯的雕鑿已有300多年的歷史,制硯是楊家的祖?zhèn)鳟a業(yè),相傳在清朝順治年間,洱源縣鳳羽村人楊必登發(fā)現(xiàn)了鳳羽硯硯石,并將其雕鑿成硯臺,作為貢品進貢。
1998年,段臻然牽頭籌建了云南洱源縣鳳羽硯臺工藝品廠,用工22人,專門從事鳳羽硯臺的制作生產,實現(xiàn)年產硯臺近千方,產品供不應求。這一年,他正好50歲。2002年,鑒于段臻然在制硯技藝方面的傳承和所取得的成就,他被云南省文化廳授予“云南工藝美術大師”稱號。2005年,他雕刻設計的硯臺“龍鳳呈祥”獲大理州旅游工藝品創(chuàng)作設計大賽銅獎。2011年,他的“白菜硯”獲云南工藝美術“512美杯”銀獎。2013年,他的“深山尋隱”硯臺獲“云南省工藝美術精品銀獎”。
硯臺雖小名氣大。鳳羽硯臺已有300多年的加工歷史,因石料質地好,加工工藝好,有濃厚的傳統(tǒng)文化含量,進入市場以來供不應求。但由于主要以家庭作坊式生產加工為主,生產規(guī)模小,所以客觀來說,對地方經濟社會的貢獻不十分明顯。為進一步擴大鳳羽硯系列文化旅游產品的生產,近年來,當?shù)卣當M在原有硯臺家庭小作坊生產的基礎上,通過統(tǒng)一選址、統(tǒng)一規(guī)劃,建設新的硯臺加工區(qū),加強人才培養(yǎng),購進先進設備,擴大鳳羽硯臺的加工生產規(guī)模,推動硯臺產業(yè)規(guī)模化發(fā)展。
在和段臻然的交談中。我一直在想這樣一個問題:在世界歷史長河中,沒有哪一個民族的文化像中華民族的文化那樣同書寫工具有著密切的關系,也沒有哪一個民族的文人像中國古代的文人那樣把自己的書具視如自己的生命和密友。中國文人用“文房四寶”來傳達自己的思想、文化、生活和感情,成就了不朽的千秋事業(yè)。無法想象如果沒有書寫工具,中國古代藝術將會是怎樣的面目,眾多光輝燦爛的典籍將會以怎樣的形式流傳,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將會怎樣表現(xiàn)自己的儒雅。硯文化對于傳承中華文明,對于表達中國古代人文思想,對于呈現(xiàn)中國古代社會生活歷史場景,都具有重要的歷史作用,因此,是不是也可以說,硯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xù)和傳承的重要載體,硯文化是中華文明得以豐富多彩的重要原因。
事后我通過查閱資料,對硯文化的了解也進一步加深了。
我國硯文化的硯,是從研墨器發(fā)展而來。其源流可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仰韶文化初期出現(xiàn)的原始形態(tài)硯臺,問世至今已有五六千年歷史。硯文化最早表現(xiàn)為硯器文化。由此可見中國硯文化是源遠流長的,肇始于中華文化的源頭。從東漢到唐宋時期形成了硯文化的高峰。明清時期也有特色,20世紀80年代以后又出現(xiàn)了高峰。作為我國傳統(tǒng)的書寫繪畫器具之一的硯,對傳播文化藝術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歷代文人把它和筆、墨、紙合稱為“文房四寶”。1975年,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國早期墓中,發(fā)現(xiàn)石硯、研石、墨及木牘等隨葬品,這是現(xiàn)在已知的我國歷史上最早的“書寫硯”,距今約2300年。戰(zhàn)國至秦代,硯形較原始簡單,無雕刻紋飾,僅為一粗糙圓形石盤,至此,石硯的生產便開始發(fā)展。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制硯工藝得到了很快恢復和發(fā)展。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推陳出新,使失傳的硯品得到恢復,同時開發(fā)出不少新品種,制硯工藝也日臻完美。專著論文不斷涌現(xiàn),如程明銘的《中國歙硯研究》,劉演良的《端溪硯》,孫敦秀的《文房四寶手冊》,趙松齡的《硯石》,蔡鴻茹、胡中泰的《中國名硯鑒賞》,羅春明等人著的《中國苴卻硯》,霍有光的《宋代硯石文獻的地學價值》,傅才生的《中國天然石硯概況》等等,不勝枚舉,這些專著、文獻為繁榮中國硯石文化,做出了貢獻。
硯文化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占據(jù)著重要的位置。自隋唐以來,硯文化就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對外交流的一種重要工具,承載著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使命。在歷次的對外交往中,中華硯文化都隨著我們的船只漂洋過海,遠赴異國,曾經獲得歐洲宮廷和日本上層社會人士的最大青睞,受到各國貴族和人士的廣泛歡迎。在中華大地上,每一次外國使節(jié)來華覲見、通商、游歷,中國最高統(tǒng)治者的御賜之物中都有“文房四寶”。通過外國使節(jié)和中國使節(jié)的交流,這些中國文人最為心愛之物也傳播到了世界各地,成為中華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代表,成為中華文化對外宣傳和展示的最佳選擇,這無疑是對中華文明的傳播。
硯文化的重要性也讓我意識到學會鑒別硯臺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在許多外行人眼里,好像每一方硯臺,除了上面的圖案不同以外,都是一樣的。于是我趁機詢問段臻然硯臺的鑒別方法。段老微笑著向我詳細講了鑒別過程,我再通過查閱相關資料,對硯臺的鑒別也有了自己的心得體會。
首先是“看”。也就是看硯的質、工、品、銘、飾與新舊、是否經過修補等。如果硯已經修補過,補過地方的顏色與硯的原色總會有差別。然后是“摸”。拿到一方硯,可以用手摸一摸。如果摸起來感覺像小孩皮膚一樣光滑細嫩,說明石質較好。如果摸上去有粗糙的感覺,說明其石質較差。還有就是“敲”。也就是把硯面用五指托空。輕輕擊打,或用手指彈,聽它的聲音。若為好硯,以木聲為好,其次是瓦聲,然后是金聲,這三種不同的聲音,分別體現(xiàn)出硯石質的嫩與老。如果敲打后發(fā)出清脆的“鐺、鐺”金屬聲為最好。如果聲音為“噗、噗”就說明多泥質,或石質有暗傷痕,為下品。還有就是“洗”和“掂”。最好要經過清洗,尤其是古硯因硯面上墨痕斑斑,遮掩了硯的自然美紋,也分辨不清石的坑口年代,因此需要洗掉硯的墨痕,看硯石是否有傷痕和修補過的痕跡。“掂”就是用手掂硯的分量。同樣大小的石硯,一般來說重的硯石膠結緊,顆粒細,輕的說明膠結松。掂的方法尤其對歙硯比較適用。除了“洗”和“掂”以外,就是“刻”了。一方硯的好與差,首先考慮的是石質的好壞。對于熟悉硯石的人,只要用力在硯石上輕輕地刻上幾道,馬上就會感覺出硯石的優(yōu)與劣。
對普通硯臺的鑒別尚且如此復雜,對名硯的鑒定更加是一門復雜的學問。通過這次采訪,我對收藏硯臺的興趣也大大增加了。一般人都把四大名硯。也就是唐代的端硯、歙硯,東晉的澄泥硯,宋代的洮河硯作為收藏的重點。但硯臺種類繁復,造型各異。怎樣才能正確鑒定它的收藏和投資價值呢?第一個就是材質。名硯比一般硯的材質好,價格總是比一般的硯來得高。另外。硯臺的雕刻工藝,也是決定硯臺收藏價值的重要因素。此外,硯臺的造型品相,也是一個價值的參考點,一般來說,方型、圓型的硯臺要比品相不規(guī)則的硯臺價格貴得多。俗話說,“硯貴有名,身價倍增”,指的就是硯臺上面的銘文。當然,硯臺的收藏價值應當從多個方面去綜合考慮。
此外,如何收藏硯臺也是各位“硯迷”需要思考的問題,在這方面,家中藏硯不少的段老也有一套系統(tǒng)的收藏方法。首先要注意避光。如果把硯放在窗前案頭,要避免太陽光直射。不然硯質就會出現(xiàn)干燥的跡象,如果曬久了,硯匣也容易干裂。玩賞硯臺時。桌上最好鋪上毛氈,不要讓硯接觸金屬和玻璃等器物,更不可以把硯重疊放置,以防碰傷。在對硯臺涂蠟時,有人經常將蠟涂遍硯身,有的還涂抹植物油,更有的涂抹墨,以為可以養(yǎng)硯,但其實這些做法并不妥當。蠟可以涂于硯的四周,但底部要薄而適中。最忌將蠟涂在硯堂磨墨的部分。硯上抹植物油的做法也是不妥的,因為植物油屬慢干性油脂,硯面有油多招塵土,使硯污穢不堪,并散發(fā)出一種怪味或產生霉變。在硯匣保養(yǎng)時,要經常打蠟以保持硯匣光澤,防止潮氣侵入。如果遇到硯匣收縮,硯身放不下的情況,可用砂紙打磨硯匣的內側,讓它增寬易放。古硯匣如有破爛和損壞。可采用匣外配匣的方法對古硯匣進行收藏。
隨著采訪的深入,我對硯臺的了解也越多,私下對硯臺的研究也越為廣泛。硯文化是一門博大精深的文化,當你一步步走近硯文化,就會發(fā)現(xiàn)里面的東西越來越復雜精妙。整個人宛如身處“霧失樓臺,月迷津渡”的環(huán)境,顯得很迷茫。“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山中”,正如段臻然所說,說到底,硯臺的實用功能還是磨墨。我們需要回歸到事物的本初,才能認識它最為重要的價值。硯臺最初的功能就是一件書寫工具。衡量其好壞的重要標準,還是墨。下墨、發(fā)墨是衡量硯材好壞的重要指標之一,簡單說,下墨,是通過研磨,墨從墨塊下到硯臺上的速度。發(fā)墨,是指墨中的碳分子和水分子融合的速度、細膩程度。下墨講求的是快慢,發(fā)墨講求的是粗細,但往往下墨快的發(fā)墨粗,發(fā)墨好的下墨慢。所以,下墨發(fā)墨均佳的硯就顯得極其珍貴。
段臻然的大兒子段志明同樣對硯臺有著深入的了解,他向我介紹說:“我們鳳羽硯臺就是那種下墨發(fā)墨都很好的硯臺,還曾經被《中國書畫報》作為名硯介紹,可與中國四大名硯相媲美呢!”緊接著,段志明還向我介紹了鳳羽硯臺的優(yōu)點。通過他的介紹,我了解到,鳳羽硯臺因為石材細膩、品質優(yōu)良,又集實用性、藝術性和鮮明的民族工藝特色為一體,所以具有易于磨墨,光澤深沉,涵養(yǎng)水分,硯蓋凝珠,有墨不腐,磨出來的墨汁流利錚亮等優(yōu)點。在造型上,鳳羽硯臺造型獨特,圖案生動活潑,精致典雅。款式新穎,深得民間傳統(tǒng)藝術之精髓。近年來,隨著生產規(guī)模的擴大,工藝水平的提高,鳳羽制硯名匠在汲取傳統(tǒng)工藝精華的基礎上,增加了八仙過海、龍鳳呈祥、雙鳳朝陽、二龍戲珠、李白斗酒、喜鵲登梅、三羊開泰、唐僧取經、牧歸硯、葡萄硯、竹節(jié)硯等30多個品種。硯臺也采用紫木雕方盒或錦緞方盒包裝。具有大方古樸的濃郁文化氣息。
正是由于鳳羽硯臺的諸多優(yōu)點,因此具有比較高的觀賞價值、實用價值、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躋身于全國硯臺之列,產品多次參加昆交會、昆明旅游商品展銷會和省內文化產業(yè)博覽會等,受到國內外書畫愛好者和收藏家的喜愛。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和旅游業(yè)的蓬勃興旺,具有很高實用價值與工藝欣賞價值的鳳羽硯臺,已經逐漸成為文化、藝術、旅游等領域中的暢銷產品,也成為節(jié)日紀念的最佳選擇和饋贈親友的高雅禮品。
我認為這次采訪收獲頗豐,不僅了解了很多關于硯臺的實用知識,還被段臻然老先生用心于制硯臺。博學于硯文化的精神所折服。相信通過我對段老的采訪,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對“鳳羽硯”和硯文化有所了解,有所喜愛。
“年去年來來去忙,春寒煙暝渡瀟湘。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揀杏梁。閑幾硯中窺水淺,落花徑里得泥香。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在離開段臻然家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我又一次想起了唐朝末期著名詩人鄭谷這首名為《燕》的古詩。硯臺不僅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家中必備之品,也是古詩詞中常見的意象。從這首表現(xiàn)古代士大夫閑情逸致的詩歌中,我們不難看出硯臺是一種高雅文化品位的象征。
硯文化也是中華文化對外傳播交流的重要工具,但隨著時代科技的發(fā)展,硯作為日用文具早已退出歷史舞臺,新的書寫工具早已取代了這一古代文具的實用價值。硯文化的社會歷史空間也已悄然轉換,就如許多傳統(tǒng)文化一樣,已離我們漸行漸遠。但硯文化帶給人們的雅趣,不僅可以讓人“發(fā)思古之幽情”,也可以令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沉下心來,心如止水,在墨香四溢中清靜人的心境。因此。我們更要珍視古老而極為文雅的硯文化,保護硯文化,推廣硯文化!
編輯手記:
在古代,硯臺是主要的書寫工具之一。是將文化以文字方式傳承下來的重要載體;而在今天,硯臺成為了一種集實用性、觀賞性和文化性于一體的藝術收藏品,不僅硯臺本身蘊含著傳統(tǒng)文化里美好的寓意,而且硯臺已成為一種高雅品味的象征。大理的洱源鳳羽出產質量上乘的硯石,再加上當?shù)厥炙嚲康闹瞥幷摺!傍P羽硯”因此名聲在外。在鳳羽鎮(zhèn)一個叫起鳳村的地方,有一戶世代傳承制作“風羽硯”的人家,本期的主人公段臻然就是這戶人家的當家人。一方小小的硯臺,凝結了段家五代手藝人的心血。段臻然從十四歲就開始學習制作硯臺,至今已有五十多年,段老先生不僅僅是在打磨著一塊小小的硯石,也是在打磨歲月,打磨自己對傳統(tǒng)手藝的“匠心”。對段老而言,一方“鳳羽硯”,既是艱苦歲月的寫照。也是傳統(tǒng)文化的象征。制硯不僅是一門供匠人養(yǎng)家糊口的手藝,更是一門與傳統(tǒng)文化息息相關的手藝。通過段老的雙手,這一門古老而傳統(tǒng)的手藝在得以延續(xù)的同時,傳統(tǒng)文化也在悄然留存。通過閱讀本期主人公段臻然的制硯故事和他對硯臺的解讀、介紹,我們將會對“鳳羽硯”有著一個更為清晰、深刻和全面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