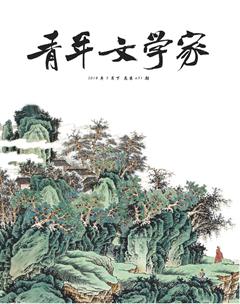根
張孟蝶
每個郁郁蔥蔥的,或搖曳扶疏的,自由伸展的,或纏綿攀爬的植株,都會有個沉默而堅韌的根,這是毋庸置疑的。一個植株,被頑皮而尚不懂珍惜的孩童摘取了妍麗清香的花朵,被貪婪饕餮永不飽足的昆蟲蠶食肥厚多汁的葉,甚至被狂風或重壓摧殘了挺拔向上的莖,被鳥獸不懂珍惜地截去甜美潤澤的果子,它依然還是可以成活的。生命就是如此的堅韌,任爾東南西北風,立根原在破巖中!
根卻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植株如果失去了根,那才真的有了性命之憂。所以許多影視作品每次為了表現奸佞壞人的殺人如麻,都會給壞人配上這樣的臺詞:“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然后將人家滿門抄斬不留一個活口,因此可見,人們對于根的重要性的認識還是十分深刻的。
說起根來,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在我的童年,城市化已經非常普遍了,水草豐茂可以拿著小水桶撈小魚蝦的小水塘被水泥抹平,樹木蔥蘢時見松鼠小鳥的小山坡被機械鏟掉建成了一個小工廠,草坪被水泥圈起來,樹也只能見到標準化的枝細葉少的行道樹,唯有馬路水泥或磚的縫隙下不甘心地執著長出地野草,還給城市一點野性的綠意。
“陰歷三月三,薺菜煮雞蛋”,我的家鄉有這個傳統。于是每到快陰歷三月三,我就要去家里四周的綠地摘取薺菜,那小小的心形的葉子,羞澀的幾不可見的白色小花,從一些蔥郁的寬厚大葉開著紫色黃色的美艷的花朵的植株中選取那清香的薺菜,我小心地攏住了所有的枝葉,控制著力道,挖著泥土,連根一起拔起薺菜,將一大捧薺菜抱回家,洗清泥土,加水煮起來。直到煮出綠綠的清香的菜汁,將雞蛋煮進去,小火煮幾個小時,直到雞蛋剝開的嫩嫩白色都染上淡綠,那種趁熱入口的清香襲人就不用說了。
在薺菜的生涯里,最美麗的是碎若繁星的白色小花,最實用的是量多細小的心形的葉,然而在美食屆,煮出來最香的地方還是根,仿佛所有的味道都濃縮在了那深沉又沉默埋頭向下的根。你看這根是多么奇妙,小時候看過許多稱贊根低調、沉默、默默奉獻、不慕名利等等品質的,雖然從道理上我是認同這些品質的,然而只有真正撥開泥土拔出根來仔細去觀察它、觸摸它,甚至品嘗它,你才能知道它有多么可貴,千言萬語都難以形容的可貴。
可惜的是,家周圍的綠地終究是越來越少了,于是這些年來,每年三月三捧回的薺菜從兩手難以合抱,到這幾年幾乎只能拿到寥寥兩三支,興許我的下一代就不能再見到薺菜了,三月三傳統的漸漸沒落,未嘗不是缺少薺菜的原因。
這個世紀80年代,尋根文學一時蔚為大觀,眾多作家都開始不遺余力地描繪故土,尤其是小村小鎮山間水鄉,那種朦朧的野性的自由又淳樸的蒙昧故土,是許多人午夜夢回里深刻入骨揮之不去的記憶。
如果追根究底,我的故土是在湖南的一個鄉下的村里,然而我從小到大從未在那里居住過,可是即使這樣,那個地方也在我家的長輩口中常常出現。
每每晚飯后,外公都會抽起一根飯后煙,然后瞇縫著皺紋深刻的眼,開始絮絮叨叨顛三倒四地說起那遙遠的只存在于記憶里的那些年,和那些年的故土。
外公小時候家里非常窮,家里孩子也生得多,沒辦法,只能供一個人上學,于是老張家想出了一個在那個情況下既公平又富有智慧的辦法:一家的孩子輪流去上學學幾天,誰成績好就誰去上學。在當時還懵懵懂懂的年齡,一次小小的測驗就決定了他們幾兄弟的一生,我的外公也許是早慧,竟然真的認真讀書,在老張家的測驗中拔了頭籌,在那個年代他的兄弟們就都去干體力活,一家來干活供養了我外公這么一個讀書人。
于是我的外公在兄弟們羨慕地眼光中,每天翻過四座山,去上小學。是的,天還沒亮,四點多就要起床,背上幾個粗饅頭,將鞋子脫下拿在手中拎著,翻過四座山。至于為什么脫鞋,是因為每日翻越四座山讓鞋子壞得異常快,家里甚至擔負不起買新鞋子的錢,以至于外公為了保住能去上學,將學費錢攢出來,不得不每每拎鞋翻山,乃至冬天也是如此。
說起翻四座山的事,外公常是興致勃勃,意圖讓我明白學習機會的珍貴。那些年,外公要翻過的四座山上有老虎,于是外公上下學的路上常聽虎嘯聲聲,外公每每害怕,老外公(外公的父親,家鄉的說法)就在家外的山坡上對著一望綿延的四座山峰,大聲喊著外公的小名,村里傳說,有人呼喊小名時,老虎就不會帶走那個人的魂魄。這也許只是農民沒有辦法下的心理安慰,然而幸運的是,外公就靠著這一聲聲大聲的呼喚,有驚無險地走過了他的小學時光。
那些年的家里還種了些蒜來補貼生計。外公直到現在還很喜歡吃蒜,每頓飯必配兩瓣蒜,生嚼。而外公的大蒜情結也和故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有一年家里特別困難,外公的學費就只能指望家里種的一點兒蒜了,于是全家悉心伺候著那蒜,希望能賣出好一點兒的價,在交了學費之后還能略有盈余。可是在交學費的前幾天的某一個夜里,這個村里的貧窮讓人忍不住滋生罪惡,有人一夜之間將外公家成熟的蒜全拔光了,第二日起來老外公長吁短嘆,最后實在沒辦法,去借了些錢又節衣縮食,將學費湊齊。
那些年,村里就那么幾個人,大家都忍饑挨餓,雖然不知道那些蒜最后被誰偷走,可是也許那些蒜在那時艱苦的歲月里免了某家一家餓死的命運,讓饑餓到過不下去的農民又挺過了一段艱辛的日子。那些年的故土,大抵就是如此。
十分幸運的是,外公作為老張家唯一讀了書的人,后來學醫了,又去軍隊里當了幾年兵,總算就業是不錯的,留在了城里的大醫院,每個月開始有了一些余錢接濟家里。
有一年,外公從部隊回家去,回到村里,村民們對穿著軍裝的外公都戰戰兢兢,在封閉的村里,對于某些有著權力象征的制服還是保持著封建的敬畏。而那些年部隊發給外公每個月的錢,外公只留下零頭,剩下的都寄回老家,也許是為了感恩家中全家努力供養他讀書,夜襲僅僅是因為純孝體貼家里,然而結果就是那些年的家里兄弟們都順利娶了媳婦,蓋了房子,老張家終于開始擺脫溫飽線上掙扎的命運。
到了我媽媽的時候,就已經住在城里了,可是我媽媽對村里的親戚還是十分熟悉。這固然是因為在我媽媽的童年,村里的親戚來我家做客是十分頻繁,也許是因為老家中的親戚也開始感受到了城市化的進程,開始迷戀于城里那鋼筋水泥、五光十色的繁華;也許是來我家可以捎一些城里的東西帶回鄉里,四處炫耀抑或度過家中艱難的日子,那些歲月家中親朋高坐,喧嘩不息,親情和物資在城里與村里流淌,帶著來來往往的寒暄,親熱又客套、熟絡又疏離,不知那些年我們究竟是滋養了哺育外公的根,還是過于急躁地催熟了原本自然生長的根。
然而不管怎樣,日子還是一天天過去,我的媽媽也隨著歲月從小女孩漸漸長成了一位成熟的事業女性、一位堅忍的母親,她也保持著每年回村去探親尋根的習慣,雖然已經沒有了外公那一輩那樣肉貼著肉的難以撕裂的熾烈親情和對于村子一家人養出一位讀書人的那種艱辛年代的別樣刻骨銘心的感恩,可是還是有些那份難以訴之于口卻在骨血中流淌的對根的眷戀。
到了我這一輩,村里的記憶只剩下“落葉歸根”這四個字。于我來說,村里的親戚大都面目模糊,名姓也常常記不清,即使親戚之間是以叔伯嬸姨等的親屬稱謂來叫,也還是生疏到我認不清那在我眼里相似的面目和繁多的稱謂。
那個有著小山坡的村子漸漸有了城鄉結合部的味道,而村里以前老家附近的小山就是我家的祖墳所在地,外公曾經用整整好幾個小時向我論述這塊山地是多么的風水寶地,多么的福澤后世,其中還夾雜著我聽不懂而外公其實自己也不怎么了解的易經、爻卦、五行方位等,我也有幸去過那神圣的地方拜祭過幾次。
帶上給親戚們的小特產,我和外公在家門口包下一輛出租車,然后在車上搖晃四五個小時,坐到村里,然后在村口見到一群咧開大嘴熱情得搓著手的親戚,吃過一頓農家特色淳樸而美味的午飯,我們就一步一步拔草攀枝地爬上小山坡。半山腰有一塊平地,老外公就葬在那里,墓碑的旁邊,各色由外公親手種植的種種花木環繞這墓,眾星拱月地拱衛著老外公的墳。
于是虔誠地向祖先禱告,然后上香,看著在山風吹拂下燃燒的香的煙霧向著山頂蜿蜒地飄上去,外公于是激動地說,這就代表我的心愿被祖上聽見了,于是又一次虔誠地感謝祖上。
外公帶我在這座山中又走了一會,便指著另一處明顯有人工痕跡的平地說道:“百年之后,我就葬在這里,到時候也像老外公一樣保佑你”。
這些年來,隨著村子的步步城鎮化,青山綠水漸少,本分的種地農民也漸少,正如許多小城市的人北漂、上漂一樣,村民們也向往著城市,他們很多去往附近的城市打工乃至于其中的佼佼者能做到定居在城市里,于是即使是回老家探親也往往有許多親戚是看不到的,那些年人數龐大的親戚,終究像蒲公英一樣,成熟、開出美麗的白色絨花,然后在現實的風中吹散到各處,在其他的富庶城市安享繁華,或在其他艱苦的地方將汗水像錘子一樣重重砸進泥土、又或是做其他人口里的不思進取之人仿佛一顆釘子扎住故土,此生都再沒見過任何其他風景。我和親戚們的感情也就不知不覺漸漸淡薄,也許再有幾代,就會徹底形同陌路。
因此我和老家的印象更多的是和墓聯系在了一起,那樣山清水秀的山上葬著老外公,以后也會葬著外公,也許那里還有許多更遠的祖輩,他們的一輩子都生在那里、長在那里、勞作在那里、娶親在那里、繁衍在那里、最后落葉歸根葬在那里,這種人與故土之間的關系真的就仿佛是植株與根一樣,離不開、斬不斷、終生的糾纏在一起,故土、故人,就像一種命運。
可是我覺得自己卻像是沒有根的人,浮萍抑或候鳥,已經沒有了扯著風箏的線。如我這樣的年輕人,一方面現代交通便利,“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已經很少有人能安于故土;另一方面,人才向著更好更大更繁華重要的是又更多機會的地方大量涌去,“寧為鳳尾,不為雞頭”。我每每回想起故土,想要尋根,閉上眼睛撥開記憶的重重迷霧、我的根也不過是一些面目模糊的親戚和莊嚴的祖墳,除外,再無其他。
我想要根,像沈從文的《邊城》、莫言的東北高密鄉那樣刻骨銘心的地方,可是,是怎樣一代代地我們就失去了那濃重的鄉情呢?
亦或是我應該高歌著鼓勵年輕人:飛吧!飛吧!不要再像你的祖輩一樣一輩子只看著腳下的那塊土地,飛吧,像那寒風中的雪花,依舊潔白而不染一塵,依舊帶著故鄉的氣息,卻勇敢地乘風飛向未知的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