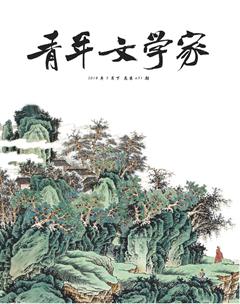走出源語言的“文化困境”
單原
摘 要:中華文化外譯是中國大國崛起背景下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手段,如何克服“文化困境”,擺脫在目的語中的“水土不服”,讓中國文化“通達”西方讀者更為順暢,擴大譯介受眾、提升譯介效果,是新時代譯者的使命。作者選取林語堂和張愛玲——二十世紀中國兩位著名的雙語作家兼翻譯家為例,以異于傳統(tǒng)“歸化”“異化”的分析角度,解析文化外譯中翻譯策略的得失權(quán)衡、翻譯理念,提出以文化補償擺脫“文化困境”的“多元調(diào)和”宗旨。
關(guān)鍵詞:中國文學(xué)外譯;林語堂;張愛玲;多元調(diào)和;文化補償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15-0-02
一、中國文學(xué)外譯的翻譯策略
中國文學(xué)外譯是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手段。而翻譯作為跨語交際活動,又必然集中體現(xiàn)了在一國語言翻譯為另一國語言這個過程中所面臨的文化困境。“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譯中如何碰撞、轉(zhuǎn)換、交流和接受的問題”。 [1]
傳統(tǒng)的分析中國文化因素的兩種手法,以源語文化為認同的“異化”原則和以目的語為歸宿的“歸化”原則不足以解釋譯者在處理“文化困境”時面對的復(fù)雜情況。二十世紀作為中國文化外譯先驅(qū)的兩位雙語作家和翻譯家——林語堂和張愛玲,前者各種英文著作及譯作共三十二部,在西方的文化譯介地位至今無法撼動;而后者的自譯作品努力用英文把那凝結(jié)著人情世故的中國故事再一次作細膩的述說。[2]他們在面對“文化困境”時采取的“多元調(diào)和”的翻譯策略,以及“文化補償”的翻譯理念,是現(xiàn)代翻譯工作者非常珍貴的研究案例。
二、“譯中有作,作中有譯”——宏觀“多元調(diào)和”策略
張愛玲的《金鎖記》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故其自譯《金鎖記》時(曾譯名有Pink Tears、The Rouge of the North 和The Golden Cangue等),對原作品在敘事策略、情節(jié)編排、人物刻畫等方面都作了較大幅度的增刪,譯文文本呈現(xiàn)出“亦作亦譯”的特色。《更衣記》和英文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不僅題目有異,中英文對比也有很大出入。借用張愛玲在散文《愛》中的說法,源語言的枷鎖是“欲言又止、進退維谷”;對于“不可譯”的翻譯策略,只能用目的語的思維重新編排,才能達到外國讀者的接受度。
這種宏觀層次的調(diào)和策略,同樣也是林語堂先生多次采用的。《生活的藝術(shù)》、《蘇東坡傳》等作品,都是集“編、譯、著”于一體。2014年于日本發(fā)現(xiàn)的《紅樓夢》林譯本原稿,也是將原著進行了重新編排,林語堂先生的個人評注穿插其中,文本同為一體,而不是采用傳統(tǒng)的標為“注釋”的方法。《紅樓夢》翻譯研究專家、南開大學(xué)教授劉士聰指出,“林語堂知道英文讀者讀這樣的故事困難在哪里,于是把《紅樓夢》用他們能理解的方式重新編寫了一遍,這很大膽但很明智。”[3]
三、分歧——林語堂的“句譯”和張愛玲的“字譯”
在《論翻譯》一文中,林語堂提出字譯與句譯說,并從語言學(xué)角度闡釋了翻譯不能以字為主體,而只能以句為本位。句譯為正,字譯為謬,兩者不可兼容并立。他認為,“譯者無字字對譯之必要,且字字對譯常是不可能之事,所以句譯家對于字義是當活的看,……先把原文整句的意義明白準確的體會,然后依此總意義,據(jù)本國語言之語法習(xí)慣重新表示出來,若能字字相對固善,若此總意義在本國文不能用同樣之辭字表出,就不妨犧牲此零字而別求相當?shù)模蜃罱谋硎痉椒ā!盵4]
這種以句為單位整體處理的特色在其著譯《武則天傳》對駱賓王《代李敬業(yè)傳檄天下文》的翻譯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可?”林語堂的譯文擺脫了源語言句式反問的束縛,又保留了源語言對仗工整的美感,“The armys cause is just, its might irresistible.” [5]而檄文名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譯文不但調(diào)整了語序,且為目的語讀者增補了“一抔之土”的解釋,仍然保持用詞工整、句式簡潔,“the orphans were abandoned when their fathers grave was hardly dry.” [5]
相比之下,張愛玲的對字譯的拘泥影響了其譯作的可讀性,其自譯作品《金鎖記》十幾度改稿,幾易書名卻仍命途多舛,也與此不無關(guān)系。校閱張愛玲《金鎖記》的學(xué)者夏志清指出她的翻譯“信”有余而“達”未及;而香港嶺南大學(xué)教授劉紹銘(2006)則認為,張愛玲的譯文“文字幽冷,只偶見沙石”,而這“沙石”的一部分就來源于太過注重字譯。例如,“這會子有這么勢利的,當初何必三媒六聘地把我抬過來?”[6]張愛玲的譯文雖加了解釋,卻固執(zhí)地保留了數(shù)詞“三”和“六”,字面雖對應(yīng)了,但原本的虛數(shù)在目的語中成了實數(shù),增添了讀者理解的難度,讀來也更加拗口,“If you are going to be so snobbish, why did you bother to carry me here in a sedan chair,complete with 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wedding gifts?”
四、文化補償——“多元調(diào)和”的宗旨
嚴復(fù)曾闡明“信”和“達”的關(guān)系:“至原文詞理本深,難于共喻,則當前后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jīng)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 [4]
林語堂先生則進一步提出翻譯詩文小說一類的藝術(shù)作品時,在達到忠實通順的標準后,“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問題。”因“凡文字有聲音之美,有意義之美,有傳神之美,有文氣文體形式之美。……理想的翻譯家應(yīng)當將其工作做一種藝術(shù)。以愛藝術(shù)之心愛他,以對藝術(shù)謹慎不茍之心對他,使翻譯成為美術(shù)之一種(translation as a fine art)”。[4]
林語堂擺脫“文化困境”的方法之一即為文化補償:若源語言有一部分“失之桑榆”,目的語一定要想辦法“得之東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之乎者也”的翻譯:
滿口仍用“者也之乎”等字——《明清小品(下)·不亦快哉》
...and still using the most polished language of thou and thee and wherefore and is it not so? [4]
“之乎者也”為文言語氣詞,屬虛詞,在英文中無法對應(yīng),必然“有失”;而林語堂的譯文用了舊體英語,模擬了文言文莊嚴的語體,所謂“有得”。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林語堂翻譯李清照詞《聲聲慢》“凄凄慘慘戚戚”一句,源語言疊音“之失”通過連用七個so和押頭韻的形容詞“得補”了回來。林語堂在《論譯詩》中如此表述翻譯這十四字的心得:“……真費思量。須知全闕意思,就在‘梧桐更兼細雨那種‘怎生得黑的意境。這意境表達,真不容易。所以我用雙聲方法,譯成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十四字(七字俱用定母譯出),確是黃昏細雨無可奈何孤單的境地,而最后dead一字最重。這是譯詩人的苦處及樂處,煞費苦心,才可譯出。”[4]
文化補償也是張愛玲嘗試和調(diào)和異化與歸化策略時所作的努力,以求達到既能在讀者理解和接受的范圍內(nèi),又“多給他們一點別的”。然而從譯文效果來看,則“金玉”與“沙石”同在。劉紹銘(2006)認為“沙石”的問題主要出現(xiàn)在張愛玲的譯文太中規(guī)中矩,學(xué)院派了(bookish English)。
以張愛玲小說中情有獨鐘的意象“月亮”為例: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凄涼。”[6]
Shanghai thirty years ago on a moonlit night……But seen after
thirty years on a rough road, the best of moons is to be tinged with
sadness。
The best of moons對于目的語讀者來說,是一個不太自然的表達。如果根據(jù)上下文“歡愉”的月亮,可以改為“even the moon at its gayest moment”。
更有比較價值的是“花”的意象,張愛玲和林語堂的不同處理。
首先是《金鎖記》中的一段,“可不是,這半輩子已經(jīng)完了——花一般的年紀已經(jīng)過去了。”[6] 張愛玲的譯文,“True, half a life time had gone by— the flower years of her youth.” [7] 中保留了“花”的意象,采取“直譯+增補”的方法,源語言中丟失的意味用目的語“youth”直白補充進來。
而林語堂翻譯《明清小品(下)·黛玉葬花詩》時,源語言中幾句帶有“花”的意象都在目的語中進行了轉(zhuǎn)換,沒有直接出現(xiàn):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游絲軟系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
Fly, fly, ye faded and broken dreams
Of fragrance, for the spring is gone!
Be hold the gossamer entwine the screens,
And wandering catkins kiss the stone.
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Oh, look upon these tender, fragile beauties,
Of perfumed flesh and bone and hair.
The admirer shant be there
when her time is up,
And the admired shall no longer care!
同樣一個“花”字,在林語堂的譯文中分別被轉(zhuǎn)換成了“dream(夢)”、“flesh(肉)”、“bone(骨頭)”、“hair(頭發(fā))”和“her time(她的年華)等,充分發(fā)揮了英文作為目的語時用詞的豐富多樣。
五、結(jié)語
在全球化的歷史文化語境下,如何改變文化翻譯中“信息單行道”的現(xiàn)狀,向世界展示中國語言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無限魅力,需要廣大翻譯工作者認真研究文化補償和多元調(diào)和的策略,不斷提高中國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質(zhì)量。
參考文獻:
[1]謝天振.翻譯的本體研究和翻譯研究的本體[J].中國翻譯,2008(5):6-10.
[2]葛校琴.譯者主體的枷鎖——從原語文本到譯語文化[J].外語研究, 2002(1):62-65.
[3]陸陽.林語堂英譯本《紅樓夢》原稿在日本被發(fā)現(xiàn)[N].中國青年報, 2015-07-26(02 版).
[4]林語堂,吳曙天(Ed).翻譯論[M].光華書局,1937.
[5]林語堂. 武則天傳[M]. 北京: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2009:4-186.
[6]于青,金宏達.張愛玲文集[C].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112-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