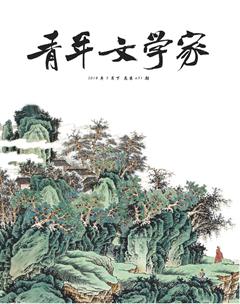論嚴歌苓新移民小說的身份敘事
摘 要:在新移民文學中,身份認同是一個核心的和恒久的主題,當然,由于時代的不同,作家身份的差異、大眾審美情趣的變化等種種原因,每一時期、每一作家筆下的有關身份認同的敘事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嚴歌苓作為新移民文學的領軍人物,其作品呈現出的身份敘事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學魅力,成為她反抗中心與主流、證明自我存在價值和意義的有效途徑,這其中尤以性別身份敘事更具特色。
關鍵詞:新移民小說;身份敘事;嚴歌苓
作者簡介:張棟輝(1980-),女,山東乳山人,煙臺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海外華人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15--03
作為“新移民文學”的代表人物,嚴歌苓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有著明確的認知和極高的追求。她不僅長于塑造西方人物眼中的“他者”形象,更立足于表達整個人類的精神探索,“文學創作需要經歷和經驗的積累、強烈情感的激發,但更需要不斷地去挖掘及開拓,將個人的情感升華為人類的普遍情感,對自我的故事筑成‘寓言”。1[P83]她長期致力于通過對一系列主流社會和兩性關系的邊緣書寫來對自己的文化身份進行某種確認,這種身份的確認是來自種族的、國別的、性別的多重變奏,成為作者反抗中心與主流、證明自我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一種方式。這種對身份的認知與思考,不僅是華人移民群體的執著探尋,也是在當今這樣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中,文化日益混雜、身份日益模糊的世界各族群所面對的精神困惑之一。因此,建構多重糾葛中的身份敘事,既是嚴歌苓的創作特色,亦是她對文化超越和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
一、“身份”的界定:“自我”建構與文化身份的確立
“身份”即“認同”。人的身份是一個復雜的界定,它是由人的種族、國籍、性別、出生地、居住地、語言、職業、階層、宗教信仰等多種元素共同構成的復合體。這些構成身份的任何一種元素都會因時因地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這樣一來,“身份”的界定就變成了無休止的流動的過程,具有鮮明的“自我”意識的個體生命就處于一種變化的狀態,“身份確認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內在的、無意識的行為要求。個人努力設法確認身份以獲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設法維持、保護和鞏固身份以維護和加強這種心理安全感,后者對于個性穩定與心理健康來說,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P331]對于每一個個體生命來說,身份的確認首先和文化體系聯系在一起,文化作為某個民族經過漫長的歷史變遷所逐漸積累的精神形態、具有特征的物質產品以及特定的行為和思維習慣的綜合體,它必然會對生活于其中的個體身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生活于某一固定國家地域的人,他的文化身份相對單一恒定,可是隨著人類遷移現象的增加,這種相對恒定的文化身份不斷受到各種外在種族、國家的異質文化的挑戰,而呈現出一種流動的非恒定狀態。當然,遷移并不意味著自身種族文化身份的消失,而是這種狀態下的身份建構會在遷移過程中不斷地汲取外來營養,吸收異質文化中的優秀養分,從而將本民族文化的獨特性與異質文化的豐富性統一起來。英國學者霍爾認為:“身份并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透明或毫無問題。也許,我們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經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實踐加以再現的事實,而應該把身份視作一種‘生產,它永不完結、永遠處于過程之中,而且總是在內部而非在外部構成的再現。”3[P208]因此,華人移民的跨國生活經歷必然是會加劇身份認同的復雜性。大多數移民通常會希冀擺脫固有種族的局限,不斷努力,試圖躋身于移居國的主流社會之中。這樣,他們可以更自由地出入于居住國的各種生活層面,享受他們合法的公民權利和國家保障,同時,他們也可以很自主地遠離本民族文化傳統中的種種弊端。但現實情形卻是,新移民無論在價值觀念和言談舉止和主流社會多么相似,他們內在的文化傳統和外在的生理特征決定了他們完成徹底的身份認同決非想象的那般容易。
海外華人生活的地方,大多會形成一些以唐人街為文化標識的華人區,從文化心理和身份認同層面看,唐人街承擔了海外華人在異域保持本土文化和異質文化沖突和交融的文化緩沖功能,隨著華人移民主流意識的增強和生存的需要,越來越多的華人后裔已經沖出了文化的緩沖地帶,躋身居住國的主流社會,這種情形下,熟悉的文化保護膜被強行剝離掉,赤裸裸地暴露于異質文化中的移民也加劇了對居住國身份認同的渴望。“對‘文化身份的不確定感和茫然不知所從,曾經困擾過無數的在美華人,這種情狀在美國華文文學中有著反復的表現。”4[P107]在這種情況下,對文化身份的確立成了海外華文文學普遍表現的一個永恒主題,當然,由于時代的不同、主流意識形態的差異、作家群體的更迭、大眾審美情趣的變化等種種原因,這種身份認同的具體過程會產生個體的、流動性的差異,這種差異也反向證明了身份認同的豐富性和重構性。當個體脫離母體文化,置身于異質文化中時,文化身份呈現不斷尋求突破、不斷被異質環境懸置的狀態時,這種身份的確認會呈現一種開放式的狀態,在建構基礎之上不斷重構。
后殖民文學批評家霍米·巴巴提出了“雜粹”的文化身份理論,這一觀點是指移民因時空的跨越而產生了復雜的身份,這種改變使傳統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隨之瓦解,代之包容、矛盾、流動的文化身份認同,正如學者黃萬華所說:“身份并非是一種界定或歸宿,而是對自身擁有的文化資源的不斷開掘。如果我們能更關注這一過程包含的悖論、矛盾,更關注文化情感、生存策略對身份書寫的影響,華文文學中的身份認同會呈現出更豐富的意義。”5[P9]在嚴歌苓的諸多作品中,我們會發現“雜粹”理論的廣泛運用,因為具體文本中這種指向身份焦慮和文化融合的細節非常多,很多時候并不能將其文化身份簡單地加以界定,所以身份認同將會呈現出復雜的豐富的多重表征。
嚴歌苓的長篇小說《寄居者》就比較典型地體現了這種身份認同的駁雜性。這篇小說講述了華裔女性May、流亡上海的猶太青年彼得、混跡美國下層的猶太人杰克布·艾德勒之間錯綜復雜的情感糾葛,在情感的講述中滲透著文化、國別、種族等多重身份指向。敘述者May出生在美國的華人移民家庭,成長于各種族雜居的上海。當她無可救藥地愛上了逃難到上海的猶太青年彼得、被他憂郁的氣質和優雅的行為所打動后,為了幫助彼得逃離日本人即將實行大屠殺的上海,May策劃了一個騙局,將與彼得容貌頗有相似的杰克布·艾德勒騙到上海,偷取了他的護照,帶彼得登上了逃往美國的船只。然而,登船的瞬間,May卻失望于彼得的冷酷自私,最終選擇留在上海,與已經投入抗戰的杰克布共生死。小說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都具有比較混雜的文化身份:May作為華人移民,在美國飽受歧視;彼得作為逃亡的猶太人,在混亂的上海苦苦掙扎;杰克布也是猶太人,在美國生活無著,到上海后被日本人欺凌。流散者身份所帶來的茫然、焦慮和一定程度的恐慌,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精神夢魘,也促使不斷思考華人和猶太人這兩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流散族群的民族性格與文化特性之間的相似與區別。這從側面傳達了嚴歌苓在文化融合中身份焦慮的具體體現和“雜粹”的文化身份觀的確立,單純的個體生命因時空的跨越在不同的場景中擁有了多變的文化身份體驗。
在短篇《太平洋探戈》中,嚴歌苓則通過文化認同的孤獨堅守折射出文化身份的異域迷失。小說中的主人公毛丫在美國街頭賣藝為生,表演以瓷碗、盤子、瓷勺為道具的中國傳統雜技,每天重復同樣的動作,過著同樣的生活,在她進行她的第三百多場表演時,她依然是美國三號街上的外來客,這種以自閉狀態來保護脆弱的內心世界成為新移民文化身份確立過程中典型的反面例證。
此外,《無處路咖啡館》中的女留學生“我”、《阿曼達》中的陪讀丈夫楊志斌、《大陸妹》中的大陸妹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都滲透著作者對文化身份認同的多方位、多層次的理解與定位。
在文化、經濟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漲的多重文化語境下,嚴歌苓在創作中對文化身份確立的思考,顯示著只有在文化間的多元共生與互動交流基礎上,我們才能確立合乎時代和族群的文化身份觀,這也是新時期移民文學長久以來始終的追問與探尋。
二、性別身份:歷史與政治消融中的性別立場
海外華人擁有多重的文化身份,而海外華人中的女性尤甚,東方、移民、女性的三重異己身份,使她們承受著多重壓力:來自西方世界的強權壓力、來自男權社會的性別歧視、來自故國的同族排斥。所以,以性別身份為基點,體察回溯個人的成長史、家族興亡史、民族的災難史、移民的辛酸史都成為她們在海外尋求身份確認的有效方式,對于海外的移民女作家來說,寫作成為她們確認自身文化價值和精神慰藉的有效途徑。
西方20世紀60年代產生的女權主義運動,一度將男性與女性對立起來,對20世紀西方社會的兩性關系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后來,極激烈的女權主義理論被溫和女性主義理論所取代,對男女兩性的差異性表達以及倡導兩性之間的和諧相處成為主要內容。中國七八十年代是繼五四運動之后是受西方理論影響最大的時代,女性主義理論進入中國后對中國當代的文學批評理論產生強烈的沖擊,女性主義文學也漸漸浮出歷史地表,成為當代文學創作的一股強勁潮流。中國女性主義文學并不像西方社會那樣熱衷于從政治方面和理論層面去探討,而是極力表達女性獨特的性別體驗和審美旨趣。
嚴歌苓赴美前已是引起文壇關注的青年作家,有著相對成熟的文化價值判斷。赴美后,處身于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之中,特別是在女性主義運動發展最充分的美國,無可避免地會接觸到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新思想的沖擊,勢必引起她更深層次的思考。因此,嚴歌苓赴美后的作品中更為注重渾然意義上的女性表達,崇尚寬容的女性,質疑女權主義的極端立場。這顯然源自她經過雙重文化洗禮之后對性別身份的獨特理解。她在塑造這些女性時,把自己對女性的理想置放其中,并且深入到女性的隱秘心理,刻畫了女性內心的歡娛和悲哀,力求將本真的女性精神世界呈現在讀者面前。羅素認為:“有大型的歷史學,也有小型的歷史學,兩者各有其價值。但它們的價值不同。大型的歷史學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是怎樣發展成現在的樣子的;小型的歷史學則使我們認識有趣的男人們和女人們,推進我們有關人性的知識。”6[P14]嚴歌苓對于歷史的書寫無疑是屬于后者的,她是一個關注歷史的作家,但并不熱衷于宏大的歷史敘事,而是喜歡從個人的微觀視角出發,以個人的沉浮折射出歷史的巨大變遷。
女性視角是嚴歌苓敘述歷史的切入點,這種性別立場是對女性作家個人化寫作立場的堅持,消解顛覆了一直由男性占據的權威話語和主流的歷史敘事模式。以《第九個寡婦》為例。小說中的人物跨越了幾十年的漫長歷史,建國前的歷次重大戰爭,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反”、“五反”、“四清”、“反右”、“文革”等大大小小數次運動都在主人公王葡萄的生活中一一展現。戰爭和政治運動使得家園被毀、生死離別、親人反目、朋友背叛成了普通民眾生活里不停上演的殘酷戲劇。然而,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政治戲劇在寡婦王葡萄的眼中,卻不過如墻外的季節更迭、村外的人來人往一般簡單:“過去十四軍來了,駐下來。后來又走了。八路軍來了,也走了。土改隊住了一年,還是個走。過去這兒來過的人多呢——洋和尚,洋姑子,城里學生、日本鬼子、美國鬼子,誰待長了?你來了說他投敵,他來了說你漢奸,又是抗日貨、又是日貨大減價,末了,剩下的還是這個村,這些人,還做這些事:種地、趕集、逛會。”7[P206-207]沒有任何特殊的意義。政治生態的變化,遠不如她照顧二大、填飽肚子、納鞋底那樣實實在在、真真切切,由此政治在她眼中成為一個虛化的概念。這種生存態度在田蘇菲(《一個女人的史詩》)和馮婉喻(《陸犯焉識》)身上同樣如此。她們對身旁的政治權力的更迭遠不如對丈夫的一嗔一笑更關注。戰爭與政治似有若無地飄在她們精神世界的邊緣。而她們淪陷于個體的兒女私情中,且哭且笑。所以,在這幾位女性的史詩中,歷史、政治都退隱到現實生活的幕后,生存與愛情才是她們生命的精神支撐。
在《小姨多鶴》這部小說中,嚴歌苓更將筆墨投注于竹內多鶴這位日本遺孤身上。在日軍大潰敗的1945年,日本女孩多鶴在族人集體自殺的時候,出于求生的本能活了下來,后被一個中國家庭買去做傳宗接代的工具。日本人的身份使她在尷尬和仇恨中存活。她既為這個家庭帶來了生兒育女的希望,同時又是仇國的代名詞。雖然這個家庭在數十載的生活中始終籠罩著一種復雜難言的家庭氛圍,但最終人性本初意義上的關愛和理解還是抹掉了外在的政治標簽,構建出一個溫馨的、超越種族和世俗倫理的奇異家庭。這部小說中,嚴歌苓把對女性生存的關注、女性自我的確立過程透過竹內多鶴這個日本移民的一生而展現出來,其中灌注著她對種族、意識形態、宗法倫理等的多重文化思考。
作為具有復雜身份認同的女性作家,嚴歌苓正是在以性別身份為基點的歷史敘述中來重塑歷史,對歷史進行重新書寫和深度挖掘。這種歷史書寫的方式既是個人的,也是民族的,既是豐富的,又是深刻的,表達了她對個體生命生存價值的肯定和對人之靈性的呼喚與祈盼。
嚴歌苓的新移民小說以身份敘事為出發點,反復言說和挖掘東西方時空下的豐富人性,對文化價值判斷與國家、階層、種族、性別等概念進行了客觀理性的質詢與考量。這種選擇使嚴歌苓的創作呈現出與中國當代文學迥異的藝術風貌,顯示了新移民文學作為跨文化的華人文學的獨特價值。
參考文獻:
[1]饒芃子.《海外華文女作家及其文本的理論透視》[A].饒芃子.《海外華文文學的新視野》[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2][荷]萊恩·T·賽格爾斯.《“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文學研究中的新視角》[A].樂黛云、張輝.《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英]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A].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4]劉俊.《“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尋——美國華文文學的一種解讀》[J].《南京大學學報》.2003(5).
[5]黃萬華.《先讀為快》[A].《多元文化語境中的華文文學》[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
[6][英]羅素.《論歷史》[M].何兆武.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
[7]嚴歌苓.《第九個寡婦》[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