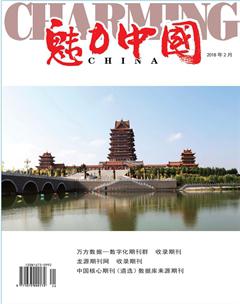農村流動青年與未流動青年的就業理性
王煒 張立龍
摘要:文章在2013年和2015年CSS數據基礎上對農村流動青年與未流動青年的就業選擇進行了研究。發現:與農村未流動青年中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和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未婚、女性的農村青年更加傾向于向外流動成為流動青年即新生代外出農民工。多元回歸結果顯示,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的就業選擇主要出于經濟理性,即如果其向外流動,收入也不能增加。但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如果選擇外出就業或者全職從事非農工作,其年收入將顯著增加;其由于承擔了更多的家庭照料責任而留在本地就業。
關鍵詞:新生代外出農民工;新生代本地農民工;就業理性
一、引言
近幾年,隨著外出務工性價比越來越低,家鄉對農民工的吸引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勞動力選擇在本地就業,農民工內部結構出現變化,表現為本地農民工增速遠遠快于外出農民工,本地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比例在逐步增加。同時,在農村青年就業和居住地點的選擇上,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選擇在農村本地就業或務農;他們大多居住在農村,而在鎮上或縣城務工。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選擇在本地農村就業或居住,這將對中國未來城鎮化的格局產生重要影響。
將流入地帶來移民生活條件改善的因素作為“拉力”,將流出地不利的社會經濟條件作為“推力”,“推拉理論”認為人口遷移在這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李強(2003)1[1]總結了農民工特殊的生命周期,年輕的時候外出打工掙錢,年齡大了以后回家鄉務農、務工或經商。在現有城鄉收入差距依然較大的情況下,無論是“推拉理論”還是“農民工生命周期理論”,都不能很好的解釋為什么一部分農村戶籍的青年選擇向外流動到經濟發達的地區打工,而仍有一部分農村戶籍青年選擇留在本地,或務農或從事非農就業,而不是外出務工?
為研究農村青年的就業選擇及其原因,本文將農村流動青年與未流動青年定義為:(1)農村流動青年是具有農村戶籍、從事非農工作、居住在戶籍所在鄉鎮以外的非農村地區的18-35歲的青年,也將流動青年稱為新生代外出農民工。(2)農村未流動青年是具有農村戶籍、從事非農工作或務農、居住在戶籍所在鄉鎮以內的農村地區的18-35歲的青年。進一步細分,將只從事非農工作(即“離土不離鄉”)的未流動青年稱為新生代本地農民工,將主要從事非農工作(部分從事農業工作)的未流動青年稱為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本文將首先分析農村流動青年與未流動青年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礎上闡釋四類農村青年群體就業決策的理性。
二、農村流動青年與未流動青年的基本特征
本文所用數據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年與2015年進行的“全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2015年數據中,由于本文僅關注有工作的農村青年,即年齡在18-35周歲(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農村戶籍青年,需將35歲以上的樣本剔除,最終樣本量為987個。2013年數據中,符合本文研究對象的樣本為1100個。
為研究農村各類青年的基本特征,本文將農村青年的就業方式作為因變量,以新生代外出農民工為參照組,將年齡、年齡的平方、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性別、居住區域作為自變量,構建多項邏輯斯特模型。模型結果顯示(表1),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性別、居住區域都對農村青年的就業選擇有影響。與新生代本地農民工和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未婚、女性的農村青年傾向于向外流動成為新生代外出農民工。
三、農村流動青年與未流動青年的就業理性
2013年與2015年CSS數據顯示,在就業方面,與新生代本地農民工、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相比,新生代外出農民工年收入相對較高,工作的技能要求高。但從變化趨勢看,新生代農民工各群體的收入均有較大幅度的提高,但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的收入增長速度和工作對技能要求的提高速度更快,這使得新生代外出農民工與新生代本地農民工之間在收入和技能需求方面的差距在縮小。新生代外出農民工與新生代本地農民工之間在月工作天數、日工作小時數、工作的穩定性(6個月內失業的可能性)等方面并不存在顯著差異。但與新生代外出農民工相比,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在工作時間與強度、雇傭身份以及工作穩定性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同樣的,從變化趨勢看,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與新生代外出農民工的就業要求在逐漸減小。從就業的社會保障水平看,新生代外出農民工顯著高于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然而從新農合和新農保的覆蓋看,與新生代外出農民工相比,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特別是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中,擁有新農保和新農合的比例顯著較高。
新生代外出農民工在收入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優勢是否是由于其受教育程度、工作中較高技能的要求等帶來的呢?或者說新生代本地農民工和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由于其本來受教育程度和工作中技能的要求就低,因此收入也低,留在本地就業也同樣是一種經濟理性的選擇?本文采用多元回歸的方法闡釋農村青年不同就業形式之間收入差別的原因。現有研究已經證明:性別差異2[2],人力資本如受教育程度3[3]、培訓4[4]、健康投入5[5],就業地區的差異等是影響就業收入的重要因素。
由于農村青年的年收入是右偏分布,因此將農村青年的年收入取對數值之后作為因變量。本文的關鍵變量為農村青年的類別,即新生代外出農民工、新生代本地農民工,新生代本地農民工(部分務農);將新生代外出農民工作為參照組。控制變量包括人力資本、人口學特征、工作狀況、就業區域等。
從模型結果看(表2),人力資本、人口學特征、工作狀況、就業區域等都對農村青年的收入有一定影響。在控制了相關變量后,新生代本地農民工這一變量并不顯著,即與新生代外出農民工相比,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的收入并沒有表現出顯著差異;新生代本地農民工如果外出就業其收入水平也不會增加,流動至外地并不能帶來額外的收入。但對于部分務農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農村青年類別中新生代本地農民工(部分務農)的變量的系數顯著,這意味著如果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外出就業而成為新生代外出農民工的話,其所得收入將比留在本地就業顯著的增加。
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新生代農民之所以選擇“留守”本地就業或務農,其還承擔了更多的家庭照料功能。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的家庭中,有80歲以上老人的比例分比為20.8%,有16歲以下子女的比例分別為72.5%,顯著的高于新生代外出農民工、新生代本地農民工。即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新生代農民之所以選擇“留守”本地,與其承擔的家庭照料責任有一定的關系(表3)。
四、主要結論與討論
本文利用CSS數據研究了農村流動青年與未流動青年的就業理性,結果表明,在控制了農村青年的人口學特征、工作特征、人力資本、就業區域等變量后,得出:新生代本地農民工如果選擇外出就業,其收入也不會增加;部分務農新生代農民工如果選擇外出就業,其收入將增加10%;但是,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的已婚比例、家中有16周歲以下子女的比例、家中有80歲以上老人的比例均顯著高新生代外出農民工,其就業選擇主要是由于本地就業在子女的教育、家庭關系與情感、老人照料等方面受益是外出就業無法比擬的;因此其就業選擇更多的體現為社會理性。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提出,到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到60%。由此可以測算預計還將有1億農民向城鎮轉移。但是從目前我國的城市空間的承載力已無法充分容納這一批人口。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從農村流動青年與未流動青年的就業分化看,與新生代外出農民工相比,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的收入增長更快,即收入有趨同的趨勢。同時,新生代本地農民工出于經濟理性留在本地就業,即外出就業也不能給其帶來收入的提高;而部分務農的新生代本地農民工由于家庭因素而出于社會理性留在本地就業。這意味著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盲目遷出的現象逐步減少,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繼續留在原居住地,“就地城鎮化”成為未來城鎮化發展的一個方向。
參考文獻:
[1]李強.影響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3(1):125-136
[2]張瓊.農民工工資性別差異的實證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問卷調查[J].廣東社會科學.2013(3):213-220
[3]張泓駿、施曉霞.教育、經驗和農民工的收入[J].世界經濟文匯.2013(6):18-25
[4]張世偉、王廣慧.培訓對農民工收入的影響[J].人口與經濟.2010(1):34-37
[5]秦立建、陳波、秦雪征.健康對農民工外出務工收入的影響分析[J].世界經濟文匯.2013(6):110-120
作者簡介:王煒,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張立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