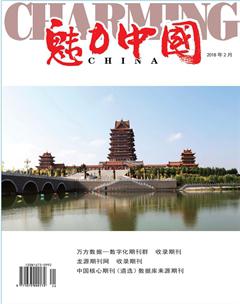探析康有為對中國畫社會實用化觀念
劉巍
摘要:在民族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下,康有為基于實用主義的觀念,出于政治目的,提出改革中國畫,強調中國畫的社會功用,其觀念有助于促進中國實用美術的發展,但也不免誤解了中國畫主要功能。
關鍵詞:文人畫;社會實用化;圖像功能;教化功能;審美性
康有為是中國近代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他雖然不是畫家,但他提出的一系列中國畫變革主張,影響了幾代美術家。尤其是他的弟子徐悲鴻、劉海粟將其觀念納入了實踐的軌道,在近代中國畫發展進程中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他既是近代早期指出中國畫問題的人,又是引起畫界諸多爭議的源頭。他所引發的關于寫意與寫實、院體畫與文人畫、中國畫與西畫等問題的論爭,至今不息。
康有為在其著作《萬木草堂藏畫目》《物質救國論》《歐洲十一國游記》等著作中,反復強調中國畫的社會功能,如他所提出的“今工商百器皆籍于畫,畫不改進,工商無可言”,“工商業系于畫者甚重。”等觀點,認為只有改革中國畫,才能發展工商業,把中國畫緊密的同國家經濟聯系起來。顯然他的變革主張更多的是從國家政治、經濟角度所考慮而提出的,而并非是站在中國畫發展的立場。康有為將中國畫與工商業聯系到一起并不是沒有道理的,他說“豈知一切工商之品、文明之具,皆賴畫以發明之。”“若畫不精,則工品拙劣,難于銷流,而理財無從治矣。”這里的“畫”,在我們今天看來更確切的應該叫做“圖”,是具有社會實用意義的美術。中國傳統工藝美術有著輝煌的歷史和舉世的成就,在自然經濟下,基本上都是手工作坊或家庭生產,用于生產的圖紙多是由畫匠負責繪制。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古老的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在西方堅船利炮面前,改良派認為只有發展工業,國家才有出路,由于機械化生產不同于手工作坊,需要更加精細和標準化的圖紙,所以對從事繪圖工作人員的要求大大提高。在洋務運動時期,上洋務派創辦的幾乎各類學堂中,都設有圖畫課程,并設有“畫圖房”或“繪事院”。晚清以圖學為核心,出現了一次全國范圍的視覺啟蒙運動,以培養和滿足工商業需求的繪圖人才。學習西方繪畫,已經不止是藝術層面的考慮,是關乎著整個社會發展。所以,康有為對中國畫社會實用化觀念帶有明顯的時代色彩。
在康有為看來,“中國既擯畫匠,此中國近世畫所以衰敗也。”而中國畫應該“以形神為主,而不取寫意;以著色界畫為正,而以墨筆粗簡者為別派。”在他看來中國畫的衰落在于貶低匠畫,推崇文人畫,文人士大夫把中國畫當作修身養性,聊以自娛的逸趣,而在那個民族危難的時代,康有為作為一個政治家,顯然是希望動用一切社會力量來促進國家救亡圖存,就算中國畫都被要求賦予更多的社會責任。
康有為的倡導順應了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時代要求,是有利于近代實用美術的萌發,但他的主張也不免給中國畫的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潘天壽在《中國繪畫史》指出:“康氏不諳中西繪畫,主以院體為繪畫正宗,是全以個人意志而加以論斷者。恐與其政見之由維新而至于復辟者相似,不足以為準繩。”陳師曾在《文人畫之價值》中指出:“殊不知畫之為物,是性靈者也,思想者也,活動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單純者也。”康有為在當時的變革主張,在當時就受到了傳統中國畫家的激烈反對,他若是僅提倡學習西方繪畫,想必不會在美術界引起軒然大波,但他貶文人畫的價值,則觸碰到了傳統中國畫家的敏感神經。康有為是站在政治立場,出于社會實用觀念,要求強化中國畫圖像功能和教化功能。而傳統中國畫家,站在中國畫立場,強調中國畫的精神性和審美性,維護中國畫的獨立性,不做社會的附庸工具。他們論爭的關鍵問題在于什么才是中國畫最重要、最本質的功能。縱觀中國美術史,從古至今,中國畫都與政治、宗教、哲學、道德等有著千世萬縷的關系。晉陸機在其《土衡論畫》中說:“宣物莫善于言,存形莫善于畫。”齊梁時謝赫《畫品》提出“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沉。”中國畫在早期主要的作用就是圖像功能和教化功能,記錄歷史或事件,宣揚政治、道德。唐代《歷代名畫記》中張彥遠雖然還是提出:“夫畫者 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發于天然,非由述作。”但是他已經開始提出繪畫的功能不僅是用以“鑒戒賢愚”,而且還用以“怡悅情性”﹐指出“書畫用筆同法”﹔提倡“自然”,以“自然﹑神﹑妙﹑精﹑謹細”等來排列畫藝高低的品第。隨著山水畫和花鳥畫先后的獨立成科,可以看出不管是皇家貴族,還是士族階層,更加重視中國畫的審美價值,已經不再局限于宣揚政治、道德的人物畫題材。再至宋代文人畫興起,畫家在中國畫中注入了更多的個人思想情感和審美情趣,中國畫成為文人士大夫修身養性,聊以自娛的逸趣,也被視為士族階層的精英文化的象征。可以看出中國畫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圖像功能和教化功能,已經上層到精神層面影響社會。中國畫一旦上升到精神層面,就需要欣賞者具有更高的文化修養,才能讀懂作品。那么中國畫更加局限于知識分子階層之間交流,對社會直接的影響已經就沒那么明顯。但需要說明的是在文人畫時期,院體畫、匠畫、風俗畫等同樣存在并發展著,文人畫只是作為畫壇主流和標桿,中國畫的圖像功能和教化功能并沒有喪失,只是退而次之。中國畫家于宋代就意識到了繪畫語言的獨立性和本質意義,放眼同時期的西方,繪畫還附庸于政治和宗教。可以看出,中國畫從最初的“存形”逐漸發展到成名畫家個人意志的載體,由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從需要借助政治、宗教等力量來維持發展,到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發展,不得不說這是中國畫的巨大進步。
在物質救國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確需要引入更加具有科學性和實用性的西方繪畫。康有為的出發點顯然是出于好意,但明顯帶有歷史局限性,使用的方法卻也是不恰當的,否定文人畫,無異于否定中國畫自宋代以后的發展,磨滅中國畫在精神層面的創造。康有為的否定,也是給他在美術界帶來巨大爭議的重要原因。不管是中國文化,還是中國畫,都是一以貫之的發展,不管自身的觀點分歧,還是外來文化的沖擊,最終會被中國包容吸收,成為其中一部分。實則,不管實用美術,還是純美術,大眾文化,還是精英文化,對于國家社會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相比康有為時代,只有“畫”一個概念的時代,如今我們對美術有了明確細化的分科,各分科各司其職,既互相借鑒,又獨立發展,避免了功用的混淆,造成爭議,使中國美術事業更加健康蓬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