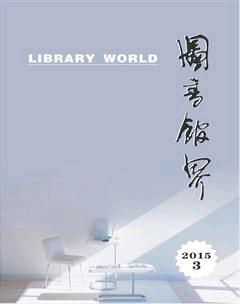1983—2013年我國學科服務和學科館員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
任湘 鄒慧玲



[摘要]通過發文年代與年發文量、發文系統與作者分布、論文影響力等指標,對我國學科館員、學科服務近三十年的國內研究現狀進行梳理,可知:我國學科館員與學科服務的研究已進入比較成熟比較穩定的階段,核心期刊與核心作者基本形成,期待更多實踐探索與國外經驗的借鑒、期待更多高校以外的研究機構與作者參與深入研究。
[關鍵詞]學科館員;學科服務;文獻計量;影響力
1研究背景和意義
學科服務是以用戶為核心,主體通過學科館員,依托圖書館和公共信息資源,面向特定機構和用戶,建立基于科研與教學、多方協同、面向一線用戶的一種新的服務模式和服務機制,向用戶提供個性化、專業化、知識化的服務,提升用戶的信息能力,為教學科研提供有力的信息保障與支撐[1]。隨著國內圖書館學科館員制度的引入,學科服務成為圖書館讀者服務的一項重要內容。它要求學科館員深入用戶的科研或教學活動中,幫助他們發現或提供更多的專業資源和信息導航,為用戶的研究和工作提供針對性很強的信息服務,是圖書館創新精神和個性化服務特征的具體體現[2]。
筆者對我國1983—2013年期間30年出版的有關學科服務、學科館員研究文獻的發文年代、來源刊物、著者分布等一系列統計指標進行分析,探求學科服務、學科館員研究發展的主要特點、所處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
2數據來源及處理方式
利用表1所列數據庫和所列條件,查找題名中含有“學科服務”或“學科化服務”或“學科館員”的文獻,檢索年限為2014年以前,檢索時間為2014年6月27日,經過去重和去除無關文獻后共檢出2 732篇。
3.1 發文年代分布
根據檢索結果顯示,我國最早的學科服務研究始于20個世紀80年代初,最初是1983年徐仁海就牧區水利如何通過調節水利資源或水文條件服務于草原畜牧業生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3]。同年,臧萬杰通過調查就高校圖書館在圖書采購方面如何為新興學科服務提出新的思路[4]。1987年、1989年陳京[5]和母益人[6]分別發文探討建立一支怎樣的“學科館員”專業隊伍和學科館員應該做好哪些工作。隨后幾年,我國的學科服務研究出現了一個“斷層”。1995年繼陳汝龍[7]提出實行學科館員與專業集成化服務是高校圖書館的最新變革舉措后,才有學者陸續對相關內容展開研究,如學科服務的思路探討、存在的障礙及對策、實施的途徑、制度的建立、隊伍的建設等。2003年,柯平[8]結合南開大學圖書館開展學科館員工作的經驗與實踐探討了高校圖書館學科館員工作。同年,一些關于學科館員制度建設及角色定位、學科館員與圖書館發展的文獻涌現。2014年(截至12月)的研究論文已有275篇(見表2)。
3.2 發文系統即期刊分布
表3顯示的前10種期刊共發表論文996篇,占檢出論文總量的36.45%,這些期刊均為圖書情報類學術期刊。按照布氏定律[9]期刊載文量的分區要求,將564種期刊上發表的2 732篇論文做以下分區:996篇論文分布在載文量50篇以上的10種期刊上,該區為核心區;804篇論文分布在載文量10—49篇的38種期刊上,該區為相關區;932篇論文分布在載文量1—9篇的516種期刊上,該區為邊緣區或外圍區。從表3可以看出三個區域的期刊之比是10∶38∶516(約1∶3.8∶51.6),即布拉德離散系數在3.8~7.2之間,核心效應明顯。從統計數據(表3、圖1)可以看出,學科館員、學科服務研究的核心期刊已形成,同時也說明我國在該領域的研究已經進入比較成熟、比較穩定的發展階段。
3.3 作者統計分析
3.3.1 合作度與合著率。從統計結果來看,2 732篇論文中單一作者論文1 991篇,占論文總數的7288%。合著論文741篇,合著率 27.12%,高于2000年圖書館學24.1%的合著率,但低于2000年情報學48.7%的合著率[10]。其中2人和3人合著論文數量最多,分別為454篇和173篇,一篇論文涉及作者最多的是8人,其次是7人,但數量均不多(見表4)。就作者重要性[11]評價而言,學科服務、學科館員的核心作者(即以第一作者或獨著發文數量最多)分別是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的初景利和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的郭晶。
3.3.2 作者單位分布。以第一單位計量結果來看,中國科學院系統發文量最多,為58篇;其次是解放軍醫學圖書館,發文37篇;上海交通大學以發文量32篇排在第三位(見表5)。
3.4 影響力即文獻被引情況
論文被他人引用數量的多少是表明論文影響力的重要指標,論文發表后什么時候能被引用、被引數量多少等因素與論文所屬的學科密切相關[12]。論文的被引頻次也是衡量這篇學術論文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論文的高引用率一直都是論文所在期刊和作者希望看到并努力追求的目標之一[13]。對作者而言,高被引論文意味著高的學術影響[14]。統計文獻中,被引頻次排名前十的文獻研究主題集中在學科服務模式研究、學科館員隊伍建設、嵌入式服務等方面,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的初景利、張冬榮發表在《圖書情報工作》上的《第二代學科館員與學科化服務》一文被引頻次最高,達到305次 (見表6)。
“學科服務、學科館員”的研究成果不僅展現了不少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而且培養了圖書情報領域有影響的知名專家,學科高被引作者中,柯平、初景利、李春旺分別位居圖書情報學科的第2名、第7名和第16名[15]。
4研究主題分布及評析
4.1 研究主題分布
關鍵詞是為了文獻標引工作而從學術論文中或學術論文外選擇出來用以表示全文主題內容信息款目的單詞和術語,是未規范的自然語詞[16]。由目標文獻關鍵詞的統計結果來看,學科館員出現頻次有1 885次,位居首位;出現頻次排在第二位的是高校圖書館,達927次;學科服務以出現頻次為423排在第三(見表7)。
分析目標文獻的主題內容,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4.1.1 學科館員角色定位及隊伍建設。范愛紅[17]引入美國學科服務前沿發展理念,介紹了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的最新學科服務特色及對學科館員角色轉型的影響,她認為學科館員要帶著合作的理念融入科研活動的全過程、嵌入課程教學的各個環節、參與到數字館藏建設的相關工作中,其學科特色應該是主動參與、深入過程與多方合作的;初景利等[18]在分析學科化服務背景的基礎上,提出了第二代學科館員的概念以及與第一代學科館員在服務地點、服務邏輯起點、服務深度、服務內容、服務責任、服務手段等方面的區別,他認為學科館員要融入一線、組織一線、服務一線,與服務機構進行責任綁定、服務綁定、創新綁定、考核綁定。
4.1.2 學科服務模式與學科館員制度。龍雪梅[19]為了使圖書館的深層次服務落到實處,在綜合考慮國內圖書館學科服務實情基礎上提出學科服務由學科團隊來完成,學科館員兼任學術秘書之職,設立首席學科館員崗位,采用矩陣管理模式,引入美國愛荷立大學的IC理念,建立學科館和學科數字信息共享平臺以提升學科服務水平,在服務實施方式上,采用先某一重點學科試點后逐漸推廣的辦法;隨后,宋海艷[20]、喻萍萍等[21]以泛在知識環境為背景,提出學科服務模式設想與實踐,宋海艷分析其對圖書館學科服務的影響,并從信息素養教育、學習共享空間、學科服務平臺和知識社區等四個方面探討了學習空間與學科服務融合的模式。胡繼東[22]于2002年探討了學科館員制度的產生背景及發展、實施與完善等問題,并分析了學科館員的素質與職責;李春旺等[23]在解析基于傳統圖書館的第一代學科館員制度基礎上,提出了基于數字圖書館的第二代學科館員制度范式,他們認為第二代學科館員在保留第一代學科館員角色職責的同時,還應該增加學科作者與發布者、信息資源管理者、知識管理員、研究人員以及虛擬交流的組織者等新角色。
4.1.3 高校圖書館學科服務與學科館員的案例分析與實踐探索。最早介紹學科服務和學科館員實施實踐的單位是清華大學圖書館,1999年姜愛蓉[24]介紹了清華大學圖書館建立學科館員制度的具體措施:建立實施機制、制定崗位職責、重視工作落實等;2002年郭依群等[25]介紹了清華大學圖書館1998年率先建立學科館員制度以來的工作實踐,解答用戶咨詢、與對口院系聯系的同時為教授提供有針對性的綜合信息服務,參與電子資源的服務與推廣,參與多層次的用戶教育活動,提供學科網絡資源導航服務,參與圖書館網頁架構建設等。10余所高校結合本單位的學科特點與實際需要,對學科服務模式與學科館員制度建立的實踐進行了介紹,其中湯莉華等[26]、郭晶等[27]、陳啟梅等[28]、陳漪紅等[29]、陳振英[30]、張蒂[31]、王群[32]分別根據所在單位學科特點與實際需要,對上海交通大學、哈佛大學、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浙江大學、南開大學、上海對外貿易大學的學科館員制度建立、學科館員服務特征及營銷策略、學科服務實踐等進行了介紹。
4.2 研究評析
通過以上定量與定性分析,我國學科館員、學科服務研究三十年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研究內容局限在理論。從以上學科館員、學科服務研究主題來看,研究的內容大多集中在對學科館員的素質要求、學科館員的具體職責、學科服務模式以及經驗介紹與羅列等方面,其中不乏重復研究與生搬硬套框架,應多結合本單位學科特點與需求、學科館員構成、現有學科服務層次,引入大數據時代的相關先進技術或電商普及的大信息環境,使學科服務更便捷有效,真正達到初景利等提到的學科服務所要達到的目標[18]。2)研究群體局限在高校。從發文作者分布機構來看,發文量(重要性評價)與被引量(影響力評價)排前10名或前15名的單位除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外,其余均為高校圖書館,這說明數字化與信息時代的學科館員與服務還沒有引起高校以外的更多重視,學科服務對象還有很大的擴展空間與挖掘潛力,未來的研究當中,學科服務與學科館員應面向社會推廣與普及。3)研究視角局限在本土。從目標文獻來看,研究群體大多為圖書館員,這也決定了研究群體大多從圖書館或學科館員本身提供的服務視角出發,而沒有更多地考慮從用戶更深層次的需求方面來提高服務水平,未來的研究應該從學術交流的虛擬環境、虛擬交流方式、學術成果虛擬出版方式等方面考慮學科服務的制度建設與學科館員素質提高,更應該立足本土特色、展望國際視野。
[參考文獻]
[1] 初景利.學科服務概論[EB/OL].[2015-01-25].http://wenku.baidu.com/view/80b12d41336c1eb91a37
5dc3.html.
[2] 學科化服務[EB/OL].[2015-01-25].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o7pey2xG_w0ELxvIgKKos5ql2k
U7m-TWrcJSM_Fxwt78RZeR_bRh1wI_IIqnoRbXCBiVGGn_yUEaelYbKOLsK.
[3] 徐仁海.牧區水利學科服務與研究的對象[J].內蒙古水利科技,1983(2):13—21.
[4] 臧萬杰.高校館面臨的新問題——圖書采購如何為新興學科服務[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83(3):62—63.
[5] 陳京.建立一支“學科館員”的專業隊伍(摘要)[J].贛圖通訊,1987(3):58—59.
[6] 母益人.學科館員應該做好哪些工作[J].河南圖書館學刊,1989(4):27.
[7] 陳汝龍.論高校圖書館的最新變革——實行學科館員與專業集成化服務[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1):103—105,112.
[8] 柯平,唐承秀.高校圖書館學科館員工作創新——兼談南開大學圖書館開展學科館員工作的經驗[J].大學圖書館學報,2003(6):42—45.
[9] 文獻計量學03——布拉德福定律[EB/OL].[2015-01-25].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8EVScTfmIom4R4gsbV9hwAL6-LcR2u7ZS5LSudRix_MBtGZVNnsUguIZG2apMsJxDnM4ew8bW0SWjGxoV8ScASNHgmyD9k53P1kPRm-rOG.
[10] 鐘旭,黃暉,薛健.中國社會科學期刊論文合著率指標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J]. 情報學報,2000(3):280—288.
[11] 鐘文娟.基于普賴斯定律與綜合指數法的核心作者測評——以《圖書館建設》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2(2):57—60.
[12]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10年度中國科技論文統計與分析[M].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2(9):8—9.
[13] 杜秀杰,趙大良,葛趙青,等.學術論文的下載頻率與被引頻率的相關性分析[J].編輯學報, 2009, 21(6):551—553.
[14] 金碧輝,汪壽陽,任勝利,等.論期刊影響因子與論文學術質量的關系[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 2000,11(4):202—205.
[15]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萬方數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中國期刊高被引指數[M].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0:187—202.
[16] 畢強,牟冬梅,王麗偉.數字圖書館關鍵技術的比較研究[J].圖書情報工作,2004,(5):27—30.
[17] 范愛紅,Deborah J.Schmidle.學科服務發展趨勢與學科館員新角色:康奈爾范例研究[J].圖書情報工作,2012(5):15—20.
[18] 初景利,張冬榮.第二代學科館員與學科化服務[J].圖書情報工作,2008(2):6—10,68.
[19] 龍雪梅.高校圖書館學科服務模式構想[J].圖書館建設,2009(4):30—34.
[20] 宋海艷.泛在知識環境下的圖書館學科服務模式與動力機制研究——基于學習空間融合服務的探索[J].情報理論與實踐,2010(7):58—62.
[21] 喻萍萍,儲冬紅.泛在知識環境下的高校圖書館學科服務模式研究[J].圖書館學研究,2011(23):83—86.
[22] 胡繼東.關于學科館員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問題[J]. 圖書情報知識,2002(3):78—79.
[23] 李春旺,李廣建.學科館員制度范式演變及其挑戰[J].中國圖書館學報,2005(3):51—54.
[24] 姜愛蓉.清華大學圖書館“學科館員”制度的建立[J].圖書館雜志,1999(6):30—31.
[25] 郭依群,邵敏.網絡環境下大學圖書館學科館員職責的擴展——清華大學圖書館案例研究[J].大學圖書館學報,2004(5):51—55.
[26] 湯莉華,黃敏.論高校圖書館學科館員制度的完善——由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建立學科館員制度說開去[J].大學圖書館學報,2006(1):45—48.
[27] 郭晶,黃敏,陳進,等.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學科服務創新的特色[J].圖書館雜志,2010(4):32—34,19.
[28] 陳啟梅,張冬榮.哈佛大學圖書館學科服務特色及對我國的啟示[J].知識管理論壇,2013(7):6—11.
[29] 陳漪紅,楊志萍,田雅娟.試析學科館員服務特征及營銷策略——以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為例[J].現代情報,2013(5):60—61,172.
[30] 陳振英.融入主流謀發展 拓展合作促繁榮——浙江大學圖書館學科服務創新實踐[J].圖書館雜志,2011(8):69—72.
[31] 張蒂.嵌入式學科館員的實踐探索及其啟示——以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為例[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2(12):125—128.
[32] 王群.發展合作項目 嵌入科研過程——深化學科服務模式探索[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1(2):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