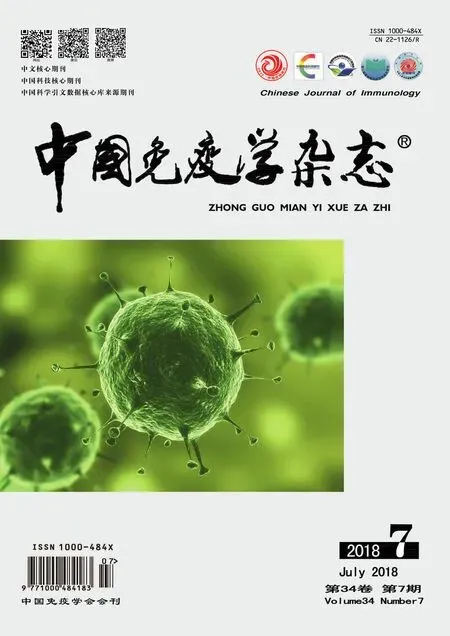腎移植免疫學研究進展
鄭浩鋒 孫啟全
(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廣東省器官移植中心,廣州 510630)
腎移植是目前終末期腎臟病患者的最佳治療方式[1]。對于腎移植術后受者而言,免疫排斥反應程度嚴重影響移植腎存活時間,從而進一步影響受者生活質量[2]。應用免疫抑制劑雖可一定程度上延長移植腎的存活時間,然而移植腎遠期存活仍不理想,移植腎十年存活率僅為50%[3,4]。晚期移植腎失功仍是目前腎移植術后所面臨的最重大的臨床問題[5,6]。對于腎移植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排斥反應、免疫抑制劑的并發癥、缺血再灌注和供體評估等幾方面,而這些研究中,排斥反應尤為重要,也是目前研究最為集中的領域(見圖1)。對于排斥反應而言,免疫系統在其中發揮著核心作用[7,8]。腎移植移植免疫研究,主要包括兩方面,即天然免疫和特異性免疫,其中特異性免疫在移植免疫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特異性免疫,主要包括T細胞與B細胞,其分別造成腎移植后T細胞介導的排斥反應(T cell-mediated rejection,TCMR)和抗體介導的排斥反應(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ABMR)[2]。而天然免疫中包括抗原提呈細胞、損傷相關的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等也在腎移植移植免疫中發揮重要作用[9]。
對于腎移植移植免疫研究,目前我國研究水平與世界一流水平仍存在較大差距。近10年全球發表高質量(影響因子大于5)腎移植論文共3 065篇(截至2018年1月),而我國僅發表46篇,并且僅有不到半數是在國內獨立完成。因此,中國腎移植移植免疫仍有較大發展空間。本文將從腎移植移植免疫角度出發,詳細闡述免疫細胞包括T細胞、B細胞和天然免疫細胞在腎移植移植免疫中的作用,為腎移植移植免疫研究奠定基礎,為今后研究指明方向。
1 T細胞與腎移植
T細胞在腎移植移植免疫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其介導的細胞性排斥反應(即TCMR),其發生機制主要與人類白細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1)有關,外來抗原(主要為移植腎抗原)刺激受者體內免疫系統,激活T細胞(主要是效應T細胞),在其他炎癥因子包括IL-2等刺激下,導致移植腎局部嚴重免疫排斥反應[10]。TCMR可分為間質性和血管性兩種,而根據病程及發病時間情況,TCMR又可分為急性和慢性排斥反應。早期發生TCMR是移植腎預后不良的危險因素之一[11]。

圖1 近10年我國高質量(影響因子大于5分)移植免疫研究論文熱點分布圖Fig.1 Distribution map of high quality kidney transplant research articles (impact factor >5.0) in China within 10 years
移植腎發生TCMR后,其常見病理表現主要為顆粒狀補體沉積、多形核細胞浸潤和微循環內皮細胞損傷,伴或不伴單核細胞浸潤,而小管炎及間質炎則較為少見[12,13]。
對于腎臟TCMR的診斷,目前主要依賴于傳統Banff病理學分級,其分級主要根據間質炎癥程度、動脈炎嚴重程度及腎小管萎縮情況進行分級[14]。Banff分級診斷標準大大提高了腎移植術后診斷及治療判斷水平,然而其也存在局限性。其最大的局限在于Banff分級仍是主觀判別,由于病理學家水平參差不齊,因此往往難以達到一致的診斷。同時,Banff分級與腎移植術后移植腎預后的相關程度也是一個問題[15]。Krisl等[16]對182例TCMR受者進行長達527 d(中位數)隨訪后發現,在移植腎失功上時間上,不同Banff分級包括ⅠA、ⅠB、ⅡA和ⅡB受者,其失功時間并無顯著性差異。同時,Wu等[17]學者也做了類似研究,對270例TCMR受者,包括TCMRⅠ、Ⅱ和Ⅲ級,結果表明不同分級移植腎生存時間無顯著差異,而內膜動脈炎嚴重程度則與TCMR預后高度相關。由于Banff分級的局限性,近年來亦有不少研究嘗試利用其他方法來診斷TCMR,包括改進版的Banff TCMR量表,基因及轉錄組等分子水平等對TCMR診斷進行研究,亦取得較大成就[15,18,19]。
對于TCMR的治療,由于其主要與腎移植術后急性排斥相關,因此其治療要點在于早期足量使用糖皮質激素。TCMR典型情況表現為腎實質出現明顯急性排斥反應、動脈及小動脈栓塞、腎實質梗死。對于此類情況,移植腎往往在1年內會出現腎失功。當發生嚴重TCMR,糖皮質沖擊療法仍是一線療法,對于輕中度TCMR,如對激素沖擊治療有效,則可口服維持,而對于重度或難治性TCMR,則需持續靜脈滴注,同時沖擊后予以抗生素以預防感染,并根據血藥濃度優化免疫抑制劑治療方案[20]。
2 B細胞與腎移植
B細胞在腎移植移植免疫中發揮著重要作用。B細胞介導的排斥反應,又稱為抗體介導的排斥反應或體液性排斥反應。ABMR是腎移植術后免疫排斥反應中存在的最大臨床問題[21]。發生ABMR后,若不及時治療,將會有20%~30%移植腎在一年內失功[22]。其發生機制主要是由于機體抗原提呈細胞提呈移植腎抗原后,刺激B細胞產生抗移植腎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HC復合物抗體(Donor-specific antibody,DSA),DSA與抗原結合反應后進一步激活補體反應,從而造成移植腎損傷[23]。MHC復合分子,在人類其主要指HLAs。至今為止,已發現的HLAs超過1 600種,其大體分為兩類,即HLA Ⅰ類和HLAⅡ類分子。HLA Ⅰ類分子(包括HLA-A、HLA-B和HLA-C等)分布在所有有核細胞,而HLAⅡ類分子(包括HLA-DP、HLA-DQ和HLA-DR等)則只在抗原提呈細胞上表達。除HLAs抗原外,其他抗原包括ABO血型抗原、微小組織復相容性復合體抗原、內皮細胞抗原等也可刺激機體產生抗體,從而導致ABMR的發生[23-25]。在ABMR的發生發展中,抗原抗體結合反應并不能直接造成移植腎的損傷,其最大的損傷機制在于抗原抗體結合后引起的補體反應。補體分子,尤其是C1q可結合移植腎內皮細胞上的抗原抗體復合物,形成膜攻擊復合物,從而引起補體系統的激活,造成細胞損傷,甚至死亡。而在此過程中,補體反應的激活也會產生部分趨化因子,從而導致移植腎免疫細胞的浸潤,包括中性粒細胞和巨噬細胞等,從而造成移植腎進一步損傷[26-29]。在補體反應后,常常會殘留補體片段C4d,因此其也成為ABMR發生的重要標志之一[30]。
移植腎發生ABMR后,其病理改變與TCMR截然不同。在ABMR中,其受損部位主要為腎小管與內皮細胞。在管周毛細血管可見明顯中性粒細胞與巨噬細胞浸潤,同時腎小球與毛細血管可見明顯炎癥[31]。而在我們前期研究中發現,ABMR中毛細血管炎的發生發展主要與T-bet有關。在Th1的調控下,T-bet的產生與炎癥細胞浸潤及毛細血管炎呈正相關[32]。
根據發病時間和嚴重程度,ABMR可分為超急性、急性和慢性排斥反應,而不同排斥反應其病理表現不一。對于超急性ABMR,其主要表現為內皮細胞表面大量免疫球蛋白沉積與內皮細胞溶解,從而導致血栓形成與組織梗死。活檢可發現炎癥細胞浸潤、紅細胞停滯、纖維素沉積以及廣泛腎小管損傷壞死等。對于急性ABMR,其主要表現為中性粒細胞遷徙到腎小管周圍毛細血管內,從而造成腎小管壞死及動脈纖維素樣壞死。慢性ABMR則主要表現為微血管的慢性病變,包括動脈內膜纖維化、腎小管周圍毛細血管基膜分層等[33,34]。
對于ABMR的診斷,目前也主要依賴于傳統Banff病理分級診斷[35]。1990年,ABMR由于其獨特的病理學表現而從TCMR中區分而來[36]。由于C4d為補體反應激活的標志,其長期作為ABMR標志物,直至2009年加拿大大型腎移植術后排斥反應研究才發現,大部分ABMR受者腎臟病理染色C4d陰性,自此,ABMR的診斷才得以進一步完善[5]。在Banff診斷標準中,ABMR根據其病程長短,可分為急性和慢性ABMR,其診斷依據主要包括三方面,即DSA檢測、C4d檢測以及管周毛細血管炎和腎小球炎[35]。對于DSA檢測,目前主要依賴細胞毒試驗或ELISA,然而其僅能檢測出抗HLA類抗原,對于非HLA抗原等缺乏標準化篩查手段。我們前期利用商品化人臍靜脈內皮細胞,建立抗內皮細胞抗體篩查方法,解決了抗內皮細胞抗體的檢測問題,并進一步揭示抗內皮細胞抗體所致的體液性排斥的臨床特征,研究成果也被國際指南采納,成為全球唯一的篩查手段[37-39]。由于臨床上存在部分受者DSA陽性而不發生排斥反應,因此單獨DSA檢測并不能成為ABMR確診的唯一依據。而對于C4d的檢測,目前主要依賴免疫熒光或免疫組化。C4d陽性是ABMR預后不良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對于C4d陰性的受者,其如果腎小管周圍毛細血管存在較多炎癥細胞浸潤,則可結合其他提示ABMR的分析生物學指標,包括C1q和C3d等進行協助診斷[40]。此外,對于ABMR的診斷,近年來在基因分子水平及體外無創診斷亦取得十分顯著成就[41-43]。基于前期研究發現T-bet在ABMR中的重要作用,我們進一步研究發現,利用T-bet與GATA3這兩種在ABMR中起重要作用的分子,其比值可作為ABMR診斷的重要指標,相比于傳統C4d診斷ABMR,其可顯著提高體液性排斥診斷的臨床敏感性,而聯合C4d與T-bet/GATA3診斷ABMR,可在不減少C4d診斷特異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ABMR診斷的靈敏度,為臨床ABMR早發現提供可靠檢測手段[44]。
ABMR的治療一直是腎移植術后所面臨的最重大難題。近年來,大量研究集中于新型免疫抑制劑,包括CD20單抗、IL-6受體拮抗劑、蛋白酶體抑制劑等的開發使用。然而ABMR為持續進展性疾病,不同時期ABMR由于其癥狀表現不一,其治療策略應有所差異[25]。我們前期研究發現,ABMR可分為早期及晚期,其分期標準主要根據時間,即6個月內為早期ABMR,而6個月后為晚期ABMR。對于早期ABMR,聯合霉酚酸酯與他克莫司可有效對ABMR進行治療。該方案在減少免疫抑制劑感染等副作用前提下,安全有效治療ABMR,且進一步降低受者醫療支出[44,45]。而在后期研究中,我們發現調節性T細胞及傳統中藥雷公藤亦可有效減輕ABMR受者排斥情況[46,47]。
3 天然免疫與腎移植
天然免疫是腎移植術后排斥的必經階段,也是適應性免疫的必要條件。長期以來,腎移植移植免疫聚焦于T細胞和B細胞所介導的適應性免疫,而天然免疫細胞所介導的天然免疫鮮有涉足。對于天然免疫在移植免疫中的作用,目前主要集中于腎臟缺血-再灌注損傷研究,而在腎臟移植免疫耐受方面,其也有少量研究。
在腎移植免疫中,天然免疫細胞通過模式識別受體識別病原體相關模式分子,例如脂多糖和肽聚糖等,產生促炎因子造成炎癥損傷,同時激活適應性免疫。模式識別受體種類多樣,大體可分為兩類,即細胞受體和可溶性受體。細胞受體包括Toll樣受體(Toll like receptor,TLR)、NOD樣受體和RIG-I樣受體,而可溶性受體則主要為補體[48,49]。
DAMPs是天然免疫識別的重要損傷物質,其主要由損傷或衰老細胞產生,經樹突狀細胞等抗原提呈細胞識別后,可通過抗原提呈細胞上的細胞受體,尤其是TLR受體,進一步產生炎癥因子,誘導炎癥的發生,從而在腎移植天然免疫中起重要作用[50-52]。線粒體DNA是DAMP重要組成成分,近年來,其在移植物炎癥中的作用也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研究表明,線粒體可通過釋放線粒體DNA,作用于TLRs和Ⅰ型干擾素而激活炎癥反應。而在心臟移植研究中發現,線粒體可以打破共刺激阻滯所引起的免疫耐受[53]。天然免疫是機體免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其在腎移植免疫中的作用,仍需進一步挖掘研究。
4 異種移植與腎移植
供體數量短缺是腎移植及器官移植所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針對供體數量的短缺,大量科學家集中于異種移植研究。長期以來,異種移植面臨的最大問題包括以下四方面,即免疫排斥反應、凝血調節功能障礙、中間交叉感染及倫理問題。靈長類動物由于與人類血緣相近,無疑為異種移植的潛在對象,然而由于其常常攜帶有人類易感病毒,且來源少、繁育周期長,在實際應用中反而較為困難。相比之下,基因修飾豬似乎是異種移植的最佳來源,其腎臟具有與人類相似的大小與解剖,而腎功能亦相近[54]。近年來,大量研究集中于豬的基因改造,而CRISPR/Cas9技術的出現,為腎移植異種移植翻開了新的篇章[55]。經CRISPR/Cas9技術,基因修飾豬可一次性敲除超過40個基因,其不僅解決了異種移植中存在的交叉感染及凝血調節功能障礙問題,而且在CD55等補體調節蛋白輔助下,天然抗體介導的免疫排斥反應亦可顯著降低[56]。基因修飾豬的出現將異種移植帶上了新的高峰,然而其距離臨床應用仍有漫長的路程。遲發的排斥反應、移植物術后長期功能及倫理認可,仍是異種移植所面臨的重大難題。
5 免疫耐受與腎移植
免疫耐受,主要分為兩大類,即自發耐受和誘導耐受,其最早于1953年由Billingham等[57]發現,在小鼠胎兒期接種外來組織,則可誘導小鼠皮膚移植免疫耐受。對于免疫耐受的機制,目前主要認為其由B細胞和T細胞介導的中樞耐受及天然免疫細胞介導的外周耐受兩部分組成。長期以來,免疫耐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動物體內研究,然而由于種屬差異,大部分動物實驗結果無法在人類身上進行重復[58]。在腎移植中,至今已有報道超過100例免疫耐受患者,而最新研究發現,除已存在的天然免疫耐受患者,亦可人工誘導腎移植免疫耐受[58,59]。國內外多所醫院包括美國麻省總院、美國西北大學、斯坦福大學和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腎移植專科分別進行了造血干細胞輸注聯合腎移植誘導免疫耐受的臨床研究。其于術前對腎移植受者進行全淋巴放射預處理,同時輸注供者的造血干細胞。結果表明,部分患者術后可完全停用免疫抑制劑,成功誘導免疫耐受。而在后期研究中發現,輸注造血干細胞后受者體內長期存在“供-受者嵌合體”,其可保持受者免疫系統對移植腎呈低免疫反應或無反應,大大降低或減少術后免疫抑制劑使用量,極有可能成為腎移植免疫耐受的新治療方案[60-62]。
6 總結
腎移植移植免疫為復雜的網絡免疫調控系統,各種免疫在發揮其單獨作用時,彼此之間也相互作用。天然免疫作為機體免疫的第一道防線,在發揮其免疫效應的同時,也可激活適應性免疫;而適應性免疫發揮作用時,也可通過釋放趨化因子等進一步加強天然免疫效應,從而起到正反饋作用。移植免疫研究是解決腎移植術后排斥、延長受者生存時間、提高受者生存質量的重要手段,而免疫耐受研究則是解決腎移植術后排斥的明日之星。然而目前腎移植免疫研究仍有較大發展空間,高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如單細胞測序、轉錄組學、代謝組學等,將使腎移植移植免疫走向一個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