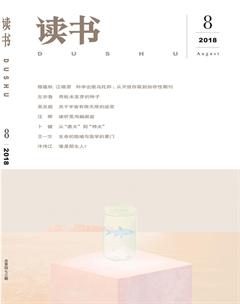君子讀史
李成晴
二0一七年九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重版了陳寅恪先生手書《后代政治史略稿》的典藏本,可謂是“再造”善本的又一范例。該版于書末附載了陳寅恪寫給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的十四通書信,并有高克勤先生的細致考證,對我們了解陳寅恪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著作出版的史事頗有裨益。
最近,筆者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陳寅恪手書《唐代政治史略稿》與民國商務印書館本《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民國三十三年重慶初版以及三聯版《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幾種重要版本進行對讀,掃葉拂塵之余,也對陳寅恪“兩稿”中的現世關懷有了初步的體會。黃庭堅曾評價陳師道說:“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脈絡。”后來,也有學人用這句話來形容陳寅恪的史學格局。大禹治水,在了然于天下脈絡的前提下,解決的仍是“現世”最迫切的問題。同樣,陳寅恪“兩稿”所揭橥的,自然是中古史上的大關節,但他在“兩稿”中的現世省思,也具有不遑多讓的恒久價值。陳寅恪曾有心撰著《中國通史》《中國歷史的教訓》,意在總結國族與文化的得失之鑒,可惜都沒能動筆。不過,“兩稿”中已然隱隱透露著他以史為鑒、“在史中求史實”的自覺意識。更為深切的是,陳寅恪在“兩稿”中還時常跳出史料之外,用一種沉靜的筆調思考,在“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時,士人的身份認同以及立身處世的楷則與底線。
在手寫本《唐代政治史略稿》的中篇,陳寅恪先考論了牛李黨爭局勢下的士人遭際,隨后,筆鋒一宕,寫下這樣一段話:
君子讀史,見玉溪生與其東川府主升沈榮辱之所由判,深有
感于士之處世,外來之變態縱極紛歧,而內行之修謹益不可或闕也。
在陳寅恪看來,隨著牛李黨爭的公開攤牌,“當日士大夫縱欲置身于局外之中立,亦幾不可能”。其中有兩個例外,一是白居易以“消極被容”,二是柳仲郢以“行誼見諒”。其他士人如李商隱,出入于牛李兩黨之間,最終為兩派皆所不容,導致“坎壈終身”。陳寅恪有關“君子讀史”的這一段議論,通過著書余瀋,遙遙地與當時及后世的一代代士人共勉。從另一角度看,這也是對自己立身行誼原則的“夫子自道”。士人之行止出處,不論時代和地域,面臨的根本問題都是近似的。世事之轉軸波詭云譎,士人應當知恥自守,或跳出風向之外,像白樂天那樣以“消極”為擋箭牌,專注于心中認定的作述之業;或臨風而不動,像柳仲郢那樣敦篤“行誼”,光明磊落。士人如果看穿了白頭宮女“眉樣如今又入時”的哈哈之笑,也許就能避開人格上的“倡優蓄之”,獨立不懼,遁世無悶,正所謂“太上有立德”。陳寅恪早年所作詩有“士有相憐寧識面”一語,他對李商隱無疑寄托著“同情之理解”。若非如此,他后來何以又寫出“玉溪滿貯傷春淚,未肯明流且暗吞”的詩句呢?
陳寅恪所言“君子讀史”,字字皆有來歷。自從《左傳》論贊以“君子日”引端以后,“君子”一語就天然地與持獨立立場的史家聯系在一起。士人于內行則以“修謹”自律,于外行則以“事功”自勉。不過,“事功”之果能實現與否,并非個人的努力所能決定,就如同孔子當年的不為“匏瓜”也無濟于事。所幸的是,古儒傳統有著精神上的退路,那就是著書立說,所謂“其次有立言”。在《唐代政治史略稿》的手寫本中,我們即可以讀到陳寅恪對君子“立言”的鄭重態度。《新唐書·儒學傳》記載,孔至撰《百家類例》,沒有將張說一門歸入禮法儒素傳家的世家舊族,而是據實剟入“近世新族”,這招致了張說之子張垍的不滿。張垍之弟以實相告,孔至感到憂懼,“欲更增損”,以氏族學名世的韋述聽聞后,說:“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
陳寅恪手寫本論進士詞科之同門關系時,曾引《大唐新語》載玄宗稱張說“如卿豈有門籍”(手寫本,184頁),來證明始興張氏實為以文學進用之寒族,并沒有征引《新唐書·儒學傳》的這則史料。不過,后來增訂時,陳寅恪在《大唐新語》后增補了《國史補》《新唐書·儒學傳》的記載。就考史立論而言,韋述之語與史證無關,可節略不引,但陳寅恪卻沒有割棄(三聯版,294頁),當是有感于韋述之語對獨立自由人格的守持。接下來便是為世人所熟知的故事。上世紀五十年代,陳寅恪的著作本可很快再版,但因他對舊稿中有關高麗、朱溫的稱呼堅持不改,致使出版事宜多波折。最近,《上海書評》刊發曹金成、李淼《陳寅恪致季羨林未刊信一通考釋》一文,是《陳寅恪集》失收的新史料。在一九五三年寫給季羨林的信中,陳寅恪第一條強調的就是,自己寄往京華友人的兩篇論文“俱保留修改權”,也就是說,不同意他人對自己的論撰加以改動。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民族文化處于兩重危機,內在則眾枝叢雜、本根不振,外在則啟蒙中斷,國本有戕伐之患。在陳寅恪看來,歷史上,種族文化所經歷的“辛有、索靖之憂”,有更甚于當下者。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陳寅恪提請世人注意,漢、魏、西晉都曾傾覆,但其學術文化卻得以保存在河西一隅之地,并最終成為隋唐文明制度之一源,所謂“河西遺傳”。陳寅恪在《禮儀》篇中特意標識:“草此短篇,藉以喚起今世學者之注意。”
言辭中有著明確的現世關切。王永興在《陳寅恪先生史學述論稿》中曾加以闡釋,認為陳寅恪重視“河西遺傳”,實際是暗示當時的同儕學人,內遷西南,歷史性地背負上了厚重的文化承擔,所謂“吾儕所學關天意”,應當在西南天地之間“繼絕扶衰”,保存華夏文化于一線。王永興這樣遙想陳寅恪修訂《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的場景:
可以想見,春城四月的深夜,靛花巷小樓先生的居室,燈還亮著。雖先生體弱,又在大病初愈,他仍坐在書桌之前。桌上擺著此書的稿本,先生一字一句檢視,不時查閱各種書籍,在再三思考之后,執筆修改,有時苦思冥想,如何把我國的傳統學術文化保存于西南一隅,如何喚起更多的學人明了這一點,把華夏民族的命脈延續下去。
就在陳寅恪修訂《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一九四二年,他別撰序文《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其中談到自己與陳垣在國難離亂中的立身處世:“先生講學著書于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間,南北相望,幸俱未樹新義,以負如來。”陳寅恪將自己在西南的輾轉流徙,比作杜甫在“安史之亂”時“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他所看重的,是兩人沒有像支愍度那樣樹新義以“負如來”。在乾撼坤岌之際,陳垣有感于“世變日亟”,于是授課改講《日知錄》,對其中的經世致用之學進行表微。北平淪陷后,則又希望通過講“全謝山之學”以振起士氣。與陳垣相較,陳寅恪的“兩稿”的現實省思更加含蓄,不過他的知交和后學往往能從“兩稿”中讀出“古今之變”的通識。
透過“兩稿”偶爾透露出的現世關懷,我們當能體會到陳寅恪提振士林志氣,以古儒精神共勉的“熱心”。但他留給后世的印象,更多的卻是一生負氣,執拗孤冷。陳寅恪的文字,不論是詩歌還是論撰,都有著一種孤獨與痛苦,沉靜卻又悲憫。北宋時,有一位學者崔子方,也是黃庭堅的知交,隱居真州六合,專治《春秋》義例之學。一次,徐積問江端禮:“崔子方秀才何如人?”江端禮回答:“與人不茍合,議論亦如此。”徐積聽了,說:“不必論其他,只‘不茍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此語似可移評陳寅恪的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