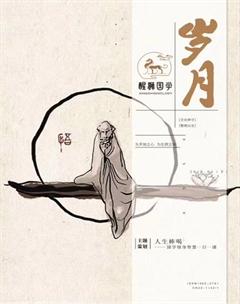藏地飲茶記
編者按:自2015年8月17日啟程,雛菊穿越中國之行正式開始。這一路她帶來風景、帶來艱苦,她痛并快樂著,她展示著她的堅強毅力,使男人們都為之傾服。
把茶喝出泥土的味道來
作為一個喝茶者,或者一個茶人,圈子內有太多專家都在告訴你或者等著告訴你,茶是怎樣的,應該怎么喝。
但是,他們忘記了一件事:你是誰,你應該怎么喝茶。
而你必須常常自問:我是誰,我想要怎么喝茶。
品味一片普洱茶,講究平衡,而喝茶也莫不如此:人也重要,茶也重要。
每一個對茶抱有美好愿景的人,內心都應該會有自己的幻想和渴望,我相信你也一樣。喝自己覺得舒服的茶,做自己想做的事。認定這件事,然后看著它,移動腳步。努力追逐夢想的道路一定布滿荊棘,但是風雨過后的彩虹才是最動人的吧。
身穿茶服或者海派旗袍,琴香花茶,萬事俱備,手握茶杯送茶湯入口,朱唇微啟;也不是說穿著高跟鞋,畫著紅唇,如赴一場約會,送茶湯進口,杯壁上留下唇印一枚;隨性穿著,或盤腿或二郎腿坐于茶臺前,于對面的兄臺討論山頭、口感最后至茶業之未來前景,推杯換盞間,檣櫓灰飛煙滅;風塵仆仆,疲憊萬分,端起一大杯,干了,把嘴巴里的沙塵盡然洗去。
無論什么樣形式,都是喝茶,只是我獨偏愛一種。
我喜歡或者更為準確的說是我想要的是那種自在舒適的狀態,喝茶也好,旅行也好。喜歡在路邊喝茶,在飯桌上喝茶,在灶火前喝茶,甚至在樹上喝茶,尤為喜歡在翻山越嶺后進入山谷,風塵滿面的坐下來,煮一鍋雪山水,沖進杯中,茶香四周,整個山谷,都變得親近起來。
朋友問: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說:我要去接觸大地,
把茶喝出泥土的味道來。
茶和摩托車的騎行藝術
提起筆開始寫這篇文章的此刻,我的旅程正停留在香格里拉。
在為期兩個多月的摩托旅行的旅程尾聲,在昨天拜訪完香格里拉深處某個制陶的村莊后,在思緒被現代文明與古老手藝兩者間拉扯下,突然有提筆寫的沖動。
是在從飛來寺前往香格里拉的路上,下午四點左右,距離香格里拉約30多公里的路邊看到了去往湯堆村的指示路牌,由國道拐進省道,沿著變窄的盤山公路繼續前行,路邊無任何指示說哪個是湯堆村,約10公里左右時覺得不對勁,折往回走,問路人,接著再拐到一條更窄的鄉間小道上,村子真美,群山環繞,風景如畫。正值豐收的秋季,青稞已經收割完畢,田地已經耕好,牦牛在農田里甩著尾巴吃草,頭頂的太陽仍是金燦燦。
由于村子中無任何指示或跡象顯示這里是制陶的,更沒有任何關于大師級的老工匠孫諾七林的家的指示。烈日下,穿著6條褲子,6層上衣熱的渾身大汗的我,騎著摩托在羊腸道遍布的村子里轉了半個小時有余,連問帶看,終于找到。而老人已于兩個多月前因為高血壓去世,現在由其兒子接手土陶的制作與售賣。
尼西,在藏語中意為太陽升起的地方,是以前茶馬古道的必經之路,制陶歷史據說已兩千多年,至今從未中斷。
不使用轉輪,不用窯子燒,不使用現代技術,一把自制的木頭工具、一方木案,和幾片木板底座,就是所有的生產工具。天氣好時,在空地上生堆火,把曬干胚子放進火里,燒個幾十分鐘,燒到像鐵一樣通紅,拿出來放我一堆木屑中不一會便成了黑色,算是自然上色,就好了。
據說以前還需再用一種酸奶水和青稞混合的液體洗下陶器內部,去除雜質,成品才算完成。這次去發現沒有這道程序了,土陶變為黑陶之后,直接售賣,回家自己需要開水或米湯煮一下。
燒制的器具也多為廚具類的生活用品,酒缸、鍋、茶壺、茶杯等,茶壺一直用來裝酥油茶,現今游客買了去盛酒用,置于廳堂上,獨有其味。
黑陶燒制的這類用品,以前茶館中也在使用,但由于現代文明的到來,一些更方便快捷的器具代替了土陶在茶館中的位置。現今大抵都是藏人自己在家中使用,還因為舌尖上的中國的熱映,使的尼西黑陶成為燉雞神器,土鍋變得空前熱火,國道的路邊都是售賣尼西土鍋,甚至孫諾七林的工作室也是以土鍋為多,茶壺這類曾經占主導位置的物品也自覺退到了土鍋后面。
茶葉向來在藏區都是生生不息,在藏區隨處可見的便是街頭茶館,無論是熱鬧非凡的拉薩市區還是荒無人煙的無人區,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茶館,有茶館的地方就可以窺得許多他們的日常生活比如從木碗、土陶這類器具看到生活環境與手藝流向。不過這也是在以前,現在的茶館也相對潮流了些。
拉薩光明茶館,每個人去臺子上拿一個杯子,找位置隨便坐下后,有巡回加茶的人員,加一杯收一次錢,錢放在桌子上隨便拿。可以一坐就是一天,也可以逛街累了來歇歇腳。巡回加茶的工作人員手中盛放酥油茶和甜茶的器具已經由陶、鐵變為暖瓶,手里拿著的杯子也由木碗變為玻璃杯。由最初的3毛一杯,變為5毛,再變到現在的7毛一杯,變了很多,但不變的是人們始終保持喝茶的習慣。
當茶葉變成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類似佐料一樣的平易近人時,家家飲茶人人喝茶,想必也不會是什么難事。
與他閑聊至傍晚時分,起身告別。本來想去旁邊的村落再探尋下,無奈夕陽將至,最終作罷,在摩托的轟鳴中踏著夕陽離開。
編輯/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