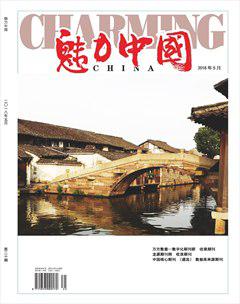濁世中的一曲清歌
摘要:世人大多看到的是袁宏道閑適與歸隱的一面,卻疏忽了他其實亦有一顆拳拳的赤子之心。本文以“清”為立腳點,從生活、為官、詩論三個方面論述袁宏道“清“的特點,講述他在無力扭轉昏暗的朝政的情況下,只得“遠濁世以自藏”,過著寄情山水,攜三兩好友,品茗論道的生活,這樣閑適、曠達的生活態度使他于濁世中脫穎而出,成為一抹不可多得的清亮之色。
關鍵詞:清;禪理;性靈;趣與真
一、生活中的一介清雅之人
山水為文人提供了一個安生立命的處所,禪悅提供的則是一種自定的方式。與眾多晚明文人一樣,生性灑脫的袁宏道在生活中是一介清雅之人。他的清雅,既有寄情于山水的清逸,又有著醉心于禪學的清通。
《四庫全書總目<增定玉壺冰提要>》中提及“山人墨客,莫盛于明末之時,刺取清言,以夸高致,亦一是風尚也。”晚明的隱逸之士數量之多,蔚然成風。袁宏道醉心于山水,一則是對山水的喜愛,二來何嘗不是與朝堂的一種對抗。作為一位極具個性的文人,袁宏道對山水有著獨特的情懷。在摩山畫水之中,充滿了清雅與淡然。山水,隔絕了塵世的紛擾,讓心靈得到片刻的寧靜,山水之景是變化之景,變化的山水為作者預留了巨大的想像空間,使作者擁有了自由與輕快的感受。袁宏道在詩文中描寫了自己觸目的風景,如同一位翩翩君子,游覽人間各處,寫下自己的所思所感,同時,顯現出自己的灑脫,有種飄飄欲仙的意味。“是時七月初,寒肌如粟子。引指人人危,回家面面鬼。歸來問童仆,髭須白余幾? 破網取珊瑚,判命競奇傀。”這首詩中則表現出此處風光的驚險以及自己游覽后的心驚肉跳之感。
袁宏道很早的時候就從禪宗中尋求精神的寄托,以禪釋儒。當他十九歲時一病三月,身體極為贏弱。為了消解對死亡的恐懼、尋求精神上的自由與解脫,袁宏道借助于佛老思想。他曾筑“柳浪館”于公安城南,一住就是六年,期間與朋友談論佛道,他的詩歌,不僅僅以禪理入詩更以禪境入詩,“閑言說知己,半是學禪人。”棲心佛道,遁跡禪門,這確實是晚明文人共同的思想歸趣,他們醉心于禪學,一來忘卻塵世的種種紛擾,二來提升了自己的佛學修為,便于將儒釋道融會貫通,為自己的精神尋找到休憩之處。
二、濁世中的一顆清澈之心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人們往往偏愛盛世,不愿觸及亂世的悲歡,殊不知興盛是一種發展,亂世亦是一種發展。“國家不幸詩家幸”亂離的社會往往更能激發文人騷客的才情。晚明帝王的種種劣行,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隱患。在朝官員朋黨之爭激烈,宦官弄權,整個朝堂可以說是一片烏煙瘴氣。
這便是袁宏道所處的時代。雖然在短短一生中, 他曾三仕三隱,但是袁宏道為官清廉,一心為百姓謀事,深受眾人愛戴。例如袁宏道在吳縣任官期間,寫的《述內》 一詩:“世人共道烏紗好,君獨垂頭思豐草。不能榮華豈大人,長伏蓬蒿終凡鳥。富貴欲來官已休,兒女成行田又少。盈篋算無千個銅,編衣那得一寸縞。陶潛未了乞兒緣,龐公不是治家寶。玉白冰清欲何為,不記牛衣對泣時。”他借述內來的口吻,來顯示自己為官的清廉。他也曾寫下《江漲》、《江南子其五》、《初夏同江進之坐孫內使池臺感賦》等詩,寫出了民間疾苦。當他發現為官之路與自己所追求的閑適相背而馳時,“男兒生世間,行樂苦不早。如何囚一官,萬里枯懷抱。”(《為官苦》)自己又無力對所處的濁世做出改變時,便毅然辭官,遠濁世以自藏,不與世同流合污。
古有謝康樂醉心山水的無奈,陶潛“采菊東籬”的悠然;近有袁宏道尋求山水之樂與苦研佛法之趣,文人們總在為自己尋求著一個心靈的休憩之所,來保持自己的清澈之心。
三、文壇中的一抹清新之意
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中說道:“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于志,莫非自然。”詩歌傳遞的是一種內在的感發與感動。然而縱觀明代詩壇,先是臺閣體歌頌圣德之風、再是粉飾太平的創作風氣彌漫文壇,接著便是前后七子高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旗幟,提倡復古,無奈卻深陷蹈循的圈子卻無法自拔。袁宏道“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主張的提出,為文壇增添了一抹清新之意,而“真”和“趣”亦為他的詩歌增添了一絲靈動。如果說李贄的“童心說”是一種新興思想的話,那么袁宏道的“性靈說”則文學領域里掀起的一種詩歌審美標準。而“真”和“趣”則是衡量作品的兩把標尺。
在袁宏道看來,文學創作首先得“求真”,“真”代表的是個人的才氣于性情, “興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在袁宏道作品中,這種“真”隨處可見。例如,袁宏道早年的時候,他和眾多讀書人一樣,渴望求取功名,報效國家。“寒氣沖筵入,鄉心冒酒生。經年事奔走,名利一無成。”(《夜坐別彭子》詩歌直露無遺的表現出作者渴望建功立業的心情。當他出任吳縣時,對于外放的無奈亦在文中流露。例如《登高有懷》“秋菊開誰對,寒郊望更新。乾坤東逝水,車馬比來塵。屈指悲時事,停杯憶遠人。汀花與岸艸,何處不傷神。”直指在朝為官的幸苦與無可奈何。其次,袁宏道認為“趣”是自然本性和欲望的真實流露。 “聞說山陰縣,今來始一過。船方革履小,士比鯽魚多。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羅。家家開老酒,只少唱吳歌。”(《初至紹興》)詩歌以輕松舒展的筆調描寫了當地的風土人情,饒有生活意趣,閑適與歡快的氣氛,在詩歌中溢出。在詩中,我們不難發現袁宏道的戲謔,不論是描寫志趣愛好,還是抒情寫景,皆追求一種清新灑脫,意趣橫生的創作效果。
袁宏道“性靈說”的提出,在文壇掀起了一場文學風暴。在詩歌模擬之風盛行的明代,確實如一曲清歌照亮了渾濁的文壇。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袁宏道的一些作品過于直率淺俗,讀之詩味盡失,再加上作者不經意的創作態度,以至于“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破壞了作品的藝術美感。
作為濁世中的一曲清歌,袁宏道的詩對詩壇模擬之風起到強有力的沖擊,滌蕩著文人士大夫的心靈。,盡管晚明時期人性解放的思潮縱放了文人士大夫們的性靈,他們不斷努力,掙扎,終究無法真正建構起新的的人格理想和思想體系。公安派的作家在創作時不免有矯枉過正之嫌,這使得詩歌詩味盡失,流于直白,著實令人遺憾。
參考文獻:
[1]胡遂:《佛教與晚唐詩》[M].上海:東方出版社.2005年
[2]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唐昌泰:《三袁文選》[M].四川:巴蜀書社.1988年
作者簡介:樊紅紅(1993—)女,漢族,山西呂梁人,遼寧大學文學院2016級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