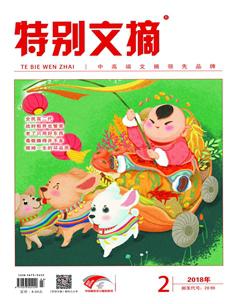我們的文化并不脆弱
我們中國是一個在文化上充滿了優越感的國家,可是近200年來,中華民族經歷了空前的危局。中國文化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當我們一遇到西方的船堅炮利——這種強大的、機械化的軍事力量、物質力量、商業力量,和我們中國一直得益于自己所講的“仁義禮智信”——我稱它為古道熱腸,兩者碰撞上了,就出現了大變局。
香港回歸的時候,謝晉先生執導了一部電影叫《鴉片戰爭》。影片中,謝晉有很深刻的思考。里面有一些令人非常痛心的畫面:英國議會辯論,要不要對中國出兵,一票之差通過了。在這些議員發言的時候,有一個議員拿著一個挺大的瓷器說:“你們看見了嗎?這就是中國!”然后狠狠地往地上一摔。電影結尾,是道光皇帝帶著他的兒子、女兒、孫子、曾孫,在大清的祖宗牌位前哭成一團——說對不起祖宗。挫折、焦慮、失敗、救亡變成了這一時期文化的主題。
高強度的文化焦慮必然會推進選擇一種文化激進主義,把已有的文化成果視為毒藥,視為垃圾。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猛烈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上一個賽一個。吳稚暉,國民黨的元老,提出來把線裝書扔到茅廁里去。魯迅答記者問,給青年推薦什么書,他說:“我以為要少或者就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更激烈的錢玄同,說“人過四十,一律槍斃”“廢除中文”。呂叔湘先生的名言是,我們中國一定要讓漢字加封建專制主義被民主加拉丁化拼音文字所取代。
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拯救了中國的文化。因為如果你不接受這些新的觀念的沖擊,那么中國至今仍然處在晚清的窩窩囊囊的狀態中。我們現在講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也經過了一個很長的過程,十八大所提出的那些詞:“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嗎?正是五四運動,引進了許多新的文化。雖然它激烈一點,雖然有些具體的說法和做法現在不可能按它那個辦,但是,它賦予了中國文化以新的生命,激活了中國文化那些最積極的部分,它推動了中國文化的重生。這里我要談到一個觀念,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和世界先進文化的對接。這是可能的,中國文化從來不拒絕吸收外來的影響。
比如說北京,北京的語言吸收了滿語、蒙古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很多人現在都不知道。北京有很多說法,管“犄角”叫“旮旯”,這是滿語。北京人喜歡吃的一種點心,叫薩其馬。“薩其馬”是蒙古語“狗奶”的意思,至于現在它是不是用狗奶來做是另外一個問題。北京話還吸收了大量的阿拉伯語。回民認為人死了變成羅漢,羅漢就是阿拉伯語“roh”,與佛教的“羅漢”無關,就是精神、靈魂。芫荽是一個怪詞,這兩個字沒有別的講法,是專門造的字。一個“草”字頭一個“元”字,一個“草”字頭一個“妥”字,這兩個字必須連在一塊兒用。“芫荽”是阿拉伯語,是從西域來的。
最主要的是,中國文化有一種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最古老的《易經》上,它就給你來一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個不得了的呀,這就是中國文化能夠和現代性銜接的陽光大道。《尚書》上講“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中國還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是鼓吹改革的呀,中國人的腦筋不死。
(摘自《文化掂量:王蒙最新演講錄》 花城出版社 圖/黃文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