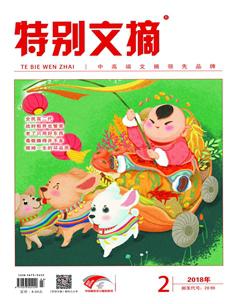安排
2018-08-08 11:19:42陳四益
特別文摘 2018年3期
陳四益
官做到了一定“高度”,退休之后就要“安排”。安排什么?安排一個雖不是官,也近于官的位置,比如到什么協會、學會去當個會長、副會長之類。這好像已經成為上上下下的通例。這些所謂“民間團體”或曰“非政府組織”,成了退役官員安置所。
按說,政府官員和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yè)從業(yè)人員不過是職業(yè)的區(qū)別,在職時崗位不同,退休后都是退休金領取者。他人不必安排,何獨官員而且是較高級別的官員就要“安排”?
或許是覺得當過一陣子官,深諳官場套路,可以輕車熟路地保持高度一致?或許覺得既然官都當得,學會、協會豈不更是小菜一碟?又或許因為社會是官本位的社會,退休的官員自然就應當有點特殊的優(yōu)惠,把“安排”當作一種安撫和照顧。但把退役官員成批地“安排”到非政府組織或民間團體擔任領導職務,其結果多半是把這些民間組織變成了“二政府”,因為官員們大多(說的是“大多”)會把政府工作的那一套程序原封不動搬到民間組織,從而使民間組織平白地多了許多官氣、衙門氣,包括目前政府部門的那些不良風氣。而非政府組織之所以能夠擔負政府部門不能擔負的作用,就是因為它是“非政府”——它的工作內容和運作方式不應也不能混同于政府。當然,官員下野,余威仍在,可以利用關系給這些協會學會弄點錢,但這恰是把官場的不良風氣擴散到了民間。
永厚先生畫了一堆鴨蛋,題款卻作“衙蛋”。“鴨”和“衙”,一音之轉,但破殼而出的卻大為不同,從“衙蛋”里出來的,只能是一堆“二政府”——許多新事物,經過我們的程序孵化,結果都是老面孔。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種社會現象。
(摘自《雜文月刊》 圖/游飛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