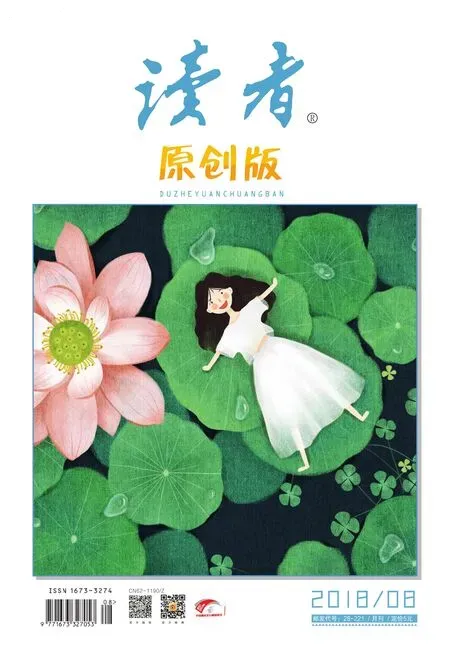深夜,孤獨(dú)的日本人都在居酒屋
文|圖 葉 醬


日本的居酒屋具有“詭異”的雙重屬性—它是一座城市最熱鬧的地方,同時(shí)也是最孤獨(dú)的地方。
它甚至摒棄了日本人在吃上面的專一追求。我們知道,日本的餐廳幾乎都只專注做一種美食,拉面店只賣拉面、壽司店只提供壽司,唯有“居酒屋”這一類別是兼容并包的。
居酒屋的老板大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來(lái),沒(méi)有所謂的正統(tǒng)和規(guī)矩,只要賓主皆歡就夠了。畢竟,人們?nèi)ゾ泳莆莶⒎菫榱苏笪W仄穱L美食,而是要去一個(gè)可以找回自己的地方。
居酒屋的雛形早在江戶時(shí)代就存在,但這種文化真正興起,是在日本經(jīng)濟(jì)騰飛的20世紀(jì)70年代。那時(shí)人們手頭寬裕起來(lái),上班族帶客戶或下班后獨(dú)自去小酌幾杯,成了一種普遍的習(xí)慣。一般規(guī)矩是,坐下來(lái)先要一杯生啤,然后再慢慢點(diǎn)菜。
20世紀(jì)80年代后,日本餐飲業(yè)越來(lái)越繁榮,各種亞形態(tài)的居酒屋慢慢出現(xiàn),像西洋風(fēng)的紅酒酒吧、主推“燒鳥(niǎo)”的串燒酒屋、賣老板人設(shè)的小酒館等。
簡(jiǎn)單來(lái)說(shuō),現(xiàn)在的居酒屋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客人為中心,另一類則是以店主為中心。
前者多為店面大、走低價(jià)路線的連鎖居酒屋,如和民、白木屋、甘太郎、鳥(niǎo)貴族之類,適合公司組織一幫人進(jìn)行以喝酒、聊天為主的聚餐。基本上,大家都是成群結(jié)隊(duì)、自愿或不太情愿地去參加這類聚會(huì)。
像一名心理咨詢師那樣,教師也需要一種共情的能力,所謂共情就是指一種體驗(yàn)他人內(nèi)心世界的能力。作為一名教師,我們要試著從學(xué)生的視角,去體會(huì)學(xué)生的感受,去看待學(xué)生的問(wèn)題。當(dāng)你靜下來(lái)去觀察和體會(huì)時(shí),你會(huì)發(fā)現(xiàn)學(xué)生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很多問(wèn)題,其實(shí)只是源于其內(nèi)心那一點(diǎn)簡(jiǎn)單的需求和渴望,只不過(guò)是被包裝和扭曲成了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樣子。這時(shí)你會(huì)覺(jué)得學(xué)生都是可愛(ài)的。
常有在日本大企業(yè)工作的朋友抱怨,上一天班已經(jīng)很累了,下了班只想回家休息,但被上司邀請(qǐng)去喝酒,又不能顯得不合群,最后搞得身心俱疲。晚上11點(diǎn)走在東京或大阪的街頭,經(jīng)常會(huì)看到一群一群剛從居酒屋出來(lái)的年輕上班族,男生依舊西裝革履,女孩子穿清一色的職業(yè)套裝,大家圍成一個(gè)圓圈互相鞠躬告別,通常要持續(xù)10多分鐘才能順利解散。
這類喧鬧型的居酒屋還有升級(jí)版,像某些旅游勝地,如沖繩,開(kāi)著不少具有當(dāng)?shù)靥厣木泳莆荩鞔驔_繩料理,還有邊彈奏三味線邊唱島歌的歌手進(jìn)行現(xiàn)場(chǎng)演出。這類居酒屋常常被來(lái)此進(jìn)行員工旅行的公司包場(chǎng)。
面紅耳赤的中年人,打著拍子、扯著嗓子唱歌,說(shuō)著略帶粗魯語(yǔ)氣的話,“干杯,干杯”的聲音響徹整棟樓,釋放著積蓄已久的壓力,完全不像白天車站里行色匆匆、拘謹(jǐn)禮貌的日本人。
但是,用虛假的熱鬧來(lái)麻痹自己,這根本不是居酒屋真正的魅力所在。
經(jīng)過(guò)車站附近黑漆漆的商店街,你會(huì)發(fā)現(xiàn)幾家大門緊閉、完全不知道里面在干嗎的小酒館,有的會(huì)開(kāi)扇小窗戶,往里偷偷一窺,會(huì)看到逼仄的吧臺(tái)邊坐滿了手拿酒杯的客人。
這就是以店主為中心的居酒屋,它們通常規(guī)模很小,小到有一兩個(gè)人來(lái)接待客人就足夠了。比起酒和料理,老板的個(gè)性、人品、待客技巧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而且這類居酒屋,菜肴往往不是批量生產(chǎn)的,酒經(jīng)過(guò)精心挑選,店內(nèi)氣氛輕松愉快,是在倍感孤獨(dú)的時(shí)候,一個(gè)人也能安心入內(nèi)的地方。
“京都坊主”就是這樣一個(gè)可以聊人生的地方。
穿著一身簡(jiǎn)約版僧衣的店主羽田高秀是光恩寺的住持,同時(shí)還是IT公司的老板和一名父親,店里打工的小哥也都來(lái)自附近大學(xué)的佛學(xué)系。對(duì)我們這樣貿(mào)然闖入的新客,他也非常樂(lè)意與我們聊天,還推薦了日本產(chǎn)的威士忌、葡萄酒和精釀啤酒。
常有女性客人向他傾訴感情上的煩惱,店主索性設(shè)置了個(gè)性十足的酒單,將雞尾酒冠以“色即是空”“諸行無(wú)常”等佛教色彩濃郁的名字。
在一次采訪中,他說(shuō):“諸行無(wú)常,沒(méi)什么恒定不變。根據(jù)當(dāng)天的心情、搭配的食物以及氣氛的不同,我會(huì)提供不同的酒,你可能不喜歡。人生也是這樣。”
游走于世俗與超凡之間,將深?yuàn)W的佛法運(yùn)用于解答關(guān)乎人情世故的難題上面,“京都坊主”只是日本居酒屋的一個(gè)特別的縮影。
每一間居酒屋的老板都擁有獨(dú)特的個(gè)人魅力,店里沒(méi)有多么高級(jí)的料理,也許只是深夜醉酒后的一碗茶泡飯,還有讓人懷念起家鄉(xiāng)的玉子燒,以及恰到好處的沉默。
下班后不想那么快回到冷冰冰、只有幾張榻榻米的小公寓里,那么去熟悉的店里坐一會(huì)兒,喝杯酒緩一緩,對(duì)日本人來(lái)說(shuō)是如同到附近的便利店買東西一樣自然隨意的事。日劇《深夜食堂》中那間同名的居酒屋便是這樣的存在。
劇中設(shè)定的地點(diǎn)在新宿黃金街,脫衣舞娘、大齡剩女、離家出走的年輕人、受情傷的男女,全都在深夜聚集于此。店主只是靜靜地聽(tīng)大家訴說(shuō),不多做評(píng)價(jià),更是從來(lái)不談自己的身世。菜單上雖然只有一道菜,但根據(jù)客人的點(diǎn)單,店主能做出各種奇妙的料理。
上回在東京,好友明日香帶我去了隱秘居酒屋的集中地—新宿黃金街。明日香是個(gè)不折不扣的酒鬼,對(duì)于東京喝酒的地方如數(shù)家珍。她帶我去的那家居酒屋很有意思:一周七天,由七位不同的店主經(jīng)營(yíng),客人和哪位店主氣味相投,便會(huì)在哪天前來(lái)。
走到門口就被店鋪的狹小程度震驚—吧臺(tái)前坐滿了客人,需要側(cè)著身子像魚一樣滑進(jìn)去,好不容易才挪開(kāi)一堆包和衣服坐下。這家店一共六七平方米,廁所、吧臺(tái)和桌椅卻一應(yīng)俱全。
周三剛好是明日香的朋友當(dāng)值,那天來(lái)的客人大多互相熟悉,他們也非常歡迎我這位新客。沒(méi)有固定的酒水單,客人告訴店主自己想喝的口味,“啊,想要一點(diǎn)水果味,酒精度不要太高,稍稍甜一點(diǎn),拜托了”,這樣說(shuō)就好。
大家平日里在各行各業(yè)工作,明日香是房產(chǎn)中介,另一位中村大叔從事建筑業(yè),還有美容師、寵物店員工、銀行職員,等等。一群完全沒(méi)有交集的人在此相遇,沒(méi)有額外的人情負(fù)擔(dān),只是一起喝酒、聊心事。
這種街區(qū)里的小居酒屋,每天都在上演著這樣的場(chǎng)景:一位客人推門而入,老板娘會(huì)心一笑,招呼道:“今天也辛苦了。”
“老樣子,跟之前一樣。”客人說(shuō)。
“好嘞。”老板娘轉(zhuǎn)身就去準(zhǔn)備酒水小菜了。這種無(wú)言的默契,昭示著居酒屋是作為“精神寄托所”的重要存在,它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酒和菜,而在于人和氛圍。僅僅有這樣的一個(gè)場(chǎng)所,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