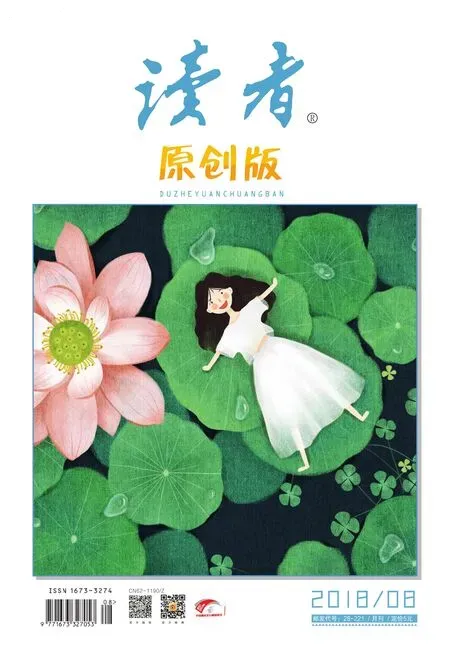曾經的咖啡館夢想
文 | 童 鈴

我們從事著不同的職業,在各自的領域奮斗、求索,終于獲得獨家的對世界的認知與感受。歡迎講述你的職業故事,分享思考與經歷。投稿請發至ycplan@qq.com。
最近有個朋友讓我幫忙寫文案,她說喜歡像“牽著你的手,如同白晝里絢爛的彩虹,黑夜里璀璨的繁星”這種文藝唯美的句子,我長嘆一聲,這樣的文字,我寫不出。
然而,翻一翻自己2005年剛開始做咖啡館時的工作心得,“喜歡磨豆時‘嗡嗡’的噪音,喜歡彌漫的咖啡香味,更喜歡將咖啡豆碾成粉的成就感”“咖啡需要被溫柔地對待”“晚上收工前,為自己做了一杯卡布奇諾,吻著濃濃的奶沫,溫柔的感覺霎時涌上心頭”這樣深情的筆觸隨處可見。
這真是我寫的?
好吧,那時的我確實是個“文藝女青年”,每天擠地鐵上下班,挨老板的訓,拿有限的工資,卻舍得花錢看話劇、聽音樂會。那個時候,我以為懂咖啡的人才稱得上有品位,每天坐在咖啡館里聽小野麗莎、讀張愛玲才叫人生。
一直想開一家咖啡館,一直下不了決心。
直到有一天,公司瀕臨倒閉,我才發覺給人打工是一種多么被動的人生。
如果是這樣,我為什么不開一家自己的咖啡館呢?哪怕它很小、很不起眼,至少我為實現夢想努力過。
真正投入進去,才知道很多事物的魅力在于它的神秘感,咖啡也是如此。在深入了解咖啡之前,我覺得它高貴、典雅、妙不可言;但真正有所了解后,我冷靜下來,才明白這些文化意義都是人們賦予它的。而咖啡師,也不過是三百六十行之一,一個人會煮咖啡,就像鐵匠會打鐵、農民會種地,只是一種職業能力罷了。
至于開咖啡館,那基本是一種商業行為。
我真傻,我單知道坐在咖啡館里喝咖啡很浪漫,卻沒想過還有那么多瑣事需要處理,更沒想過咖啡館要賺錢才能交得起房租、買得起原料、請得起員工。
最初階段毫無疑問是混亂的。為了省錢,我找了“裝修游擊隊”來干活,沒有效果圖、施工圖,想到什么弄什么。那幾個工人也看出我什么都不懂,瞎弄了弄就完事了。之后,不停地有朋友跟我說這里不行、那個會掉下來,再然后就是不停地返工,幾十平方米的小地方居然花了三個月才裝修完。
2005年的中秋節,終于完成了所有的前期準備,我帶著無比茫然的心情開始營業。
我已經預感到后面的路不好走了。
總有人以為,一個人過了三十歲就會懷念二十多歲時的青春年華,但其實不是。伴隨著青春的還有無知和幼稚,在人生經驗不足的情況下,前方的路通向哪里,常常不可辨別。有很多日子,店里沒有一個客人上門,那種孤零零一個人等生意的感覺真不好受。比這更可怕的是,我當時完全不知道該做些什么才能改變這種局面。
那段時間,我上街發過傳單、貼過小廣告,在社區論壇里寫過各種宣傳文章,為了一百多塊錢的生意工作至深夜,客人們聊一個通宵,我就在吧臺里坐一個通宵……
如今想起,依然覺得人生不易。
慢慢地,情況有所好轉,咖啡館從幾十平方米擴展到一百多平方米,再搬到高檔寫字樓里。但不知從何時起,我對錢變得敏感,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測別人,我越來越明了這個游戲應該怎么玩。最近和一個同樣開咖啡館的朋友聊天,他說自己現在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賺錢、怎么讓顧客多消費。我輕輕一笑。初識他時,他剛畢業,還在當服務生,滿心只有對咖啡文化的頂禮膜拜,如今他也變了。
是啊,這一路上摔倒過、疼過、笑過、難受過、精彩過,誰會不變呢?
2010年是“團購”大火的一年,我的咖啡館也搭上了這條“賊船”。那時,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日子過得跟打仗似的,沒招到洗碗工之前我都是自己洗杯子,最多的時候一天洗過幾百個杯子;遇到過職業差評師,各種找茬、刁難、威脅……過大的工作量既摧毀了我的健康,也透支了我對咖啡館的熱情。我是懷揣著夢想開咖啡館的,此時,夢想早已不知遺落在哪個角落了。
有一天,我翻看自己很久以前寫的一篇文章,叫《販賣咖啡,同時附贈一個巨大的朋友圈》,讀著讀著,不免黯然。
“我的夢想是販賣咖啡,同時附贈一個巨大的朋友圈。幾年前,我迷上了幾米的漫畫《向左走,向右走》,深深印在我心里的是這部漫畫的靈感來源—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的詩《一見鐘情》。詩里說,陌生的你我可能早就接觸過,比如在旋轉門里面對面的那一刻,比如電話里一句唐突的“打錯了”,但因為我們并未相識,所以彼此的生活還在按原有的軌跡前行。
我一直認為,喜歡去同一家咖啡館的客人必定有共同點:或許都喜歡這家店的氣氛格調,那么說明他們有共同的審美情趣;或許都喜歡服務員親切的笑容,那么說明他們在待人接物方面有類似的傾向;或許喜歡同一款飲品,那么說明他們有相近的口味……可是上午來的客人和晚上來的客人怎么可能相識呢?即使是在同一時段光臨,甲坐窗邊,乙坐包間,彼此還是不相識。咖啡館不應該是一座孤島,它應該提供讓陌生人彼此認識的機會。所以,在販賣咖啡的同時,我們還應該附贈一個巨大的朋友圈。”
原來我曾經那么有情懷,我自己都快想不起來了。
2011年春節后,團購突然不行了,咖啡店的很多尾款收不回來,店里一下子陷入了困境。而此時我的哮喘也已嚴重到了每月都要去醫院輸液的程度。
其實這六年里我沒少遇到難事,唯一不同的是,這一次,胸中的那口“真氣”散了。
和咖啡館分手后的一天,我望著夕陽西下,突然之間醍醐灌頂—六年來我的心只和咖啡館建立聯系,美好的景色一直都在那里,我卻許久沒有關注過了。我一直以為是咖啡館需要我,但其實是我需要咖啡館,因為只有身處大小事務之中,我才能感覺到自己存在著。那一剎那,我明白了,一個人怎么能只和一樣東西建立聯系呢?生活如此多姿,事業再重要也僅僅是人生的一部分。
之后我學了很多東西,烘焙、攝影、繪畫……我并非要變得多才多藝,而是感覺只有和更多的東西建立聯系,才能把心里的坑填滿。
如今開咖啡館的夢想已經離我很遠,這期間經歷的事、見過的人、承受的痛苦、明白的道理,終將停留在我的內心深處。
如果要問我還愛不愛咖啡,我不知道應該怎么回答,這就像身上的一個烙印,洗不掉、擦不凈,它永遠都在,愛不愛的,還重要嗎?
“讀者”簽約作家王國華獲第八屆冰心散文獎“單篇獎”
“讀者”簽約作家王國華近日憑借作品《我不認識鐵崗村的人》獲冰心散文獎“單篇獎”,本文首發于《讀者·原創版》2017年第12期雜志。“冰心散文獎”都有哪些作家獲得過呢?鐵凝、賈平凹、肖復興、趙麗宏、遲子建、葉文玲……一眾文壇大咖。而這一次,本刊作者王國華也獲此殊榮,編輯部的同事們都不禁為雜志擁有這樣的作者深感榮幸。今后我們會繼續致力于為讀者尋找最優秀的作者、最優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