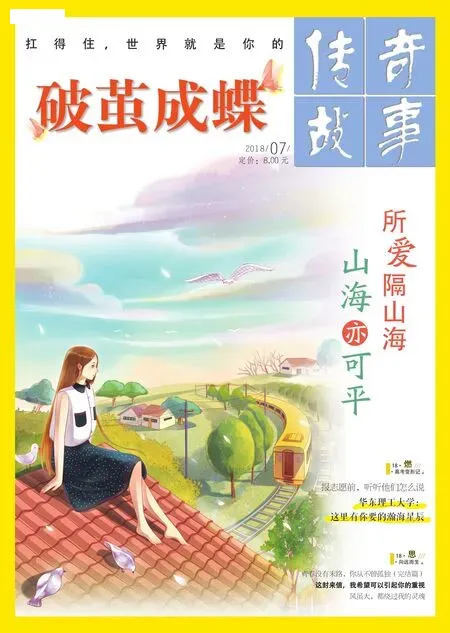我獨自向北,逐傳媒之美
○ 程則爾

三年前填高考志愿時,我在父親的“威逼利誘”下入讀了陌生的法學系,在本該最詩意的年華里變得輾轉迷失;三年后,當同學們皆成群結隊奮斗在司法考試或律所實習的路上時,我卻獨獨坐在了與法律風馬牛不相及的雜志社新媒體部里,煮字療饑,以夢下飯,每一天清晨在微笑中醒來。
一路跌跌撞撞的試錯,一場與年輕的死磕,我終于在傳媒領域靠岸。如果將大學比喻成祖國的版圖,那么同學們都規規矩矩地按照專業培養要求邁向南方的四季如春,我則偏愛北方那塊神秘的土地,孤獨地穿過冰封雪舞,開出青春最芬芳的臘梅。
意外與你喜相逢
大學第一學期結束,那張慘不忍睹的成績單是壓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除開體育和軍訓,其它科目全在及格線上低空掠過!
喜歡不需要理由,不喜歡也同樣不需要借口。雖然明知自己不喜歡法律這盤菜,但骨子里仍是個不甘落后的人。也有過強迫自己在課上集中注意力,也有過課余時間拼命地做兼職,甚至還批發來一堆小百貨在地攤街嘗試著掘第一桶金,可這看似被打了雞血的充實生活,卻只換來了兼職受騙、創業夭折、考試成績全班倒數的悲慘結局。
陰郁的寒假,就這樣在百思不得其解中度過,即使開學后氣候迅速回暖,也沒能驅除我心間的寒冷與迷茫。
那是一場與我不期而遇的講座,主講人是鳳凰衛視知名主播吳小莉女士。下課后經過禮堂,懷著消遣的心情,我拐了進去。講座很成功,優雅知性的吳小莉引經據典、談吐自如,傳媒人的情懷猶如一片片在沸水中舒展的茶葉,這是一種不同于法律人斤斤計較的大氣之美。
講座結束后,吳小莉在保安的護送下離開,閑雜人員都被擋在了人墻外。此時,一位記者快步上前,在保安還未反應過來時迅速向吳小莉說了一句奇怪的話:“小莉姐,您能像當初可口可樂總裁給了您機會那樣,也給我一次采訪機會嗎?”正當我以為吳小莉會婉拒時,誰料她居然點頭答應了。那天,事務繁忙的吳小莉特意在原地多停留了兩分鐘,接受了女記者的采訪。
后來,我才搞懂個中玄機。學生時代的吳小莉憑借不屈不撓的精神采訪到了可口可樂公司的總裁,從而在傳媒界一戰成名,開啟了璀璨一生。女記者猶如讀心高手,一招即擒住她心中那縷永不遺忘的月光,在情感共振中得到了采訪機會。
知道這美麗真相的一刻,我心中為女記者響起了排山倒海的掌聲,同時也感到有暖流一點點蔓延,漸漸澆潤枯萎的心田。用鏡頭對焦人生,用文字記錄百態,用行走去丈量生命的長度,并發掘其中的隱藏之美,這樣的生活太迷人,不正是我想要的嗎?
那一刻,我做了此生最重要的決定:與法律告別,跨專業就業到傳媒。
不怕節操碎一地
沒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再多情懷亦是枉然。連新聞要素都分不清的我,急需一場知識的惡補與思維的融入,傳媒領域第一站,從厚著臉皮蹭課開始。
我們學校的新聞系雖是新興學科,但與鳳凰衛視聯合辦學,大膽引進了一批思維活躍的中青年教師,堪稱一塊可供學子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精神沃土。
攥著千方百計搞到手的新聞系課表,第一次站在人聲鼎沸的教室前,我望而卻步了。他們能接受我這位不速之客嗎?他們會怎樣揣度和看待我呢?太多疑問化成我心中的忐忑。
猶豫之際,講臺上的男老師發現了我,詢問我是何方神圣。當他搞懂了我是想蹭課后,笑著說,不要怕,想當記者,得先把節操碎一地,說罷,帶領學生鼓掌歡迎我的加入。在大家友好的注視中,我放心地走進了教室。媒體人的包容,果然不假。
而這位男老師,正是前中央電視臺法制頻道高級編導,現新聞系主任劉勇,人送外號“劉美人”,亦是我在自學傳媒路上的啟蒙人。他告訴我們新聞人要像瘋子一樣生活和思考,他的節操論也影響了我們很長一段時間。
記憶最深刻的一次,是劉老師帶我們幾個去退休職工茶話會采寫。廳堂內,彼此久違的老人們眼眶含淚,嘮成一片。連著采訪到的兩三位老人都顯得悲傷難抑對我們的采訪愛理不理。在我們一籌莫展之際,劉老師眼珠一轉,對我們下了一道“圣旨”:“《小蘋果》,走起!”
當眾跳《小蘋果》?這若放在以前,“高貴冷艷”的我們絕不就范,但跟著劉老師在新聞戰線上摸爬滾打日久,我們已磨礪出一顆不問節操在何處的小心臟。隨著劉老師手機中的音樂響起,我們兩手一抬屁股一扭,以慰問的名義開始了笨拙的舞姿。雖然舞蹈跳得不整齊,但成功吸引了老人們的注意,緩解了他們悲傷的情緒,隨后,采訪得以順利進行。
“劉美人”的節操論,還被我們實踐到了很多地方。曾經我對傳媒的理解就是移花接木、寫寫畫畫,如今方知大錯特錯。新媒體時代,見了太多人生贏家,飲了太多心靈雞湯,點贊?NO!轉發?UNWANTED!評論?TOO LOW!每一次討論,都是一場震撼的發聲,一場IDEA的閃光。在“劉美人”的帶領下,我這個新聞系編外成員也開始沒節操地等上三個小時只為采訪五分鐘,沒節操地熬到凌晨只為趕完一篇新聞稿,沒節操地在邊邊角角搜羅一切資訊,只為將它們漂漂亮亮地做成專題。
劍走偏鋒又何妨
大三末尾,新聞系的課程基本結束,大家轉戰在了考研或實習的路上。同時,法學系學子則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司法考試備考之旅。司法考試是法律從業者的必過門檻,若不通過它四年大學等于白讀,我也因此陷入了強烈的恐慌中。如果說從前我還能毫無壓力地“腳踏兩條船”的話,那么今時今日我必須做出果斷的抉擇,并承受一切可能會帶來的后果。
一夜失眠,天光熹微之際,我選擇不忘初衷。在輔導員和同學們詫異的目光中,我成了那一屆法學系唯一既不參加司考也不考研的人。
隨之,我迅速開始找起了實習工作。年輕的我們,既要為夢想走,也要為稻粱謀。
我求職的方式很大膽,不僅僅只局限于泡在求職網,但凡是手邊的一份本地報紙或雜志,我都敢按照目錄上的辦公電話打過去,謙虛地問一句,您好,請問需要實習生嗎。幸運之神很快降臨,一家雜志的副總編邀我會面一敘。
去的路上,心一直忐忑高懸,最怕的,是被總編嫌棄非科班出身。學校離雜志社有十幾站公交的距離,我卻覺得路程太短,倏忽而至。
總編在編輯行業耕耘數十載,熱情接待了我。果然不出所料,她好奇地詢問我為何身在法學心在傳媒。這話是一把鑰匙,瞬間釋放了我心中埋藏已久的情懷。那天,我將自己大學三年的心路歷程向她娓娓道來,她聽得有些動容,感慨地說,是啊,只要熱愛,劍走偏鋒又有何妨。
隨后,總編讓我從專業的角度點評下他們的雜志。這可讓我的心懸到了嗓子眼,對紙媒一竅不通,我該如何是好?裝模作樣地翻開目錄,卻驚喜地看到幾個熟悉的筆名。我眼睛一亮,抬頭自信地答,老師,這幾位作者都是我的文友。接著,我避開了對雜志的點評,而是將幾位熟識作者的風格談了一遍。總編聽得有些高興,打趣到,原來你還是有作者資源的呀。
接到錄取電話那天,我在窗前久久佇立,看著懷揣夢想的莘莘學子來去匆匆,眼眶也一點點,變得濕潤。這一路,身在南國的我揀盡寒枝不肯棲,孤獨向北,終于降落在了屬于自己的森林。
我曾看過一幅漫畫,分岔路口,一群人向右,一個人向左,寓意這不是孤獨,而是一種選擇。是的,回首來時路,我就是那個向左的人,就是那個折騰青春的人,就是那個劍走偏鋒的人,懷一腔赤誠,遵循自己心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