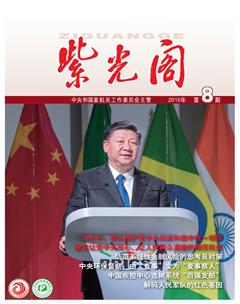財政部向“地方債”監督問責
李忠峰
7月17日,財政部官網連發四期通報,通報安徽、寧波、云南、廣西等地違法違規舉債問責情況,問題類型包括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違法違規舉債、財政局與城投簽訂回購協議以建設-移交(BT)方式舉債、地方人大政府違法擔保承諾通過信托方式舉債、將公益性資產注入融資平臺通過融資租賃舉債等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通報中,地方人大領導也首次被問責,開創先例。地方人大是當地最高權力機關,之前其違法違規出具有關決議似乎無法處理。從地方人大領導首次被問責,到地方政府領導無一脫責,財政部整飭地方政府舉債秩序的決心可見一斑,在防范和化解政治風險上自覺擔當責任、主動有所作為,不讓小問題演變為大問題、簡單問題發展為復雜問題、局部問題升級為全局性問題。
眾所周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大攻堅戰中,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被放在首位,而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則是打贏這一仗的重要內容。公開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余額13.48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6.47萬億元,兩項合計,我國政府債務余額29.95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GDP初步核算數82.71萬億元計算,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債務余額/GDP)為36.2%,比上年(36.7%)下降0.5個百分點,低于歐盟60%的警戒線,也低于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地方政府債務的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為76.5%,低于國際通行的100%—120%的警戒線。可以看出,與世界上主要國家對比,我國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此外,我國經濟總量和地方財政收入今后仍將繼續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長,也有助于更好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雖然法定限額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我國一些地方在法定限額之外通過融資平臺公司、PPP、政府投資基金、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違法違規或變相舉債,形成的隱性債務規模難以估計,因而風險較大。從去年至今,封堵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的文件接連下發。這一系列規定基本都是緊緊圍繞一個大目標: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積極化解存量隱性債務。
盡管如此,仍有一些地方存有僥幸心理。究其原因,也暴露出當前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問題:一些地方黨政領導干部政績觀不正確,走高負債投資保增長的老路,過度舉債謀“政績”,無序舉債搞建設;一些地方政府預算軟約束,建設項目脫離經濟發展水平和超越歷史階段,只考慮借錢花錢,不考慮還錢,債務不斷累積;一些地方和部門審核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把關不嚴,沒有充分考慮地方政府還款能力,還有些項目單位未按要求落實建設資金來源;一些金融機構行為失范,存在財政兜底幻覺,放松風險管控要求,違規提供融資;一些地方和部門對違法違規融資擔保行為問責不嚴格不到位等。這些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真正解決,繼續放任地方政府走無序舉債搞建設保增長的老路,發展到一定程度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影響我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影響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
種種舉措表明,嚴查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嚴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當前中央部署的“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一項重要任務。如何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既要開好“前門”,穩步推進政府債券管理改革,強化政府債券資金績效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益,支持補齊民生領域短板;又要嚴堵“后門”,守住國家法律“紅線”,堅守財政可持續發展底線,硬化預算約束,堅決制止和查處各類違法違規或變相舉債行為。
無論是開好“前門”,還是嚴堵“后門”,關鍵是要健全監督問責機制,對頂風違紀的必須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問責一起,終身問責、倒查責任,形成強大的震懾作用。當然,從長期來看,要深化財稅體制、投融資體制、金融改革,建立健全長效機制,全面推進地方政府債務公開,推進政府債務立法,強化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