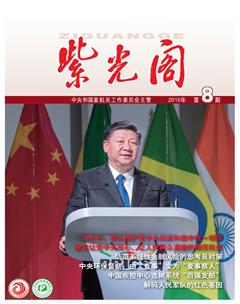解碼人民軍隊的紅色基因
李濤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加強軍隊黨的建設,開展“傳承紅色基因、擔當強軍重任”主題教育。日前,中央軍委印發(fā)《傳承紅色基因?qū)嵤┚V要》指出:紅色基因是我黨我軍性質(zhì)宗旨本色的集中體現(xiàn),必須一代代傳下去。紅色,是共產(chǎn)黨人的底色,也是人民軍隊的本色;基因,決定生命的構(gòu)造。兩個詞結(jié)合在一起,就構(gòu)成人民軍隊獨樹一幟的精神內(nèi)核和非凡特質(zhì)——紅色基因。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
軍隊歸誰領導、聽誰指揮,是軍隊建設的根本問題。在人民軍隊出現(xiàn)之前,我國歷朝歷代的軍隊無不體現(xiàn)私有特質(zhì)。經(jīng)歷大革命風暴洗禮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深刻認識到:黨對軍隊的領導權(quán),是黨和人民的一種生存權(quán)、發(fā)展權(quán)。黨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就必須擁有和牢牢掌握軍隊;人民軍隊要堅持無產(chǎn)階級性質(zhì),就必須時刻聽從黨的指揮。毛澤東曾深刻指出: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共產(chǎn)黨人要爭黨的兵權(quán),而不是個人的兵權(quán)。
中國共產(chǎn)黨在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后,就開始了黨對軍隊領導原則的理論創(chuàng)造和實踐探索。南昌起義時,黨在起義部隊中設立前敵委員會,軍、師設黨委和黨代表,團設黨的支部。1927年9、10月間,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在進軍井岡山途中進行三灣改編,確立在營、團建立黨委,連隊建立黨支部,班、排設黨小組,連以上各級設黨代表。后來,毛澤東在總結(jié)井岡山斗爭經(jīng)驗時指出:“紅軍所以艱難奮戰(zhàn)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幾乎與此同時,朱德、陳毅等人也在進行黨領導軍隊的不懈探索。1927年10月下旬,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受挫后,余部轉(zhuǎn)戰(zhàn)至贛南安遠縣天心圩。當時部隊僅剩千余人,四面受敵,孤立無援,瀕臨潰散。關鍵時刻,朱德在陳毅等人的支持下進行整頓,統(tǒng)一思想認識,振奮革命精神。月底,部隊來到大庾地區(qū),整編部隊,整頓黨團組織,成立黨支部,重新登記黨、團員,加強黨在基層的工作。天心圩整頓、大庾整編,以及隨后的上堡整訓,合稱“贛南三整”,對建設一支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進行了寶貴探索。
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強調(diào)紅軍必須完全地置于黨的領導之下,一切活動都必須服從和服務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從而實現(xiàn)了軍權(quán)由個人掌控向無產(chǎn)階級政黨領導的飛躍,在根本上保證了人民軍隊的性質(zhì)。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由此鑄就定型。正是在這個生存發(fā)展的根本性問題上堅定不移,紅軍才能歷經(jīng)艱險而無往不勝。新中國成立后,人民軍隊的職責使命雖發(fā)生轉(zhuǎn)變和拓展,但始終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軍隊各項建設的首位,聽黨指揮的信念更加堅定,軍魂意識更加牢固。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軍宗旨
軍隊宗旨是指建設軍隊干什么,為誰服務。這是由軍隊的性質(zhì)決定的,同時又是軍隊性質(zhì)的集中體現(xiàn)。一支軍隊在人民心中擁有多大分量取決于這支軍隊對待人民的立場和態(tài)度。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軍的根本宗旨、初心所在,也是我軍的力量之源、生命所系。
“在湖南汝城縣沙洲村,3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深情講述,讓“半條被子”的故事穿越歷史時空,盡顯歷久彌新的魅力。一條棉被,剪成兩半,永不放棄,永遠相連,記錄著紅軍戰(zhàn)士與老百姓的親密感情,象征著人民軍隊與廣大群眾須臾不可分離的魚水深情。一部紅軍長征史,同時是一部反映軍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的萬里轉(zhuǎn)戰(zhàn)史;一部人民軍隊史,同時是一部見證軍民血脈相連、生死相依的魚水情深史。
子弟兵愛人民,是天然的,因為這是我軍的宗旨。為了掩護群眾安全轉(zhuǎn)移,當年狼牙山五壯士與日寇周旋到最后一刻,縱身跳下懸崖絕壁;劉老莊八十二勇士阻擊牽制日軍10多個小時,全部壯烈犧牲。寧可自己丟掉性命,也要保護百姓安全,這是人民軍隊永恒的信念與堅守。即使在物質(zhì)匱乏、戰(zhàn)斗頻繁、環(huán)境惡劣的困境下,全軍官兵仍始終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真正維護群眾利益。1947年,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劉伯承、鄧小平為部隊“約法三章”:以槍打老百姓者,槍斃;掠奪民財者,槍斃;強奸婦女者,槍斃。
人民軍隊為人民,又是必然的,因為軍隊打勝仗,人民是靠山。無論是土地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以及抗美援朝戰(zhàn)爭,還是建國后歷次邊境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廣大人民群眾無不全力以赴掀起參軍參戰(zhàn)、支援前線的熱潮,留下許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淮海戰(zhàn)役,我軍能用“小米加步槍”打敗美式裝備的國民黨鋼鐵大軍,取得60萬完勝80萬的奇跡,與人民群眾的全力支援分不開。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決戰(zhàn),糧食和物資消耗遠超一般戰(zhàn)役。以糧食為例,戰(zhàn)役發(fā)起時每天需要原糧300萬斤,隨著戰(zhàn)役推進增加到近400萬斤。這么多糧食都是后方人民節(jié)衣縮食、踴躍支援的。他們寧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節(jié)省下來的糧食運往前線。整個戰(zhàn)役中,前后方共出動民工約543萬人,平均每名解放軍戰(zhàn)士身后有9名支前民工。華東野戰(zhàn)軍司令員陳毅曾動情地說:“淮海戰(zhàn)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堅定信念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關乎事業(yè)成敗。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永遠是革命軍人的政治靈魂。正是出于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新中國、共產(chǎn)主義的堅定信仰,無數(shù)革命軍人拋頭顱、灑熱血,用生命澆灌出理想信念之花。
九一八事變后,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東北抗日聯(lián)軍縱橫馳騁于白山黑水間,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并拖住數(shù)十萬日軍精銳不能南下入關,有力地支持了全國抗戰(zhàn)。據(jù)日本陸軍省公布的數(shù)字,這一時期關東軍的傷亡人數(shù)為178200人,相當于近8個日軍甲種師團的總兵力。日本侵略者驚呼“三江省已變成共黨樂土!”為鞏固其侵華戰(zhàn)爭的后方基地,日軍自1938年起向東北大量增兵,關東軍由20萬猛增至40萬人,同時推行“滿洲國三年治安肅正計劃”,強迫民眾“歸屯并戶”,建立“集團部落”,實行“十家連坐”的保甲制,在抗聯(lián)經(jīng)常活動的山區(qū)修筑“戰(zhàn)備道”,制造無人區(qū),斷絕抗聯(lián)的補給來源,把抗聯(lián)逼入“無房可住、無衣可穿、無糧可吃”的絕境中。東北抗日游擊戰(zhàn)爭由此進入最為艱難的時刻,抗聯(lián)為之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
面對日軍殘酷的“討伐”,革命信念堅如磐石的抗聯(lián)將士沒有被嚇倒。他們以野草充饑,同風雪抗爭,與敵苦苦周旋,頑強戰(zhàn)斗,不畏犧牲,涌現(xiàn)出無數(shù)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1938年9月下旬的一天,活動于吉東深山密林中的抗聯(lián)第二路軍總司令周保中在日記中寫道:“是晚之時在小溪谷露營,乘馬餓斃者十余匹;昨今兩日無食,凍餓交加”;1940年冬,中共南滿省委書記、抗聯(lián)第一路軍副總司令魏拯民在漫天大雪的二道河子密營中給黨中央寫下了一封信:“我們現(xiàn)在的處境十分艱難,身邊的戰(zhàn)友已經(jīng)相繼犧牲……盡管敵人現(xiàn)在正向我們瘋狂進攻,盡管密營已是糧盡彈絕,但我們?nèi)匀灰园僬鄄粨系木翊驌魯橙耍蚁嘈盼覀儠蛴鷱姟!贝藭r的魏拯民已重病癱瘓在床,身邊只有6名戰(zhàn)士。他們以草根、樹皮為食,靠著堅定的革命信念一直堅持到第二年春天。1941年3月8日,32歲的魏拯民病餓而死。臨終前,他把信交給戰(zhàn)士們,并下了最后一道命令:一定要堅持活下去,把信轉(zhuǎn)送出去!遺憾的是,幾個月后,日軍討伐隊找到這個密營,6名戰(zhàn)士全部戰(zhàn)死。解放后人們在整理日偽檔案時發(fā)現(xiàn)這封信,才揭開這段不為人知的悲壯故事。
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
在中國人民革命戰(zhàn)爭的長期實踐中,人民軍隊逐步形成和確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的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成為在戰(zhàn)爭力量敵強我弱、武器裝備敵優(yōu)我劣的不利形勢下,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例如,在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贛南閩西蘇區(qū),粉碎國民黨軍“進剿” “會剿”的作戰(zhàn)中,形成“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紅軍游擊戰(zhàn)原則十六字訣;在中央紅軍反“圍剿”斗爭中,形成積極防御,誘敵深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zhàn)、速決戰(zhàn)、殲滅戰(zhàn)等一系列作戰(zhàn)方針和原則;在抗日戰(zhàn)爭中形成持久戰(zhàn)、敵后游擊戰(zhàn)、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zhàn)等;在解放戰(zhàn)爭中形成“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后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 “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等十大軍事原則;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形成“零敲牛皮糖” “蘑菇戰(zhàn)術(shù)” “冷槍冷炮運動”等。
發(fā)生在長征中的四渡赤水充分彰顯了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從1935年1月19日紅軍離開遵義北上至5月9日勝利渡過金沙江為止的72天,3萬多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兵不厭詐,聲東擊西,調(diào)虎離山,避實就虛,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把國民黨軍對紅軍戰(zhàn)略上的優(yōu)勢轉(zhuǎn)為紅軍對國民黨軍戰(zhàn)役戰(zhàn)斗上的優(yōu)勢,變封鎖為反封鎖、防御為進攻,化不利為有利、被動為主動,最終粉碎了蔣介石在川滇黔邊圍殲紅軍的計劃,擺脫了數(shù)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成為紅軍戰(zhàn)略轉(zhuǎn)移中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轉(zhuǎn)折點。一直被紅軍牽著鼻子走的蔣介石惱羞成怒,訓斥部下:“我們有這么多軍隊來圍剿,卻任他東逃西竄,好像和我們軍隊玩耍一般,這實在是我們最可恥的事情!”就連在遵義會議上交出指揮權(quán)的共產(chǎn)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心悅誠服地表示:“渡過金沙江以后,在戰(zhàn)略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比較有利的局勢。”1960年5月27日,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華時,曾對毛澤東說:“您指揮的三大戰(zhàn)役,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偉大的戰(zhàn)役相媲美。”毛澤東卻出人意料地回答:“三大戰(zhàn)役沒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筆!”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zhàn)斗精神
人無精神不立,軍無精神不勝,國無精神不強。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是從舊世界沖殺出一條血路的新型軍隊,誕生于武裝斗爭中、成長在浴血奮戰(zhàn)里,是一支“遇強敵而勇過、臨險阻而志堅”的英勇善戰(zhàn)之師。這支軍隊的戰(zhàn)旗彈洞累累,寫滿了無名烈士的英名;這支軍隊的武器裝備總是落后于對手,卻鮮有敗績;這支軍隊精神彌堅,從高級將領到普通士兵都敢于刺刀見紅,不畏犧牲,不曾懼怕任何強大的敵人;這支軍隊令人敬畏,蒙哥馬利告誡全世界軍人:“只有傻瓜,才會在地面上跟中國軍隊交手!”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戰(zhàn)爭年代,我黨我軍先后有2000多萬革命先烈獻出寶貴生命。僅四年解放戰(zhàn)爭中,人民軍隊就犧牲26萬余人,負傷104萬余人。從一個特殊的視角可以窺探人民軍隊的戰(zhàn)斗精神是如何鑄就的——我軍可能是古今中外軍隊中,高級將領受傷最多的一支鐵血之師。十大元帥有7位受過傷,十位大將累計戰(zhàn)傷37處,最多的是徐海東,負傷9次戰(zhàn)傷20余處。位列十大將之首的粟裕曾6次負傷,最嚴重的一次是1930年水南戰(zhàn)斗中,頭部被迫擊炮彈彈片擊中,治療了3個多月后才歸隊,但從此落下了時常頭痛的毛病。每當工作勞累或戰(zhàn)事緊張時,粟裕就會頭痛得要命。戰(zhàn)爭年代,由于我軍的醫(yī)療條件非常簡陋,一直也沒能查明病因。解放后,醫(yī)生檢查發(fā)現(xiàn)粟裕的頭骨里竟有彈片,這就是折磨他多年的頭痛病的罪魁禍首。直到此時,粟裕才想起那是水南戰(zhàn)斗頭部負傷時留下的。但由于時間太久,彈片早已深深地嵌入骨頭里,無法取出。1984年2月5日,粟裕在北京去世。遺體火化后,親屬們才從骨灰中把彈片取了出來。在1600多名開國將帥中,還有一批因戰(zhàn)傷而斷臂斷腿、終身殘疾的將軍。他們是彭紹輝上將、賀炳炎上將、余秋里中將等九位斷臂將軍,還有鐘赤兵中將、謝良少將兩位獨腿將軍。曾有記者采訪開國少將徐其孝,問他身上究竟有多少彈創(chuàng)。他說自己也不清楚,就把前襟一撩說:“你數(shù)數(shù)看,就這里,起碼30多個。但是,我可以自豪地告訴你,我都是在前面負傷的,如果在背后負傷,那我肯定是逃兵!”說完此言,老將軍笑聲朗朗,豪氣沖天。
對于人民軍隊的戰(zhàn)斗精神,毛澤東曾有兩句十分經(jīng)典的話:“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 “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支連死都不怕的軍隊,還有什么可以畏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