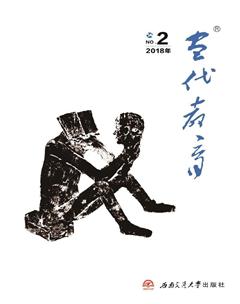磨豆腐
吳曉波
掀開臘月紅紅的封面,時光指針的轉速陡然加快,原來寂靜沉默的山村一下子沸騰起來。殺年豬,磨豆腐,打糍粑,做麥芽糖,趕年集辦年貨……匆忙而又雜亂的腳步,把整座山村攪得沸沸揚揚。磨豆腐是家家戶戶年前必做的一道功課。
喧鬧聲從村中磨房長滿蒿草的屋頂上傳了出來。許久沒有這么多人光顧了,磨房里的兩片石磨興奮得“吱吱呀呀”,大口大口地吞著人們喂下的豆子,雪白的豆汁從磨沿上嘩嘩流出來。院中,提桶的,擔水的,來來往往,絡繹不絕。磨豆腐通常男女搭手,男人推磨,女人坐在一旁添磨,其余人按次排著隊搭著訕,借機討論著過年的時程安排。小孩越是人多越是喜歡扎堆,時不時引起大人們一頓呵斥。不知不覺,半個時辰下來,一擔豆腐就磨好了。
小時候,每年春季母親都要挑上一塊荒地,種上黃豆。這些黃豆?jié)娖ひ靶裕陨蠋状文赣H施下的草木灰就一個勁地瘋長;到了秋季,就結出一串串喜人的豆莢來。母親把它們拔起在谷場曬上幾日,揮著連枷輕輕一拍,一粒粒金黃的豆子就微笑著滾了出來。母親把它們裝進一個袋子,懸在梁上。等到了陰雨天,母親解下袋子,把豆子倒進筐中,揀出癟籽、霉籽用來喂豬或牛,剩下的臘月里就可以用來磨豆腐了。
豆腐磨好了回來,母親和父親聯(lián)手把它們倒進一個懸著的布包袱里,用力地擠,擠出白白的汁就是豆?jié){了。母親把灶上的火燒得旺旺的,把滿桶豆?jié){倒入鍋里煮沸,豆?jié){甘甜濃郁的淳香爬滿了整座屋子。煮好的豆?jié){倒入一個大缸,父親用調(diào)好比例的石膏水往缸里一撒,蓋上缸蓋,不一會兒,揭開缸蓋一看,滿滿的一缸的豆腐腦。再把豆腐腦舀起來裝進包袱,等水流干,扎起來,在上面壓上幾塊大石頭,過上幾個時辰,打開包袱,就是白嫩嫩的豆腐了。
臘月里莊戶人家通常要磨兩輪豆腐,一輪在臘月初,一輪在年邊上。第一輪的豆腐主要用來平時吃或做豆腐乳。吃的豆腐泡在盆里,冬季缺菜,隨便撈上一塊燉上腌白菜就是一頓不錯的主菜了。把瀝干了水的豆腐切成小塊,找上一個籮筐,在上面鋪上一層干凈的稻草,把豆腐塊一層一層地鋪上去,每層都用稻草隔開,最后上面捂上一個舊棉襖,在暖陽下曬上幾個日頭,等豆腐塊全身都長出一層白白的絨毛,就可以用來做豆腐乳了。母親用筷子把這些豆腐塊揀下來,在拌有辣椒生姜和鹽的調(diào)料里打個滾,然后一層一層地鋪在一個瓷壇子里,最后澆上一層油封上,過不了多久,一壇美味可口的豆腐乳就好了。
第二輪的豆腐主要用來過年吃。年三十的年夜飯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就是青菜豆腐,說是吃了青菜豆腐,來年就能清清白白、平平安安。雖然有點迷信的說法,但也寄托了莊戶人家對生活的美好憧憬和追求。正月里,人們大魚大肉吃膩了口,豆腐反而成了最受歡迎的一道下飯菜。母親心靈手巧,每年還會用豆渣霉成豆渣團,由于發(fā)酵的火候掌握得恰到好處,霉出的豆渣團味道極其鮮美。每次城里的親戚來了,點名就要吃母親做的豆渣團燒腌菜,吃得大呼過癮。
如今,石磨早已被機器替代。每年過年回家,照常要吃上豆腐,卻怎么也吃不出那串“吱吱呀呀”小石磨里飛出來的童年音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