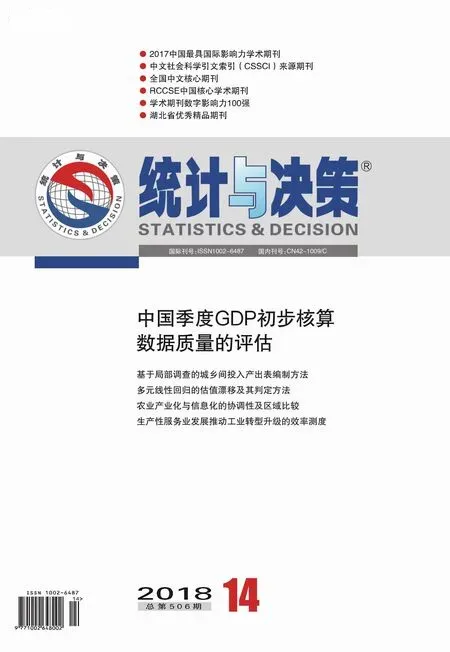全民醫保有效抵御了疾病經濟風險嗎
楊紅燕,聶夢琦,李凡婕
(武漢大學 社會保障研究中心,武漢 430072)
0 引言
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籌資方式是決定國民健康和福祉的關鍵性因素。第58屆世界衛生大會上,WHO呼吁成員國確保衛生籌資系統包含預付機制,避免因尋求治療而發生災難性衛生支出(下文簡稱CHE)和貧困(WHO,2005)。而保障居民基本的健康權利,為全體國民提供獲取醫療衛生的途徑也已成為現代醫療衛生籌資系統的基石(Yardim M.,2009)。醫療保險籌資的制度以其互助共濟、分擔風險的優點受到了世界多個國家的歡迎。不過,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道德風險,沒有任何醫療衛生系統的花費能夠全部由醫療保險籌集的資金承擔,大多數系統要求某種形式的個人分擔,以控制醫療保險成本。不過,需要明確的是,醫療保險籌資系統要為病人的高額衛生支出導致的經濟風險提供保護,使病人不至于因現金支付的相對份額過高、無法承受而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貧。
1998年、2003年和2007年,我國強制性的城鎮職工、自愿性的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制度分別建立。2012年后,以上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實現全覆蓋,進入后全民醫保時代,織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醫療保障網。合計參保人數超過13億,參保率保持在95%以上,基本醫保住院費用政策范圍內報銷比例均達到了70%以上。三項基本醫保制度加上計劃經濟時期延續下來的公費醫療,以及行業組織、商業保險等機構開展的補充醫療保險,多種形式的醫保對于保障人們的醫療衛生需求,應對疾病經濟風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與此同時,居民發生CHE乃至因病致貧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數據顯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戶在所有貧困戶里的占比達44.1%。而且,醫療保險的碎片化導致因病致貧狀況存在制度間差異。在此背景下,精確評估全民醫保各制度應對疾病經濟風險和因病致貧的效果,對于有效解決因病致貧問題,促進精準醫療扶貧,實現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所提出的推動健康領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有著重要意義。
1 研究方法與研究數據
本文首先采用世界衛生組織Adam Wagstaff的方法(Wagstaff等,2003),研究集中指數調整前后的家庭CHE發生率、發生強度,從家庭層面考察不同醫保制度抵御疾病經濟風險的保障效果,以及CHE的分配敏感性差異。在此基礎上,考慮到發生CHE可能有醫保制度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如籌資水平、報銷比例等制度內的原因,以及保障人口的收入水平、年齡、衛生廁所的使用等制度外的原因。為了將二者識別開來,本文進一步采用以個人為單位的數據和二元Logistic模型來考察不同醫保制度對于參保個人陷入CHE的概率和疾病經濟風險的影響。
1.1 家庭CHE發生率和發生強度
家庭CHE發生率為發生CHE的家庭占全部樣本家庭的百分比。用Ei表示是否發生CHE,則其計算公式如下:

公式(1)中Ti為家庭年現金衛生支出,xi為年消費性支出,fi為家庭食品支出,z為設定的閾值。根據以往的研究,本文中闕值確定為40%。CHE的平均差距0反映全社會CHE的嚴重程度,相對差距MPO反映CHE對于發生CHE家庭的沖擊強度。計算公式見式(2)至式(4)。


1.2 CHE的分配敏感性衡量
CHE對于收入分配狀況是不敏感的。因此,進一步引入集中指數以反映CHE的收入分配狀況。集中指數是衡量健康領域不平等的常用變量,被定義為集中曲線和公平(45°)線之間區域的2倍。計算公式如下:

公式(5)中,r為收入水平的排序狀況,h為健康變量,μ為h的平均值。
更進一步地,按照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窮人衛生支出的邊際效用將會比富人更大。為了更加直觀地反映窮人和富人在CHE上的分配差異,一般采用加權的方式,對于窮人和富人賦予不同的權重,收入越低,權重越高。由此得到集中指數調整后的發生率HW和平均差距OW(見公式(6)和公式(7))。o

1.3 二元logistic回歸
模型如下:

其中,i,t分別代表調查樣本與時間,i=1,2,…;t=2012,2014。
被解釋變量cheit是虛擬變量,有發生和不發生CHE兩種結果,值分別為1和0。cheit-2反映2012年樣本是否發生CHE①,insurit是醫療保險解釋變量,有公費、職工、城居、補充、新農合、無醫保共6種類型。xit是控制變量,有城市、慢性病、自評健康、衛生廁所、男性、老年人、就醫高級別機構、貧窮等。所有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均是虛擬變量,1代表是,0代表否。?0為常數項,?1至?3為代估系數,εit為擾動項。
1.4 研究數據
本文采用了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2012年和2014年數據。CFPS由北京大學實施,是一項全國性、大規模的多年社會跟蹤調查項目,樣本覆蓋25個省/市/自治區,調查對象包含樣本家戶中的全部家庭成員。CFPS對于調查對象的健康和醫療保險等內容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其中,2012年數據為實現全民醫保后第一次全國性調查數據,2014年數據為2012年的追蹤調查數據,以及部分新增樣本數據。剔除部分變量缺失的數據后,本文分別得到2012年和2014年有效樣本31169個和15913個。
樣本相關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城鎮地區醫保碎片化明顯,公費醫療、城鎮居民等各項制度的參保人口比重都不大。參保人口比重最大的城職保,也僅為10.6%左右。2012—2014年間,城職保的人口比重穩中有升;新農合的人口比重最大,且呈上升趨勢;無醫保的人口比重從12.7%下降到7.5%。

表1 樣本相關的描述性統計(均值、標準差)
2 研究結果
2.1 2012年與2014年各(無)醫保制度下家庭CHE發生率與平均差距
由圖1、圖2(見下頁)可以看出,從2012—2014年,CHE的發生率整體下降了2個百分點左右,各項醫保制度的平均差距雖然沒有明顯降低,但是其絕對水平都較低,且兩年間新農合和補充醫保的CHE的平均差距仍在繼續下降。CHE發生率方面,各制度的表現也不同。無論是2012年還是2014年,CHE的發生率和平均差距都是新農合最高,居民醫保居中,職工醫保較低,補充醫保最低。這或許與新農合參保人口的收入最低,且新農合保障水平低,人群現金衛生支出高,而補充醫保的參保人員經濟狀況好有關。無論用扣除食品支出前后的消費來衡量,補充醫保的家庭消費都僅次于公費醫療,高于其他醫保類型和無醫保人群。基本醫保內部,職工醫保的CHE風險較小,可能歸功于職工醫保較高的籌資水平、較年輕的年齡結構和較低的撫養(贍養)率。而同屬城鎮,城居保的CHE發生率和平均差距并不低。這或許與城居保的籌資、報銷水平低以及較高的撫養(贍養)率有關。令人詫異的是,無醫保人員的CHE發生率排名第二,平均差距排名第四,與其他醫保制度相比并非最高。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逆選擇”行為,即:更為健康的人群醫療支出較少,并傾向于選擇不參保。統計結果也顯示:無醫保者的醫療支出最低,但其家庭消費支出大于新農合,小于其他類型的保險人群。表明該類人群特征是現金衛生支出少而非富裕。

圖1各(無)醫保人群集中指數調整前后的CHE發生率

圖2各(無)醫保人群集中指數調整前后的CHE平均差距
從2012—2014年,新農合的CHE發生率降低最多,職工醫保降低最少,降低次少的是城居保和補充醫保。可能與城職保和補充醫保原本的發生率較低有關。而城居保原本的發生率也較高,且兩年間降幅較低,表明其保障效果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2.2 2012年與2014年各(無)醫保制度下家庭CHE相對差距
2012年相對差距的結果有所不同(見圖3)。城居保發生CHE家庭的風險最大,超過了新農合和職工醫保。接下來,無醫保、公費和補充醫保的相對差距依次降低。表明,從發生CHE的家庭來看,基本醫保覆蓋的家庭受CHE沖擊強度仍較大,制度保障效果有待于進一步提升。值得欣慰的是,2012—2014年,各制度在應對CHE相對差距,即發生CHE的家庭面臨的CHE沖擊強度上發生了反轉。2014年補充醫保最高,無醫保次之,然后依次是公費、職工醫保和新農合,居民醫保最低。也就是說,補充醫保和無醫保家庭一旦發生CHE,其面臨的CHE沖擊強度會大于基本醫保家庭。這有力地論證了基本醫保抵御疾病經濟風險和反貧困的實際效果,體現了基本醫保的功績。2012—2014年,城居保、新農合、職工醫保的相對差距均有不小的降幅,而補充醫保和無醫保卻升幅很大,時間趨勢同樣印證了基本醫保的有效性。

圖3各(無)醫保人群的CHE相對差距
2.3 2012年、2014年各(無)醫保制度下家庭CHE的分配敏感性狀況
由圖1、圖2可知,補充醫保2012年平均差距的集中指數超過了0.3(見圖4、圖5),且集中指數調整前后CHE平均差距的差異最大,存在親富的相對不均等。2012年公費醫療集中指數調整前后發生率的差距最大,且發生率和平均差距的集中指數都親貧(見圖4、圖5)。不過,2014年情況均已好轉。2014年,除無醫保者外,所有醫保參保者的發生率略親貧;除補充醫保者外,其他制度的平均差距略親富。這或許可以從支付能力的角度得到解釋。雖然醫保制度釋放了所有人包括窮人的現金衛生支出和支付能力限制,但是,釋放的程度受限于保險的保障水平。因而,窮人比富人更容易發生CHE。不過,真正遇到巨額的醫療支出,富人可能會繼續治療從而面臨更大的支出風險,而窮人可能放棄治療因而避免了更大的CHE沖擊強度。這就可以解釋為何除了補充醫保外,各醫保制度下平均差距都輕微親富。需要說明的是,除了2012年補充醫保外,兩年各醫保制度的集中指數無論親貧還是親富,都不超過0.2,表明CHE的收入分配狀況是相對均等的。

圖4兩年CHE發生率的集中指數

圖5兩年CHE平均差距的集中指數
2.4 2012年醫保制度對于個人是否發生CHE的影響
如下頁表2所示,2012年的回歸結果表明,公費、職工醫保制度下,制度內人群發生CHE的邊際效應,即比率比(Odds Ratio)更低。而城居保、新農合、無醫保等制度內人群發生CHE的幾率比制度外人群的發生幾率更高。尤其是新農合,參保人群發生CHE的幾率是非新農合人群發生幾率的1.98倍。幾項醫保制度中,制度內/外人群發生CHE的比率比(OR)由低到高依次為:職工、公費、補充、居民、無醫保、新農合。這與上文以家庭為單位的CHE的分析結果是一致的。城市、擁有更衛生的廁所、男性發生CHE的風險更小。過去六個月內,患有經醫生診斷的慢性疾病的人口CHE發生率稍高,自評不健康、60歲以上的老年人和窮人發生CHE的風險更大。尤其是窮人,是富人發生幾率的5.56倍。只是城居保等指標在統計上并不顯著。
2.5 2014年醫保制度對于個人是否發生CHE的影響
如下頁表3所示,2014年是否發生CHE的回歸結果中,2012年曾發生過CHE的人口面臨的風險是2012年未發生CHE的人口的3.7倍,邊際效應為3.7。幾項醫保制度中,制度內/制度外人群CHE發生的比率比(OR)由低到高依次為職工、公費、補充、城居保、無醫保、新農合。從2012—2014年,除了無醫保和城居保的順序顛倒了一下外,各項醫保制度的OR排序沒有變化。除了新農合外,每一項醫保制度內人群的CHE發生率都比制度外的人群要低。但新農合制度內人口的發生率依然比新農合制度外人口的發生率要高。這與12年回歸及上文CHE的分析結果是類似的。不過,無醫保、城居保的結果在統計上并不顯著。中西部發生CHE的邊際效應比2012年又提高了。與2012年相同,城市、擁有衛生廁所、男性發生CHE的OR比對照組人群要低;擁有慢性病、自評不健康、60歲以上老人、窮人等發生CHE的OR更高。

表2 2012年是否發生災難性衛生支出的二元logistic回歸結果

表3 2014年是否發生災難性衛生支出的二元logistic回歸結果
3 結論與對策建議
3.1 結論
根據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全民醫療保險的推行有效地應對了疾病經濟風險
從2012—2014年,醫保覆蓋人群CHE的發生率整體降低2個百分點左右。各項醫保制度的平均差距雖然沒有明顯降低,但是其絕對水平都較低,且兩年間新農合和補充醫保的CHE的平均差距仍在繼續下降。
(2)不同醫保制度應對CHE的效果各不相同
總體來說,在CHE的發生率和全體人群面臨的風險強度方面,城鎮醫保好于農村醫保。在城鎮內部,職工醫保的效果好于公費和城居保。補充醫保的效果好過城居保、新農合等,無醫保也并非是最差的。原因涉及醫保制度保障水平、不同醫保參保人之間的經濟社會差異、逆選擇等。
(3)基本醫療保險的保障效果優勢初顯
如果只考察已發生CHE的個體面臨的沖擊強度的話,2012—2014年基本醫保抵御疾病經濟風險的效果由落后變為超前,兩年間的靜態比較和動態趨勢都有力地論證了基本醫保抵御疾病經濟風險效果的優越性。
(4)各醫保制度的CHE收入分配狀況相對均等
除了2012年補充醫保存在一定的親富不均等外,兩年各醫保制度CHE發生率和平均差距的集中指數或略親貧,或略親富,但各制度下CHE總體的分配狀況是相對均等的。這或許與醫療保險相對縮小了窮人與富人的支付能力差距有關。
(5)除了醫療保險外,人口的環境特征和個體特征也影響CHE的發生
無論是否參保及參保何種制度,2012年曾發生CHE的人口2014年再次發生疾病經濟風險的概率是其他人群的3.7倍。中西部地區、農村、老人、窮人、廁所不衛生、自評不健康、有慢性病等人群相比其對照組面臨更大的CHE風險。
3.2 建議
WHO指出,所有人都應當享有所需要的有質量的衛生服務,并且不因享受這些服務而出現經濟困難。為此,要推行包括人口全覆蓋、服務全覆蓋和費用全覆蓋在內的全民健康覆蓋(UHC),提高居民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WHO,2010)。基于此,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鞏固、擴大基本醫保制度應對疾病經濟風險的成效,進一步降低CHE發生率。借鑒城鄉居民醫保改家庭賬戶為社會統籌的經驗,逐步弱化職工醫保個人賬戶,擴大社會統籌部分的比重,提高制度互助共濟能力和保障水平。并通過多樣化宣傳方式、完善宣傳內容等措施,強化自愿性城鄉居民醫保未參保人口的保險意識和對基本醫保的認同感,抑制逆選擇,進一步降低未參保人口比重,降低CHE發生率。
(2)實現從全民醫保到全民健康覆蓋的轉變,有效降低CHE的沖擊強度。我國實現全民醫保是一個巨大的成就。但全民醫保不等于UHC,而僅僅是UHC的一個維度。要想從根本上抵御CHE,必須在實現基本醫保人口全覆蓋的目標之后,繼續朝著衛生服務和衛生費用全覆蓋的方向努力,把更多、更優的衛生服務項目納入醫療保障范圍。一方面,要根據財政收入和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的速度,穩步提高基本醫保制度的籌資和保障水平,合理調整醫保目錄,放寬大病、門診慢性病等相關病種的限制范圍,減少自費藥品和診療項目比例,提高社會衛生支出比重。另一方面,要實現大病補充醫保制度的全覆蓋,并與基本醫保加強銜接,形成雙層保障網絡,提高整體的保障水平,降低人群現金衛生支出負擔,降低CHE平均差距和相對差距,從源頭遏制疾病經濟風險和醫療貧困。
(3)逐步縮小乃至消除各項醫保制度內部疾病經濟風險的差異。一方面,要按照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醫保的規定,實行城鄉統一的繳費、管理、報銷政策,統一定點醫療機構、統一醫保目錄內藥品和診療項目。另一方面,通過推行全科醫生和分級診療制度,完善醫療服務支付方式,完善按人頭預付、按病種付費等科學的支付方式,利用農村和社區醫療的便利和成本優勢,降低農村、基層就醫的費用負擔。提高城鄉之間、職工與居民之間疾病風險保障的均等性。
(4)多措并舉,降低貧困、脆弱人口疾病經濟風險應對的不均等性。要按照民政部[2017]12號文的要求,加強醫療救助與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的有效銜接,分類、分段確定救助比例,實現精準救助,提高貧困人群,及近期曾陷入醫療貧困人群的報銷比例。推進健康扶貧,優先為貧困家庭提供全科醫生簽約服務,對因病致貧、返貧家庭進行分類醫治。完善公共衛生和預防保健制度,徹底實現改水、改廁。通過推進定期體檢、醫養結合服務等,及早診斷、治療,提高老年脆弱人群的應對效果,避免小病拖成大病。通過各級財政支持,提高中西部、農村等人群的籌資水平。從而公平地保障所有人口的疾病經濟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