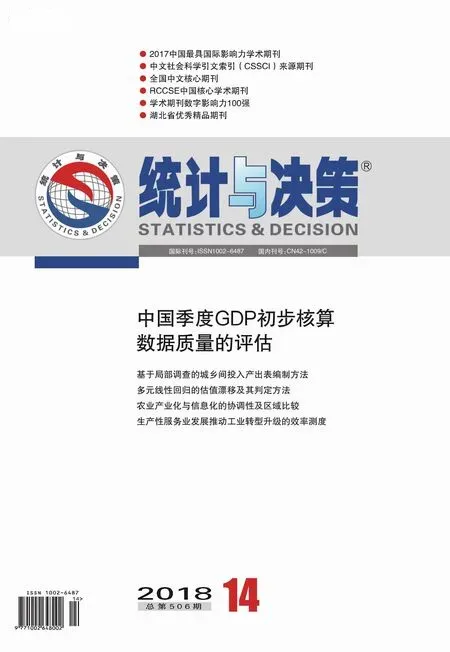貧困人口視角下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研究
孟秋莉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武漢 430073)
0 引言
何為“貧困”?亞洲發展銀行(1999)把“剝奪了每個人應有的基本物質和機會”定義為貧困,世界銀行(2008)界定了國際貧困線為每人每天消費不低于1.25美元。“反貧困”一直是全球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英國國際發展署(1999)首次提出發展有利于貧困人口的旅游,即旅游扶貧的PPT(Pro-poor tourism)模式,強調旅游應為貧困人口帶來大于其成本的凈收益[1]。旅游扶貧作為“造血式”發展戰略,成為世界多數國家“反貧困”的重要方式之一,并對當地經濟發展有較大帶動作用[2]。旅游扶貧不僅僅是資金、技術、人才等的投入,更多表現為面向貧困人口通過參與旅游業,使其獲得發展機會并提高收入水平,進而減少貧困。
旅游扶貧是通過政府扶貧投入、社會企業投融資等形式獲得資金支持,資金保障將影響旅游地基礎設施的建設和保障措施的實施,對于旅游收入的增加和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增長有重要影響。由于貧困的多維性以及旅游扶貧相關數據收集的復雜性,對于旅游扶貧微觀經濟效應的定量分析和研究較少[3],旅游乘數效應成為常用的研究方法[4],管理學、地理學、經濟學的相關研究方法也被應用到旅游扶貧的研究中。本文基于計量經濟學面板數據模型,以湖北省旅游扶貧經濟效應為例,瞄準貧困人口的微觀經濟收益,研究政府旅游扶貧投入、企業旅游投資、地方旅游收入對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影響程度,從微觀經濟的視角研究面向貧困人口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
1 理論模型
實現基于貧困人口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受到諸多條件和因素的影響,首先旅游扶貧參與主體間的相互作用和利益關系,是實現旅游扶貧經濟效應以及貧困人口收入增加的的內在源泉;選用何種形式的旅游扶貧機制,則影響到旅游扶貧項目開發和運營模式的選擇,以及扶貧經濟效應能否惠及貧困人口,如何實現并維持其可持續性;貧困人口視角下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主要是指貧困地區人口人均收入的增加,以及這種收入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與旅游扶貧各投入要素相關。
1.1 旅游扶貧參與主體利益關系
鑒于旅游扶貧的系統性與復雜性,旅游扶貧項目的實施需要各利益相關者共同努力。旅游扶貧參與主體包括政府、貧困人口、企業、旅游者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團體等[5],他們在旅游扶貧中各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國內旅游扶貧參與主體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政府在旅游扶貧中的作用和影響,對于企業、其他社會組織團體的扶貧影響研究較少[6]。
政府通過資金投入、法律法規與政策方針制定、旅游扶貧規劃引導等形式參與旅游扶貧,進行市場開發與營銷,為貧困人口提供人才培訓和信息,使其能參與旅游業并獲得發展機會,以保證貧困人口的合法權益[2];貧困人口在旅游扶貧中,既是旅游扶貧的對象又是扶貧的主體,是最有力的內源動力之一[7]。貧困人口參與到旅游發展中來,為旅游業提供勞動與服務,以獲得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與知識技能的提升,利用參與機會改變其貧窮的命運;企業通過投入資金和提供就業機會,并提供信息和技術支持、開拓客源市場等[8],促進了貧困地區旅游業的發展;旅游者是貧困地區旅游收入的來源,是旅游扶貧項目實施的外部推動者,旅游者的消費行為和文明素質,直接影響貧困地區旅游經濟的發展以及環境、資源的保護;其他社會組織團體,比如非政府組織等,在我國力量仍較為薄弱,可為旅游扶貧項目的開發提供了部分資金與技術支持、人員培訓等。因此,在旅游扶貧中各參與主體相互作用,政府、企業、旅游者和其他社會組織團體的各種投入,以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和就業機會的增加為產出,共同促進旅游扶貧項目開發與扶貧目標的實現(見圖1)。
1.2 旅游扶貧機制的影響與作用
扶貧機制決定了旅游扶貧的發展方向,并影響旅游扶貧經濟效應能否惠及貧困人口[9]。貧困地區應根據實際發展情況選擇不同的扶貧機制,建立并完善適合自身發展的扶貧保障機制、運行機制、受益機制以及利益相關者協調機制[6],確保貧困人口在旅游發展中真正獲益。
在實施旅游扶貧項目的貧困地區,應加強旅游業與貧困地區其他產業的融合,并加強旅游業與當地社區的聯系,建立當地社區從旅游業中獲利的框架[10];同時完善旅游扶貧運行機制,從目標、決策、動力、信息等方面的構建加以保障[11];并通過政府與非政府部門的參與,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建立多元參與協同機制[12],通過各方共同努力促進貧困地區旅游經濟效應的實現;并建立貧困人口共同參與旅游發展的扶貧長效機制,使旅游業發展的成果長期惠及貧困人口[13],以實現旅游扶貧的可持續發展,即“可持續旅游-減貧”(SE-EP)。
1.3 旅游扶貧經濟效應理論模型
旅游扶貧項目的實施給貧困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均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在這些影響當中,就像早期旅游扶貧研究的那樣,對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而言,旅游扶貧的經濟影響并由此產生的經濟效應往往被認為是最重要的[14]。旅游業在貧困地區的發展,宏觀上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地方財政收入,帶動了貧困地區旅游企業和私營部門的發展[15];微觀上為貧困人口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進而提高貧困人口的人均收入[16]。
然而,旅游扶貧經濟效應的獲得并不是必然,這是因為旅游業在貧困地區的發展,會面臨“旅游飛地”和“旅游漏損”現象;就貧困人口而言,由于參與成本加大,以及旅游收益的波動風險,使得貧困人口真正獲益有限[17]。因此,要取得旅游扶貧經濟效應,在宏觀視角上應加強旅游業與貧困地區經濟的聯系,擴大乘數效應,避免旅游飛地,減少旅游漏損,降低各種負面影響;同時強調加大政府的旅游扶貧投入,吸引私營企業投資,為貧困人口提供就業機會,促進貧困人口參與旅游業,并為其提供知識和技能的培訓,使貧困人口具備參與旅游業的基本技能,抓住并利用參與機會為旅游者提供旅游服務,分享貧困地區旅游收入的份額,進而使其脫貧致富[18],真正實現旅游精準扶貧“真扶貧,扶真貧”的理論思路。因此,貧困人口視角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所帶來的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受到政府扶貧投入、企業投資以及貧困地區旅游收入的影響(見圖1)。

圖1貧困人口視角下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理論模型
2 模型和數據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研究貧困人口視角下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面板數據也稱作時間序列與截面混合數據,是截面上的個體在不同時間進行重復觀測的數據。面板數據從橫截面上看,是若干個體在某一時點構成的橫截面觀測值,從縱剖面看,每個個體都是一個時間序列[19]。面板數據模型通常有三種設定形式,即混合回歸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面板數據模型的設定方法如下。
混合回歸模型定義為:Yit=α+βXit+uit,i=1,2,…,N;t=1,2,…,T。
其中,對于任何個體和截面,截距項α和回歸系數β都相同,即效應不隨時間或個體變化而發生顯著變化,則為混合回歸模型。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進行參數估計,且解釋變量與誤差項不相關,模型參數的混合最小二乘估計量均為一直估計量。
固定效應模型定義為:Yit= αi+ βXit+uit,i=1,2,…,N;t=1,2,…,T。
其中,模型截距項α隨個體或時點變化而發生變化,而回歸系數β不隨個體或時點變化而變化,則為固定效應模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需用最小二乘虛擬變量(LSDV)和離差OLS進行參數估計,并通過構造F檢驗,來完成對個體固定效應模型的檢驗。
隨機效應模型定義為:Yit=αi+βiXit+uit,i=1,2,…,N;t=1,2,…,T。
其中,模型截距項α和回歸系數β均隨個體變化而變化,則為隨機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可用可行GLS進行參數估計,可通過構造LM檢驗,來完成對隨機效應模型的檢驗,并可通過Hausman檢驗中H統計量的非零顯著性,檢驗面板數據模型中是否存在個體固定效應。
2.2 計量模型的設定
2.2.1 被解釋變量
對于貧困人口視角下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本文選擇貧困人口的人均收入(InPCI)作為被解釋變量,此指標可解釋旅游扶貧為貧困人口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可衡量旅游扶貧微觀經濟效應的大小。
2.2.2 解釋變量
基于貧困人口視角下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理論模型(見圖1),本研究選取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InGFFPA)、企業旅游投資(InETI)、地方旅游收入(InLTR)三個指標作為解釋變量。其中:
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用InGFFPA來表示,從理論上分析,政府扶貧資金投入應與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增加呈同向變化,其回歸系數應該大于零。
企業旅游投資用InETI來表示,從理論上分析,企業投資應與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增加呈同向變化,其回歸系數應該大于零。
地方旅游收入用InLTR來表示,從理論上分析,地方旅游收入應與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增加呈同向變化,其回歸系數應該大于零。
為便于消除數據異方差,所有數據均取對數,分別為lnPCIit、lnGFFPAit、lnETIit和 lnLTRit,根據上述變量的設定,構建如下基本計量模型:

其中,i表示各貧困地區,t表示時間,ε表示隨機變量。
2.3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0—2015年湖北省下轄1個副省級市、11個地級市、1個自治州、3個直管市、1個林區的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旅游企業投資以及旅游收入等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分析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旅游企業投資、旅游收入之間的關系,探究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旅游企業投資、旅游收入等因素對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影響程度,研究貧困人口視角下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研究數據來自于湖北省扶貧辦、湖北省旅游委等相關機構的統計資料,并整理使用了《湖北省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數據來源與選取均客觀真實。
3 實證分析
3.1 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
為了確定面板數據的平穩性,需對其進行單位根檢驗,以保證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采用不同單位根ADF檢驗,只要檢驗中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即“不存在單位根”的結論成立,則說明本文中面板數據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反之則不平穩。
由表1得出,對InPCI、InGFFPA、InETI、InLTR進行單位根檢驗時,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不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結果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InPCI、In-GFFPA、InETI、InLTR“不存在單位根”,因此判定InPCI、InGFFPA、InETI、InLTR時間序列均是平穩的,因此,可對其進行協整分析。

表1 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結果
3.2 面板數據協整分析
對面板數據進行協整檢驗,確定其各變量間的均衡關系,以說明均衡關系機制形成的穩定性。本文協整分析采用兩變量的恩格爾—格蘭杰檢驗,即E-G兩步法協整檢驗方法,此檢驗方法是對回歸方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先進行協整回歸,然后檢驗殘差的平穩性,以判斷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由表2得出,以湖北省為研究單元,由于殘差ADF檢驗的τ統計量小于臨界值,且P值<0.05,這說明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存在協整關系。湖北省下轄地區的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存在協整關系。同理,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旅游企業投資、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旅游收入協整檢驗結果見表3和表4。

表2 殘差e1的平穩性檢驗
由表3得出,以湖北省為研究單元,由于殘差ADF檢驗的τ統計量小于臨界值,且P值<0.05,這說明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旅游企業投資存在協整關系。湖北省下轄地區的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旅游企業投資入存在協整關系。

表3 殘差e2的平穩性檢驗
由表4得出,以湖北省為研究單元,由于殘差ADF檢驗的τ統計量小于臨界值,且P值<0.05,這說明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旅游收入存在協整關系。湖北省下轄地區的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旅游收入存在協整關系。

表4 殘差e3的平穩性檢驗
3.3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由于解釋變量InGFFPA、InETI、InLTR與被解釋變量InPCI之間均存在協整關系,因此,可對InGFFPA、InETI、InLTR與InPCI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以此來判定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旅游企業投資、旅游收入之間的影響方向。本文選取滯后階數分別為1、2、3階,且在5%顯著水平上,檢驗結果見下頁表5。
通過對InGFFPA、InETI、InLTR與InPCI的面板數據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由表5可知:
第一,在滯后1~3階條件下,且在5%顯著水平上,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與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即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是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格蘭杰原因,此結果說明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影響著貧困人口的人均收入的增加,即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是提高貧困人口收入的影響因素。
第二,在滯后1~3階條件下,且在5%顯著水平上,旅游企業投資與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即旅游企業投資是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增加的格蘭杰原因。旅游企業在貧困地區的投資完善了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把發展旅游業作為帶動貧困地區發展的產業,不僅使其產業結構更為合理,而且為貧困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貧困人口可以就地就近就業,增加了貧困人口收入,解決了貧困地區的社會問題。此結果說明,旅游企業投資是提高貧困人口收入的影響因素。
第三,在滯后1~3階條件下,且在5%顯著水平上,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旅游收入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即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旅游收入之間具有雙向促進作用。貧困地區發展旅游業,促進了地區旅游收入的增長,并促使貧困人口就業,帶動了貧困人口收入的增加。貧困人口收入的一部分也會在本地進行旅游消費,會成為本地旅游收入的組成部分。此結果表明,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旅游收入之間具有雙向促進作用。

表5 InGFFPA、InETI、InLTR與InPCI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3.4 面板數據模型的選擇與估計
3.4.1 面板數據模型的選擇
本文根據F檢驗和Hausman檢驗判斷建立混合模型、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以InPCI為因變量,In-GFFPA、InETI和InLTR為自變量,進行F檢驗,從表6可知,F=6.2171>F0.05(14,89)=2.2,所以,判定排除混合模型。然后,進行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Hausman檢驗,從表6可知,Hausman檢驗統計量H=2.369<χ2(1)=3.8415,所以,判定本文應建立隨機效應模型,排除固定效應模型。因此,本文計量模型修改為:


表6 面板數據F檢驗和Hausman檢驗結果
3.4.2 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
因為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存在協整關系,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旅游企業投資存在協整關系,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旅游收入存在協整關系,根據面板數據模型選擇結果,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對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與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旅游企業投資與旅游收入的關系進行估計,結果見表7。

表7 隨機效應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根據估計結果可知:就全省整體而言,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增加1%,貧困人口年人均年收入將增加0.0826%;旅游企業投資增加1%,貧困人口年人均年收入將增加0.1204%;地方旅游收入增加1%,貧困人口年人均年收入將增加0.3782%。以上結果表明: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旅游企業投資與旅游收入對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具有正向影響;且三個要素對各地區的影響程度不同,武漢、神農架、黃石、宜昌、恩施自治州等地區,影響程度較大,而其他地區較小,具有地區分異的特點,估計結果見表7。就全省而言,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旅游企業投資與旅游收入的投入增長幅度,分別對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增長幅度的影響程度較低。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本文運用面板數據模型,通過湖北省2010—2015年旅游扶貧相關數據的實證分析,探究了貧困人口視角下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主要研究了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旅游企業投資、地方旅游收入對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影響程度。研究結論如下:(1)通過對面板數據進行ADF檢驗和協整關系分析,得出面板數據具有時間序列的平穩性,且具有協整關系,這說明了面板數據模型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和均衡關系機制的穩定性;(2)通過對面板數據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可知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與旅游企業投資均對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有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即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與旅游企業投資是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Granger原因;地方旅游收入與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增長有雙向Granger因果關系,二者雙向促進;(3)根據F檢驗和Hausman檢驗結果,判定本文需建立隨機效應模型;通過面板數據模型參數估計可知,就全省整體而言,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旅游企業投資、地方旅游收入增加1%,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將分別增加0.0826%、0.1204%、0.3782%。
4.2 理論意義
關于旅游扶貧經濟效應的前期研究,學者們大多從宏觀經濟效應出發,研究旅游扶貧對貧困地區經濟增長的總體貢獻,較少把研究關注點放在貧困人口的實際既得利益上。本文關注旅游扶貧經濟效應的微觀視角,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1)旅游扶貧的實現在于貧困人口的參與性,旅游業通過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旅游企業投資等為其提供就業機會,而貧困人口通過積極參與獲得個人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尤其是“精準扶貧”的提出與實施,讓我們更關注貧困人口,從“真扶貧,扶真貧”的理念出發進行旅游扶貧;(2)本文正是從微觀視角并基于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增長,探究各利益相關者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影響關系和作用機制,并運用面板數據模型,通過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估計政府旅游扶貧資金投入、旅游企業投資、旅游收入對貧困人口年人均收入的影響程度,以此來分析貧困人口視角下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是對以往學者研究成果的發展與補充。
4.3 實踐意義
貧困人口視角下的旅游扶貧是“精準扶貧”理念的體現,本文主要回應旅游扶貧是否能夠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帶動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問題,為有效衡量旅游扶貧微觀經濟效應提供了理論和實證研究基礎。(1)本文為政府旅游扶貧政策的制定和扶貧效果的衡量提供可以參考的依據,為制定下一步扶貧攻堅計劃提供基礎;(2)衡量旅游企業的投資是否有利于帶動當地村民提高收入水平,其扶貧微觀經濟效應如何,為制定旅游投融資和政府招商引資政策提供實證基礎;(3)在實際發展中,貧困人口是否能在地方旅游收入中獲益,這是本研究關注的一個重點,回答貧困人口在旅游發展中的整體獲益程度。因此,本文從微觀視角研究旅游扶貧經濟效應,對于旅游扶貧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