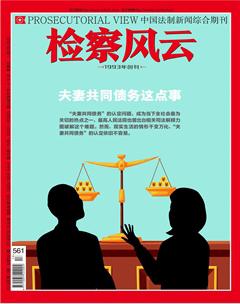夫妻共同債務,難以說清的“家務事”
史友興
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產生的債務,究竟是真債務還是假債務,是合法債務還是非法債務,是共同債務還是個人債務,往往難以區分,致使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與處理成為疑難問題。
丈夫賒款買彩票
巨額債務妻子脫身不容易
博彩,已成為一個十分狂熱的話題。不知有多少人為之瘋狂,在高額的獎金誘惑面前,不惜豪擲千金,甚至賒購彩票舉下巨額之債。賭債不受法律保護,而彩票具有賭博屬性,對賒購彩票所舉之債,能否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引發廣泛的關注。
29歲的馮坤寧,對彩票有些癡狂,妻子徐秋月有點看不慣,好幾回氣急了就和馮坤寧爭吵。
2017年3月2日,馮坤寧攜帶3萬多元和往常一樣,來到離家不遠的顧國忠開辦的體育彩票銷售站,通過對過往已經中獎號碼的一番研究分析,精心編選了一大串號碼。這天,馮坤寧自我感覺特好,認為自己精心挑選的這些號碼囊括了全部中獎機率,篤定能中得500萬元的巨獎,遂決定把選定號碼全部買下。可是,要買下全部號碼,需要近20萬元,但其身上攜帶錢款不足,就提出向顧國忠賒購彩票。
雖說馮坤寧賒購的數額巨大,但顧國忠考慮到馮坤寧是老主顧了,經過協商,馮坤寧同意當場支付31000元,余款158100元作為欠款隨后支付,由顧國忠先行向彩票投注機內充值為馮坤寧提供投注資金。
但造化弄人,馮坤寧所購彩票未能如愿中巨獎。他的發財夢破裂,也無能力支付剩余彩票錢。顧國忠在索要無果后,以馮坤寧、徐秋月是夫妻關系,所賒彩票款是夫妻共同債務為由,將馮坤寧和其妻子徐秋月一同告上了法庭,要求馮坤寧和其妻子共同歸還欠款158100元,并承擔利息。
法庭上,馮坤寧答辯說:“根據《彩票管理條例》規定,彩票發行機構、彩票銷售機構、彩票代銷者不得以賒銷或者信用方式銷售彩票。顧國忠通過彩票賒銷的方式向我銷售彩票違反了行政法規的強制性法律規定,系違法無效民事法律行為。”徐秋月在法庭上則說:“丈夫馮坤寧動用巨額資金購買彩票系賭博,屬丈夫個人行為,且彩票欠款并非用于家庭開支,該債務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銷售和購買體育彩票均為合法行為,馮坤寧向顧國忠購買彩票的買賣合同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系有效合同。馮坤寧向顧國忠賒賬購買彩票,應按約向顧國忠支付其尚欠的彩票款158100元。馮坤寧購買彩票的行為發生在其與徐秋月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其購買彩票的行為是一種投資,購買彩票中獎后的獎金系夫妻共同財產,購買彩票所負債務也應視為夫妻共同債務。法院依據法律的規定,作出了一審判決,判決馮坤寧、徐秋月共同支付顧國忠合同款158100元及利息。
點評:對賒銷彩票所形成的債務,是否屬于夫妻的共同債務,雖然本案中的兩級法院均認定屬于夫妻的共同債務,但因對此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爭議,也出現過不同的判決。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查詢,可知有些法院對此是不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的。
借錢為兒買婚房
離婚期間單方負債單方擔
離婚期間,一方為了孩子的利益,不惜舉債,在生活中并不少見。制造債務,目的是為了孩子,很容易為人們所理解,與道德也不相沖突。然而,合情合理的家庭債務,不一定就是合法的夫妻共同債務。
徐坤與郭靜曾是一對夫妻,兩人于1993年5月結婚。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不斷發生摩擦,直到夫妻感情破裂。2007年2月,徐坤就訴至法院,要求與郭靜離婚,后被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判決不準離婚后,徐坤與郭靜雖然繼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夫妻感情已在冰點。2016年2月,徐坤再次向法院起訴要求離婚。2016年3月,法院再次判決兩人不準離婚。這次判決不準離婚后,徐坤便搬出去租房另住,正式與郭靜分居。2016年11月15日,徐坤第三次向法院起訴要求與郭靜離婚。見徐坤要求離婚如此堅決,郭靜覺得沒有再挽回的必要了。因兒子到了成家立業的年齡,可婚房還沒有著落,郭靜向徐坤提出離婚前給兒子買一套婚房,但遭到了徐坤拒絕。郭靜便決定自己掏錢為兒子買套婚房。
郭靜看中了一套價值170萬元的房屋,但有30萬元的缺口,便向好友董學勇借款,共出資170萬元,為兒子購買了房屋1套。2017年年初,董學勇因急需用錢,就向郭靜催要借款。可是,讓董學勇沒有想到的是,郭靜提出,因丈夫徐坤從家中先后拿走了100萬元,且自己現在和丈夫正在鬧離婚,自己一個人已沒有能力償還借款。
董學勇認為,徐坤與郭靜夫妻雖然在鬧離婚,但畢竟沒有離婚,且郭靜借款的目的也是為了給雙方的婚生子購買婚房,由此形成的債務應當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在多次催要無果的情況下,董學勇將郭靜及徐坤一同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徐坤說:“本人與董學勇不是朋友,也不認識董學勇。郭靜存在虛構債務之嫌,其向董學勇所借債務的真實性無法確認。郭靜向董學勇借款即便屬實,因發生在本人起訴郭靜鬧離婚及雙方分居之后,向董學勇借款屬郭靜單方面的意思,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第一,郭靜在向董學勇借款時,徐坤已再次提起離婚之訴,郭靜向董學勇借款未征得徐坤同意。董學勇與徐坤互不相識,徐坤未參與郭靜向董學勇借款的洽談,故徐坤與董學勇間也不存在借款合意。第二,借款金額達30萬元,金額巨大,郭靜為兒子購房也是家庭重大事項,應由雙方共同協商處理,郭靜單方向董學勇借款,不構成夫妻家事代理。第三,他們的兒子已成年,郭靜為其購房并非履行法定的撫養義務。郭靜購房并未因此增加徐坤、郭靜的夫妻共同財產。第四,郭靜向董學勇借款發生在徐坤再次提起離婚之訴之后,在婚姻關系面臨解體之際,郭靜向董學勇借款目的是為了增加夫妻共同債務,增加徐坤的經濟負擔,其主觀上存在惡意。據此,法院認定郭靜向董學勇所借的30萬元為郭靜的個人債務,應由其個人歸還董學勇并支付利息。
點評:夫妻雖然在鬧離婚,但畢竟沒有離婚,且妻子借款的目的也是為了給雙方的婚生子購買婚房,由此形成的債務讓妻子一人承擔,似乎不太公平。但是,依據法律的規定,滿足孩子基本的生活、學習所需,是父母的法定義務,在鬧離婚期間,如果一方不履行義務,另一方單方為此所舉債務,則屬于共同債務。反之,則不構成共同債務,誰舉債誰償還。
雇工摔傷致殘
經營發生侵權債務共擔
對于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因生產經營行為對外所產生的侵權之債是否應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郭瑛與董文軒于1979年12月登記結婚。婚后的前幾年感情還不錯。可是,在共同生活中,雙方有了矛盾又不能相互溝通,夫妻感情一直動蕩不安。1989年,郭瑛曾起訴董文軒離婚,后經法院調解,撤回了起訴。2010年8月17日,雙方又協議離婚;離婚3年后,雙方于2013年11月6日又復了婚。誰知,復婚后的第二天,兩人又協議離婚了。
2010年7月11日,從事建筑施工的董文軒作為承包方,從發包方許勇、李濤處承接了一座寺廟的建筑工程。接到承建寺廟的工程后,董文軒聘請徐斌等人修建寺廟。
2010年8月8日,徐斌在修建云峰寺廟過程中,因所踩鈴木折斷,從高處跌落摔傷致殘。事故發生后,因雙方就醫療費、殘疾賠償金、殘疾輔助器具費等損失的賠償問題無法協商一致,徐斌遂向法院起訴,要求董文軒、許勇、李濤連帶賠償其醫療費、殘疾賠償金、殘疾輔助器具費等11項損失共計112萬余元。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董文軒作為雇主應當對徐斌受傷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許勇、李濤作為工程發包方,將工程發包給沒有資質的董文軒,應當對徐斌受傷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遂于2011年5月23日作出了判決,判決董文軒、許勇、李濤連帶賠償徐斌11項經濟損失共計50萬余元。
該判決生效后,董文軒、許勇、李濤未在指定期間履行金錢給付義務,徐斌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但因董文軒、許勇、李濤沒有什么財產,致使執行款不能及時到位。徐斌認為他在2010年8月8日發生事故時,董文軒與郭瑛沒有離婚,但在事發后第九天的8月17日,董文軒就與妻子郭瑛協議離婚,且兩人協議離婚時,夫妻共有的六間房屋,董文軒只分得面積為16.5平方米的房屋一間,其余面積為112.47平方米的五間房屋全部歸郭瑛所有,有逃避承擔責任之嫌,遂以董文軒對其承擔的賠償損失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為由,將郭瑛告上了法庭,要求判令郭瑛與董文軒共同承擔賠償之責。
郭瑛答辯稱:本人與董文軒早就沒有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徐斌在起訴董文軒的時候就沒有提到本人的連帶責任,經過幾年后才要求郭瑛承擔連帶責任,其原因在于得知本人獲得了政府的征地房屋拆遷補償,所以才起訴承擔連帶責任。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中的債務雖發生在郭瑛與董文軒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但系徐斌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而引發的侵權行為之債,董文軒作為雇主承擔賠償責任是基于法律的規定,郭瑛并非徐斌的雇主,且對徐斌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也無過錯。董文軒作為雇主對徐斌承擔賠償責任,并非董文軒夫婦合意舉債,而系夫妻一方的侵權行為引起的,郭瑛也未因該侵權之債獲取利益,故顯然不屬于郭瑛與董文軒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徐斌要求郭瑛對董文軒因侵權產生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無法律依據,不予支持,遂判決駁回徐斌的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徐斌不服,提出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后,維持了一審判決。兩審均敗訴,徐斌還是不服,向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審申請。省高院經再審認為,徐斌主張要求郭瑛與董文軒承擔連帶責任的債務,系董文軒因雇主行為而依法對徐斌承擔的侵權之債,該債務產生于董文軒與郭瑛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且董文軒承包修建寺廟的行為系生產經營行為,所得的收益依法屬于其與郭瑛夫妻共同所有,根據權利義務對等原則,郭瑛從該經營行為分享了利益,也應當對該經營行為所致債務承擔相應的義務。故本案中董文軒對徐斌負擔的債務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省高院遂作出判決,判決撤銷了一二審法院的判決,改判郭瑛對董文軒所負擔的徐斌的債務501898.03元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點評:夫妻一方因生產經營行為產生的對外侵權之債,不同于夫妻一方因家庭共同生活所需借貸所產生的對外之債。夫妻一方的生產經營行為,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增加具有預期性,且因生產經營行為產生對外侵權之債,也非必然,而是一種風險。不參與生產經營的夫妻另一方,在分享夫妻一方因生產經營帶來的夫妻共同財產預期效益時,也應承擔對因生產經營行為產生對外侵權之債的風險。
受托炒股損巨款
保底承諾配偶可拒高風險
李明與張娟原系夫妻,后于2016年3月1日協議離婚。李明有幾位同學,在證券公司上班,對炒股很有研究,常常接受他人的委托,幫助他人炒股,掙到的錢雙方平分。李明接受同學的委托,常常幫朋友撮合委托理財事宜。
潘妤是李明的朋友,手上有些富余的資金,得知李明能幫助介紹理財高手幫助理財,就托李明幫忙。在2014年以前,潘妤在李明撮合下,多次簽署委托理財協議,委托他人炒股,從中也掙得了不少的錢。
在與同學的交往中,李明耳濡目染,對炒股也頗感興趣,漸漸摸到了一些門道,自我感覺不錯,也想試試接受他人委托幫助炒股。2014年6月,潘妤與別人委托理財的合同正好到期,又委托李明幫其介紹理財高手,李明就說:“你別委托別人了,我幫你理財吧。”
這樣,2014年6月17日,李明與潘妤簽署了一年期委托理財協議,潘妤在自己的炒股賬戶中注入10多萬元,然后將賬戶及密碼交給李明,由李明使用潘妤的賬戶及10多萬元的資金進行炒股,雙方約定按“5∶5”的比例進行收益分配;李明承諾如發生虧損,將不足資金補給潘妤。
還真別說,李明通過“杠桿炒股”操作,大膽、精心、謹慎理財,僅僅一年的時間,利用10余萬元的本金,就為潘妤賺到了360萬元。潘妤也信守承諾,在合同到期后,按照合同的約定,將李明應分得的投資收益180萬元匯入李明的銀行賬戶。
合同到期后,李明與潘妤又于2015年6月17日重新簽訂了一份內容完全相同的協議,只是這次潘妤投入的資金為200萬元。合同簽訂后,李明按照合同的約定,用潘妤的賬戶進行炒股。然而,因股市動蕩調整,這一年,李明卻敗走麥城,虧損了194萬余元。
由于虧損數額太大,李明一下子籌集不到這么一大筆錢來補足潘妤的虧空,雙方發生糾紛。潘妤認為,雖然李明與張娟離婚了,但合同簽訂時兩人并沒有離婚,便將李明及李明的前妻張娟一同告上了法庭,請求判令李明與張娟共同支付虧損款194萬余元及相應利息。
李明對潘妤的起訴沒有意見,但認為這是他的個人債務,與張娟無關,他個人愿意承擔該債務。
張娟辯稱,1.其并不知曉雙方簽訂委托理財合同;2.其因與李明感情不和,于2016年3月解除婚姻關系;3.李明僅代為炒股,并不實際獲取原告資金,且雙方結算發生在婚姻關系終止后;4.該債務非為家庭生活或經營所負。綜上,該債務系李明個人債務,不應由本人承擔還款責任。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第一,從委托理財協議的簽訂看,雖簽訂時間在李明與張娟的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內,但是均系李明一人參與、一人簽字確認,并無張娟簽字認可,且被告張娟事后亦不予追認。第二,從委托理財協議的內容看,李明的債務源于對證券投資本金的安全保證承諾,該條款通常被稱為“保底條款”。鑒于李明自愿承擔潘妤全部損失且依本案審結情形不會侵犯第三方利益,故可予準許,但李明對“保底條款”的承諾,實際上將高風險轉化成配偶一方對委托方的保證,損害了妻子的權益。第三,李明雖曾于2015年獲得過一次原告分配的收益,但是該款直接匯入李明銀行賬戶,從外觀上不能直接得出張娟據此受益,結合被告張娟具有正當職業等情形,現有證據尚不能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綜上,法院作出判決,判決李明向潘妤支付194萬余元及利息,駁回潘妤對張娟提出的訴訟請求。
點評:證券投資損益具有高風險性、不確定性。委托投資協議確定的“保底條款”,事實上將高風險轉嫁于受托方,受托人對“保底條款”的承諾如因婚姻法律關系發生牽連,實質轉化成配偶一方對委托方的保證。夫妻一方未經配偶同意對外承擔保證責任,配偶不能當然也負有該保證義務。
(為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文中人名作了相應的技術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