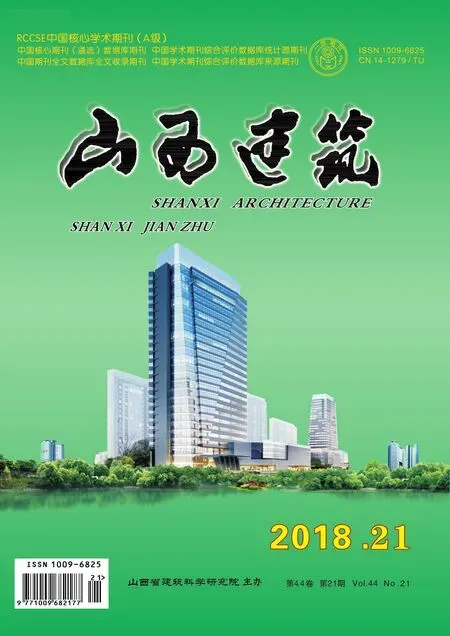老齡化背景下公共服務設施可步行性優化策略
劉 暢
(黑龍江科技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2)
1 研究背景
自1999年中國步入老齡化社會,關于養老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居家養老逐漸成為養老的主要形式,社區公共服務設施逐漸成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核心載體[1]。街區空間形態既表現了城市的社會經濟文化活動,又決定了公共服務設施的可步行性。由于老年人身體機能的衰退,其出行主要方式為步行,公共服務設施是否可步行,一方面將影響到公共服務設施的集聚效益是否最大化,另一方面將影響到老年人日常生活質量。
近些年來,哈爾濱市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老舊街區的滯后發展,忽視了老年群體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時,交通體系的變化,哈爾濱市老舊街區步行環境被機動交通侵蝕。因此,結合老年人的需求,客觀分析街區空間形態對公共服務設施可步行性的影響,對探討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布局,增加公共服務設施可步行性以更好地發揮公共服務設施對老年人服務功能具有重要的意義。
20世紀初期,國外學者對可步行性的研究不斷深入。從研究對象上來看國內外對可步行性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出行目的地的研究、步行出行環境的研究兩個方面。研究表明,公共服務設施均衡布置、高連通性的路網、緊湊的用地開發模式、公共服務設施混合使用模式[2-5]等都可以提升人們步行至公共服務設施的可能性。2007年美國研究者提出“步行指數”概念,對日常服務設施的可步行性進行評價[6]。我國諸多學者從使用頻率、使用多樣性、使用的距離衰減規律三個方面對服務設施的可步行性進行分析,建立步行指數模型[7-13]。
根據以往的研究,關于目的地可步行性的研究主要采用“步行指數”法,研究中缺乏對步行者主觀感受和需求的關注。此外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面向大眾人群的、配套設施較全面的住宅區日常服務設施上,很少在老舊街區層面探討以老年需求特征為出發點的公共服務設施可步行性的關系。本文從街區空間形態的視角,揭示與老年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布局與可步行性間的關系。
2 數據和方法
2.1 研究區域及數據獲取
本文以哈爾濱市道外區二十道街—太古街—景陽街—大新街—北新街圍合部分為研究區域,為方便以下簡稱為道外街區。
為突出老年人服務設施可步行性的側重點,以獲取相應公共服務設施POI數據,根據GB 50442—2008城市公共設施規劃規范、《老年住區開發建設導則》(中國中建設計集團有限公司(直營總部)技術文件)及對現狀街區的調研,選取醫療衛生設施、文化休閑設施、商業配套設施三大類,13小類公共服務設施,各類公共服務設施空間統計見表1。

表1 公共服務設施統計
2.2 研究方法
2.2.1核密度分析法
本文利用核密度分析法以直觀反映各設施點的空間集聚情況,經實驗選取200 m為距離閾值。
2.2.2空間句法分析法
本文先利用軸線分析法選取整合度、可理解度、協同度從整體角度對街道空間形態進行分析。軸線分析忽視距離因素,所以引入線段分析法使得拓撲空間更加貼近實際街道空間。
3 分析結果討論
3.1 設施點空間集聚熱點分析
利用ARCGIS10.2對哈爾濱市道外街區醫療衛生設施、文化休閑設施、商業配套設施進行核密度分析,如圖1~圖5所示。



道外街區醫療衛生設施呈現多核心分散布局模式,主要在北十四道街、南七道街、南十道街、南十六道街附近集聚。對于文化休閑設施,通過調研主要選取社區服務中心、棋牌室、老干部活動中心、活動中心、花鳥市場進行分析,從表1我們可以發現,該區域文化休閑設施類型單一,數量較少,難以滿足老年人群最低需求。文化休閑設施網點分散(主要為各社區中心),難以形成聚集區。商業配套設施數量相對較多,呈現多核心分散布局模式,主要集中于南新街與南十九道街交匯處,南新街與南十六道街交匯處,靖宇街與南十五道街交匯處,南勛街與南七道街交匯處。其中,發現區域內無專門的老年人餐飲中心,主要能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務的為街區餐館、還有一些養老機構,呈點狀分布于街區空間的幾何中心。街區整體公共服務設施為多核心分散布置,且各個核心之間呈帶狀聯系,關聯性較強。設施多集中在街區的東北部分,越趨近西南部分設施越少,設施聯系度越差。
3.2 街區空間形態分析
3.2.1軸線分析
1)整合度分析。
通過整合度計算與公共服務設施密度的對比分析可以發現(如圖6所示):
a.公共服務設施網點的集聚區域為街區的整合度核心及其附近區域,且集聚區與街區外部空間均聯系緊密,增加人們對于設施網點的可達性(如圖3所示);
b.以北十四道街為界,兩側地塊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空間形態,經計算,左側街區平均選擇度值為略高于右側街區,公共服務設施形成不同的集聚形式。左側為歷史核心形態,其表現為長進深線條形的空間形態,內部院落式空間布局,構成內向型空間,人們在空間中更易于集聚。設施網點多自發集聚在空間的幾何中心上,但受該處部分地塊功能(歷史文化)與空間環境等外力的影響,設施網點多集聚在與整合度較高、選擇度較高且與外部空間有較好聯系的空間網絡上;右側地塊為傳統擴展形態,由較為簡單的方格網式形態構成,街區內無大型封閉小區,人們在空間中能夠自由穿行,表現為外向型街區,經計算其平均選擇度較左側街區低,街道吸引穿越人流的能力較弱,人們在空間中呈現分散式流動,致使設施網點呈現均衡分布狀態。

2)人流分析。
本文研究的設施使用主體為老年人群,位于易辨別方向、易找到、可交流空間上的設施更有利于老年人使用。現狀街區空間可理解度為0.275<0.5,空間的關聯性較弱,在街區空間中老年人難以從局部空間對整體進行方向、信息等的判定,易于迷失。為提高可理解度,設施宜布置在整合度、連接度均較高的空間中,這類空間彼此間緊密聯系,與外部空間的拓撲距離為1,且空間連通性好且無轉折形態。街區空間協同度為0.615,人群在空間中的活動均衡無明顯的集聚區,因此多核心分散式的設施布局更加有利于人群獲得相應的服務。
3.2.2線段分析
在上述分析中對道外街區空間與設施布局的關系進行闡述,并提出多核心分散式的設施布局,本文繼續采用線段分析法來分析在街區空間的作用下不同類型、規模的公共服務設施的布局問題。通過調研,老年人步行出行可接受距離為1 000 m,以此為半徑對角度選擇度、角度整合度進行分析。
零散型設施網點(如商店、藥店、診所、餐館、活動中心等)規模一般較小,此類設施,老年人主要關注獲得設施的便利性。靖宇街西南段、南勛街中部、北十四道街、仁里街及南十六道街中部具有較好的被穿過性,作為運動通道的潛力更大,且這類空間多在整合度較高的空間上集聚,且依托城市支路分布,將零散設施網點布置在這類空間中對老年人基本的生活需求帶來便利(如圖7所示)。集聚型設施網點(如醫療中心、購物中心、商業綜合中心等)規模較大、等級較高,老年人出行至此類設施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南十四道街與靖宇街交匯處周邊區域角度整合度大并向東南方向延展,該空間具有較高的吸引力,容易形成人流匯集地,將集聚性設施網點布置在該類空間上,有利刺激老年人的目的性步行出行(如圖8所示)。

4 結語
本文對哈爾濱市道外街區的調研,結合現有公共服務設施空間數據,利用空間句法分析法,考察街區空間形態與公共服務設施可步行性的內在關聯性,得出以下結論:
1)街區空間模式對于公共服務設施的可達性有著極大的影響。
街區空間為老年人群出行的活動載體,其空間形態影響著老年人對設施網點的獲取。方格網式小街區,道路通達性好,空間界面簡單,老年人在空間中可以自由穿行,因此設施網點的均衡分布有利于老年人對設施使用;歷史街區,進深過長、內部院落式布局,空間構型復雜。設施網點集聚式布局,在復雜的空間形態中呈現出明顯的集聚核心,刺激老年人的出行且增加老年人步行出行至設施網點的標識性。在街區空間中,高整合度的街道網絡對于老年人來說可達性越高。將集聚性公共服務設施布置在整合度核心區附近,老年人至公共服務設施更加方便,提升設施共享性的同時促進老年人群對社會活動的參與度。盡量避免將公共服務設施布置在整合度較低區域,以減少無效設施造成的資源浪費。
2)注重道路網絡的規劃,增強城市支路的服務功能。
基于空間可理解度與整合度分析可知,盡端路造成空間不連通,降低空間可達性;轉折路使得空間迷失度大從而致使空間可達性較差。因此,為提高設施的可達性,最大可能的減少盡端路與曲折道路的使用,且避免將設施布置在其上。城市支路為生活性道路,將老年人群與設施網點進行空間上的聯系。增加城市支路的密度,改善支路的環境,為老年人營造一個舒適安全的步行環境,提高老年人步行至服務設施的道路連通性與選擇性,以充分發揮支路的空間紐帶作用。
3)公共服務設施布局宜“大集中、小分散”。
公共服務設施布局過于集中使得土地開發強度過大,密度過大,設施分配不均;公共服務設施布局過于分散使得設施利用率過低,土地資源浪費。通過對空間形態分析,角度整合度較高的街道段具有較強的吸引力,等級較高的公共服務設施置于此區域內形成功能核心;角度選擇度較高的街道段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一般性公共服務設施網點置于此區域內形成功能點,形成不同層級服務圈層,提高老年人對公共服務設施的可獲得性,促進公共服務設施的可步行性。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不足。在應用空間句法過程中存在著人為因素的干擾。其次,哈爾濱市道外區數據較少,在進行數據爬取、分析時會存在一定誤差,僅做參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