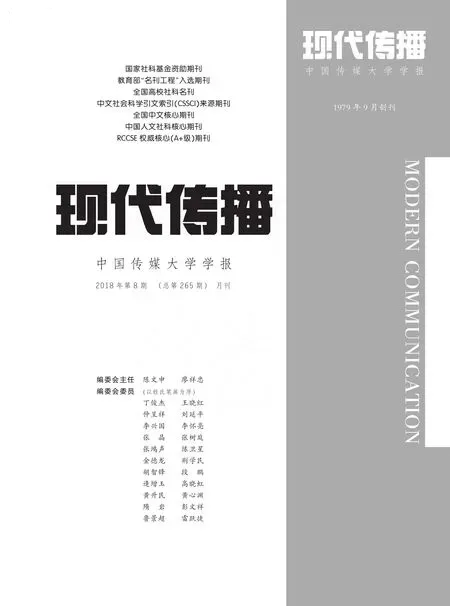論人工智能出版的版權邏輯*
■ 王志剛
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ience,AI)在出版傳播領域得到越來越為廣泛的應用。在當下的出版實踐中,我們看到基于用戶大數據分析而新興起的新聞內容智能傳送平臺(如今日頭條),也能看到一些傳統媒體自行研發出的機器人編輯(如《紐約時報》的Blossomblot),都是通過智能分析輔助挑選出潛在熱文,以達到推送文章“病毒式”傳播的效果。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其應用領域也不再限于“傳播”環節,而是逐漸向內容的智能化生產領域滲透,如一些新聞媒體平臺紛紛推出智能寫稿平臺(見表1),一些出版商也推出人工智能圖書(如湛廬文化推出由微軟小冰創作的《陽光失了玻璃窗》)。不僅如此,隨著多媒體內容智能生產技術的不斷突破,一種創意多樣表達的全媒體智能出版平臺將成為現實,由此也將催生出一個人工智能出版高峰。如果說今天大量的機器人新聞稿仍屬于版權保護之外的“單純事實性消息”,未來人工智能則會創作出大量可版權的獨創性作品。這一發展趨勢也帶來一系列問題:人工智能出版物有無版權?若有版權則應如何判定歸屬?在人工智能出版時代應該采取哪些措施予以保護?由此可見,人工智能技術給出版產業帶來生產傳播便利的同時,也對現有版權制度體系形成挑戰。人工智能出版物的版權性質、歸屬以及保護措施等問題必須厘清,否則將對整個文化產業創造環境形成沖擊。
一、人工智能出版物的權利性質
界定人工智能出版物的權利性質,解決的是這種特殊模式下生產的內容產品是否擁有版權的問題,其前提是要解決人工智能出版物能否構成版權意義層面的作品。從世界范圍版權立法實踐來看,能否將人工智能出版物視為作品爭議不斷,但人們又在積極想辦法利用版權改革解決這一因技術發展而引發的新問題。

表1 國內外主要新聞機器人
(一)人工智能出版物能否擁有版權引發爭議不斷
人工智能創造物是否擁有版權,一直爭議不斷。早在上世紀50年代,在計算機技術剛剛興起之時,美國就對“機器創作”產品應否給予版權展開討論。當時有人利用計算機創作上千首歌曲,然而由于美國版權局從未登記過由機器創作的作品,因而拒絕將該類歌曲視為作品加以登記。①此后較長一段時間內,美國版權局始終堅持認為版權保護的作品必須來源于人的創作,如1973年第一版的《美國版權局工作手冊》中明確提出這一觀點。②此后,美國國會為考察新技術如何影響著作權,成立了“版權作品新技術應用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New Technological Uses of Copyright Works),該委員會1978年發布的最終調研報告仍舊重申了版權局對待計算機程序生成內容的態度。③
關于人工智能創作物版權爭議也出現在澳大利亞。1993年,澳大利亞司法部曾在一份有關計算機軟件版權保護的報告草案中提出建議,要求增加計算機生成物為新的作品類別④,但這一提議遭到了澳大利亞版權委員會的反對,最為突出的反對理由是此類內容無法達到獨創性的最低要求。⑤這一反對理由也被澳大利亞司法部的版權審議小組所接受,在其發布的修改報告中,不再建議將諸如自動新聞寫作程序等計算機生成內容作為作品保護,而是建議將這類創造物視為一種創新的鄰接權客體,其名稱也由最初的“計算機生成作品”作品改為最終的“計算機生成內容”⑥。名稱上的差異明顯看出人工智能創造物在當時的澳大利亞沒有獲得具有版權價值的作品地位。
在爭議聲中,反對人工智能創作物擁有版權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一些人工智能創作物無法達到版權保護的“獨創性”要求,二是人工智能創作主體不是版權法所規定的具有情感的“人類主體”。因此由于人工智能產品不符合現有版權制度的原則性要求,在很長時間內無法得到“作品”的相應版權待遇。發生在美國、澳大利亞的版權爭議同樣也在英國、日本等國長期存在。
(二)人工智能出版物視為版權作品漸成趨勢
隨著機器學習技術的不斷進步,涵蓋出版產品在內的人工智能創作物內涵漸趨豐富,獨創性日益明顯,逐漸具備了作品的基本特征。這一現實也促使世界各國開始重新審視機器創作的“絕對輔助”角色認知。
美國對待人工智能創作物的態度在1986年有所轉變。當時美國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在重新研究計算機程序生成內容的問題時,認為隨著計算機程序與操作者互動性的日趨增強,計算機在某種程度上有被視為合作作者的可能。⑦現實也正如該機構所預測,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機器創作逐漸從輔助角色轉向直接參與創作,特別是在視覺藝術領域,很多作品(尤其是繪畫)已具備了成熟風格,完全滿足獨創性要件。在這一現實下,如何認定人工智能等機器創作物的可版權性及其權利歸屬,已經成為美國現行版權法下一步要重點解決的議題。
由于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日本也正在謀求修改現有知識產權制度,謀求賦予人工智能出版物的作品地位。長期以來,由于人工智能創作物無法滿足日本《著作權法》第2條第1項所規定的“創造性地表達思想或者感情之物”的要件,因此無法產生著作權。⑧目前日本正在討論修改現存版權制度,建立像商標那樣保護人工智能創作物權利的新注冊制度,以代替傳統著作權。由此看出,隨著算法和機器學習的不斷進步,人工智能出版物的獨創性也已經逐漸達到知識產權的保護標準,因此在制度層面應該給予相應的版權作品地位。
二、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權的權利歸屬
在關于人工智能出版物享有版權保護的反對聲中,內容的非獨創和主體的非人類是最為重要的兩大理由。在上文的論述中我們發現,隨著算法的進步,基于機器學習技術的人工智能產品已經具備了高度獨創性,因此賦予其作品以版權保護理所當然。而第二個反對理由——人工智能創作主體的“非人類”特征,則涉及到人工智能作品版權的歸屬問題。按照目前大部分國家的現存版權法,具有主觀情感的人類才是唯一可能的版權保護主體,顯然,如果這類特殊作品的版權歸屬給人工智能機器則無法符合制度要求,也無法得到現有制度保護。現實中人工智能作品越來越多,理清人工智能出版物的版權歸屬問題成為當務之急。
(一)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權歸屬的理論困境
關于人工智能出版物權利主體的討論,目前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人工智能本身是否可以成為著作權人;二是人工智能作品權利主體的適用原則能否統一。
1.人工智能本體主體化有悖傳統民事法理
人工智能產品雖然因其獨創性而具備版權保護價值,但由于人工智能本身也是一種由人類作者所創造出的產品,因此在目前的知識產權法理層面很難成為獨立的權利主體。有學者從司法中權利主體和客體地位出發,指出人工智能不可能從權利客體轉為權利主體,只可能是法定支配權的對象。⑨
這種認識觀目前被大部分國家所接受,包括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在大陸法系國家,民事法律關系主體通常被理解為享有民事權利、負有民事義務和承擔民事責任的人,強調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相對應,也要求履行相應的民事責任。而人工智能雖然可以創造財富,但其本身無法支配財富,因此也就無法承擔自然人所承擔的侵權責任后果(如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故無法成為權利主體。在英美法系國家,也將法律責任的承擔視為構成權利主體的重要條件。如英國1981年對《版權、設計和專利法》的修訂時,在對計算機創作物的作者認定條款修訂時指出,“計算機創作物的作者,應是通過操作軟件程序處理數據并對此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的人”。其后,澳大利亞也采用同樣的立法模式,將權利主體授予應該承擔法律責任的人。
隨著社會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等自然人以外的權利主體也被版權法所確認,這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但人工智能能否成為權利主體應從現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衡量。之所以目前不宜賦予人工智能權利主體資格,主要因為“機器人不是具有生命的自然人,也區別于具有自己獨立意志并作為自然人集合體的法人,將其作為擬制之人以享有法律主體資格,在法理上尚有斟榷之處”⑩。當然,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工智能軟件達到高度智能化,并具備類似于人類的創作水平和獨立思考能力,屆時立法同樣會考慮賦予人工智能的權利主體地位。
2.人工智能作品權利歸屬的判定原則存在分歧
目前大部分國家雖然一致認同人工智能本身不能成為適格的權利主體,但人工智能作品版權到底歸屬于誰也未能得到統一。由于人工智能創作過程中所涉主體相對復雜,因此其作品的權利歸屬也存在分歧。
首先,關于人工智能作品版權權利歸屬,理論層面缺乏統一的適用原則。學術界關于人工智能作品版權歸屬的討論,有編程者獨立權和操作者獨立權的紛爭,也有學者提倡二者共有人工智能作品版權。此外,一些學者建議將人工智能作品視為類職務作品,從而按照傳統版權制度的職務作品版權歸屬原則去界定。還有學者建議為人工智能作品創設虛擬法律人格,從而解決人工智能本體不能“人格化”的問題。這些理論在一定意義上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如編程者獨立享有人工智能作品版權顯然抹殺了操作者的獨創貢獻,操作者獨立權同樣忽略了編程者設計人工智能本體的創作活動。共有說意圖用合作作品的形式去解決編程者與操作者的矛盾,但卻很難發現一部合作作品產生所需要的創作合意和行為。職務作品理論很難適用于廣泛的操作者群體,虛擬法律人格理論也存在適格主體如何承擔法律責任的問題。面對人工智能作品版權的權利歸屬,學術界尚未總結出一個可以廣泛適用的原則性理論。
其次,在實踐方面,各國關于人工智能作品版權歸屬也存在著多種立法選擇。總體來看,目前國際社會主要有兩種立法選擇:一種認為應當屬于編程者,如美國的司法判例就傾向于此。這種立法選擇認為編程者創作了人工智能,因此應該由編程者享有人工智能產品所產生的作品著作權。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當屬于程序操作者或使用者,比如英國、南非、新西蘭等國,這些國家認為人工智能作品版權應該歸屬于軟件使用者或操作計算機軟件的人。國際組織也曾試圖統一人工智能版權歸屬原則,比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曾系統開展關于人工智能作品版權歸屬的大討論。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于1979年就召開過關于利用計算機創作作品的版權問題會議,其關于機器創作作品的權利歸屬結論傾向于編程者。而1991年3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又在斯坦福大學召開了“人工智能的知識產權問題國際研討會”,對人工智能與知識產權的關系進行討論,其關于權利歸屬結論開始傾向于操作者。經過這一矛盾階段后,鑒于人工智能作品版權歸屬的復雜性,目前國際知識產權組織不再就此出臺原則性意見,而是選擇交由各國自行解決。
(二)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權歸屬的現實安排
隨著人工智能作品的大量涌現,人工智能出版物的權利歸屬問題亟待解決,一些原則性的規定必須盡快推出。歐盟法律事務委員會就在近期對歐盟委員會提出建議,要求對于計算機或者機器人創作的可版權作品,盡快提出界定人工智能的“獨立智力創造”的標準,以便明確版權歸屬。筆者認為,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權歸屬原則的確定,一方面要尊重智能技術變化規律,另一方面,現階段要以“歸屬操作人”為主要導向。
1.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權歸屬應尊重技術變化規律
按照“智能化”程度高低,人工智能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依托于硬件的“準智能”、依托于計算機軟件的“算法智能”和基于人工神經網絡的“全腦仿真智能”。智能化技術發展階段不同,其權利歸屬也應由不同的分配原則。
“準智能”階段所產生的作品,主要是使用者依托于各種硬件進行創作,如照相者使用照相機在不同心情和場景下的精心構圖,照片這一作品的權利人應是相機的使用者。因此“準智能”階段人工智能作品的版權歸屬以使用人為原則。
在“算法智能”階段,其顯著特征是各種軟件的運用,比如音樂自動生成軟件、美術作品自動生成軟件、新聞類作品自動寫作軟件等。本階段中編程者設定了學習過程和方法,即授予人工智能收集數據、學習數據的方法,但此階段的人工智能并未脫離編程者的算法架構而具備獨立創作算法的能力。如機器人新聞就是使用算法自動地從結構性數據中生成新聞,但算法限定了數據的結構、報道的主題、常用的模版。因此這一人工智能產品還不能達到完全自主的獨創版權作品,需要人類用戶配合使用。最終作品的產生,雖然是依據使用者提供的素材而產生,但卻是遵循編程者提前預置的學習和生成方法,因此編程者和使用者均涉及該作品的權利及其責任。由此看出,這一階段人工智能作品的版權歸屬必須考慮編程者和使用者的共同權益。作為人工智能的過渡階段,這一時期作品的版權歸屬原則必然較為靈活,以適應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需求。
而在模仿人類生物神經的全腦仿真階段,人工智能達到高度“智能化”,因而具備一定的自我學習和輸出能力,屆時人工智能本身可能會成為作品的版權主體。當然,即便人工智能軟件被認定為作者,由于機器本身無法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因此最初制造此軟件的最初編程者仍應視為共同作者,在權利、義務以及責任方面承擔共同責任。
2.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權應以歸屬操作者為導向
雖然當前以算法智能為基礎的人工智能作品版權涉及編程者與操作者,但從產業發展推動以及作品權益實現來看,提倡一定前提下將人工智能作品版權歸屬為操作者較為合理。
人工智能作為新興產業,需要編程者的設計創新,更需要操作者在內容方面的創新性應用。當操作者利用人工智能軟件創造出新產品時,雖然是基于編程者的算法或預置程序,但作品主題的選定和素材的選用無不體現操作者的創作意圖,最終推出的出版物在實現操作者創作意志的同時也豐富了人類文化寶庫。在一定前提下,將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權歸屬于操作者,無疑會激發創作熱情,有利于人工智能創作作品的爆發性成長,這也將倒逼人工智能技術和整個產業的快速進步。基于這一認知,2016年12月,國際標準化組織“電氣與電子工程協會”(IEEE)在其標準文件草案《合倫理設計: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統(AI/AS)最大化人類福祉的愿景》中也提出人工智能作品版權歸屬的基本原則:如果AI依靠人類的交互而創造新內容,那么使用AI的人應作為作者或發明者,受保護程度與未借助AI者相同。可見,只要人工智能軟件創作作品無法脫離人的幫助,那么其出版物版權歸屬應當遵守“操作人優先”原則。
當然,“操作人優先”原則的實現有著一個必要前提,就是需要人工智能軟件的編程者或投資人放棄基于軟件所產生的作品版權。從目前來看,版權歸屬的“操作人優先”原則也得到人工智能軟件編程者或投資商支持。如在2017年5月,湛廬文化推出由微軟人工智能軟件微軟小冰創作的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市場大受歡迎,盜版等問題也隨之四起,一時間關于其作品版權問題也引發紛爭。然而在2017年7月5日,微軟(亞洲)互聯網研究院宣布放棄小冰所著詩歌版權,推出人工智能與人合著新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人工智能軟件完成初步創作,而人類作為使用者在此基礎上完成創作,最終由此產生的作品全部版權則由使用者獨享。可以想象,在這一聲明下,會有更多的人去使用微軟小冰,這樣一方面擴大微軟人工智能產品的影響,同時使用記錄也能為微軟的進一步研究提供數據積累,最終也能推動整個人工智能產業的快速發展。
三、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權的保護路徑
盡管人工智能作品版權有著爭議,但隨著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出版物涌入市場,成為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面對技術變革引發的新局面,我們必須積極調整版權制度,創新版權管理方式,在明確人工智能出版物具有可版權性的基礎上,給予其相應法律保護。基于人工智能出版物的特點,筆者認為當前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權保護應該堅持以下兩點,一是將人類作品與人工智能出版物區別對待,二是設立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權登記制度。
(一)將人類作品與AI作品版權進行區別管理
雖然人工智能出版物因其獨創性而應受到版權保護,但是由于其創作主體的特殊性,在具體作品版權管理過程中,應當與人類作品版權區別對待。
傳統版權法強調作品權利主體的自然人屬性,一方面是為激勵人類的創造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富含人類情感的文化產品才能引發閱讀者的共鳴。一部獨創性作品,本質上是作者情感、知識與人格的表達,而讀者閱讀、欣賞作品過程中的收獲與感悟,實質上是穿越時空與作品作者的精神交流。人類通過閱讀這種特殊的互動行為,使內心得到溫暖和豐盈。而這一切的起源,在于作品背后是作者情感的表達。通過文本,讀者體驗到的是作者情感與觀點的流露。
而人工智能出版物與傳統的人類作品有所不同。盡管AI作品已然具備獨特的人文價值,甚至一些作品若不告知為人工智能創作很難區分,但畢竟創作過程中加入了強烈的“機器”元素。人工智能作品的閱讀,讀者交流的對象不止操作者這個人類,大部分情況下,其“交流”的對象變成程序代碼或邏輯演算。如果當你知曉自己面對的是一部AI作品,內心一定無法產生類似的互動共鳴,因為在你心中,此刻閱讀文本背后的創造主體虛無縹緲無法追尋。即使未來人工智能創造出人類無法比擬的作品,但我們還會更為關注人類所創造出的杰出作品,因為只有這樣才會使我們感到興奮與震撼。
如果說移動互聯等數字技術的出現在傳播層面對版權制度提出了挑戰,那么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是從作品創作伊始就沖擊著現有版權制度的架構。因此我們在創新版權制度設計時,必須有這樣一個基本的判斷:即便將來有大量的人工智能出版物涌入市場,人們依然會對傳統人類出版物保持興趣和需求。新的規制方案,需要就人工智能出版物設計出一套新的版權制度,將人工智能出版物和傳統人類作品區別對待,以推動兩類作品共存發展。
(二)創設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權登記制度
面對AI出版的迅速崛起,傳統版權保護中作品版權的自動保護原則已經遭到嚴峻挑戰,而創設新的版權登記制度則是大勢所趨。
1.重建版權注冊制是數字時代版權法改革趨勢
在早期版權制度中,作品要獲得版權保護也需要一個類似商標、專利權一樣的履行注冊手續,但隨著版權制度發展,自動保護原則成為國際主流。這一原則也成為《伯爾尼公約》的主要原則之一,因此目前世界范圍內大部分國家都堅持作品版權的“無手續”。自動保護原則給作者帶來一些好處,如作者不會因為沒有注冊或無版權標記而導致其作品進入公有領域,喪失自身權益。然而,這種“無手續”的自動保護選擇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一方面,“無手續”導致人們很難找到真正權利人,授權層面的實質困難會損害創作者以及后續使用者的利益;另一方面,“無手續”也影響了作品再次開發的空間,因為商業開發者很難去判斷哪些作品作者希望被嚴格版權保護,而哪些不是。尤其在數字時代,某些作品很少或幾乎沒有商業價值,如電子郵件、商業備忘錄等就屬于缺乏獨立商業價值的作品,對其保護也無法體現版權制度的激勵目的。而博客等特殊作品形式,雖然享有版權保護,但其作者內心更加希望自己作品能夠被沒有限制或最低限制的廣泛傳播。而在作品的自動保護原則下,很多在商業層面“已經死亡”的作品,卻不能安全地被其他使用者作為“積木”,從而搭建出具有價值的新作品。在這種情況下,版權制度已經出現了某種失衡。
在這一背景下,重建版權注冊制成為近年來版權法改革的大趨勢。如2010年1月,美國“版權原則項目組”發表的《版權原則項目:改革方向》(The Copyright Principles Project:Directions for Reform)報告中,正式提出復興版權注冊制的改革建議。報告所提出的注冊制建議,不是簡單恢復舊有的手續要求,而是重新建構。在新的注冊制下,不遵守注冊程序并不導致作品進入公有領域,而是只影響權利持有人可以享有的權利以及救濟措施,從而降低使用未注冊作品的人的侵權責任風險。這一版權改革主張,適用于解決數字時代作品數量爆炸性增長與優秀作品相對稀缺的矛盾,也適應數字時代作品在傳播中創造增值的商業特征,因此得到美國出版協會、美國版權局以及各方利益群體的普遍支持。歐盟以及其他國家的版權法改革中也開始就重建版權注冊制議題展開討論。
2.版權登記制符合AI出版的技術特征
版權登記制度能夠明晰人工智能出版物的權利人,從而有助于維系版權利益平衡。版權制度的立法宗旨,是通過賦予權利人專有權,通過保護與限制并重的制度以激勵作品創作和傳播,其制度核心強調依據作品的傳播方式調整創造者、傳播者與使用者之間的利益平衡。人工智能擁有超越人類數倍的創作能力,因此在未來將涌現出海量可版權的作品。因此如果人工智能出版物不經過版權登記,作品來源無法判斷,侵權與否無法斷定,將使得作品傳播者、使用者以及演繹者無所適從。尤其是處于版權價值延伸鏈條上的出版商等傳播者,權利明晰至關重要,否則這些版權延伸產業將失去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版權登記制也是人工智能時代推進作品精英化的現實需求。強調人工智能作品的登記確權程序,一方面,能夠有效限制大量獨創性較低的人工智能作品獲得版權,使人類作品與人工智能創作的作品總量相對平衡,避免版權市場出現“機器壟斷”。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出版物中有大量獨創性較差的作品,版權登記制度也能從海量AI出版物中挑選出精英作品。如微軟“小冰”共創造了7萬余首現代詩,有139首收錄進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比例僅有0.2%。而這種選擇也能促進人工智能創作的進一步發展。此外,經過登記確權的人工智能作品,經過合法授權,人類也可以在人工智能作品的基礎上進行再度演繹創作,創作出具有更高水準的作品,最終促進文學藝術市場的整體繁榮。
注釋:
① Register of Copyrights.68thAnnualReportofTheRegisterofCopyrights,1966:4.
② U.S Copyright Office.CompendiumofCopyrightOfficePractice,1973,Item2.8.3.
③ Washington,DC.FinalReportoftheNationalCommissiononNewTechnologicalUsesofCopyrightedWorks.July 31,1978.
④ Copyright Law Review Committee.DraftReportonComputerSoftwareProtection,Office of Legal Information and Publishing,Attorney - General’s Department,1993.
⑤ Australian Copyright Council,ResponsetotheCopyrightLawReviewCommittee’sDraftReportonComputerSoftware,1993.
⑥ Copyright Law Review Committee,ComputerSoftwareProtection,Office of Legal Information and Publishing,Attorney - General's Department,1995.
⑦ U.S Congress.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n Age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April 1986.
⑧ 《知的財產推進計劃2016》,http://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kettei/chizaikeikaku20160509.pdf.訪問時間:2018年1月28日。
⑨ 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著作權認定》,《知識產權》,2017年第3期。
⑩ 吳漢東:《人工智能時代的制度安排與法律規制》,《法律科學》,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