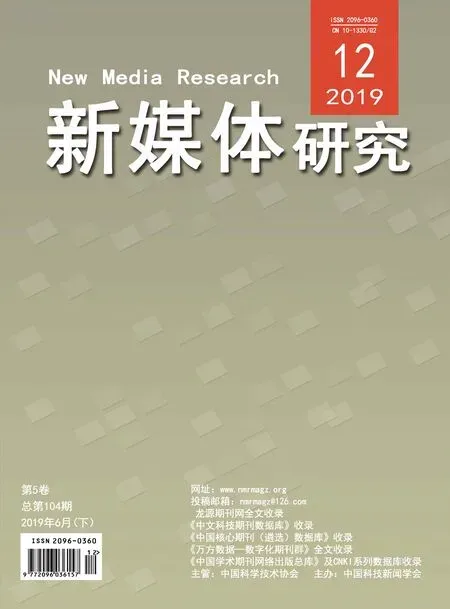表演與互動:網絡運動場上的人際傳播
岳山 李夢婷
摘 要 以微信為代表的新媒體平臺已經成為當代人際交往的主要陣地,微信朋友圈因此成為個體展現自我、了解他人的渠道。文章以微信朋友圈中出現的“運動打卡”現象為研究對象,基于歐文·戈夫曼的“擬劇理論”,通過文本分析和深度訪談,分析“運動打卡”現象中人際傳播的特點及其產生的動力機制。
關鍵詞 人際傳播;微信朋友圈;運動打卡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8)12-0008-02
隨著互聯網融入個體生活,人類社會迎來了馬克·波斯特所言之第二媒介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從現實轉向虛擬,網絡因此成為人們表演與呈現的另一交往空間。莎士比亞在《皆大歡喜》中說,“整個世界是一座舞臺,所有男女不過是舞臺上的演員”,社會情境中的人類行為總是有表演的成分,即使我們相信自己是最本能和最真誠地對他人進行反應。截至2017年9月,微信日平均登錄用戶達7億多人①,除了社交功能,微信朋友圈也成為網民交流交往、發布和獲取信息的公共空間,一般來說,朋友圈發布的內容主要包括休閑旅游、日常生活、心得感悟等,不知何時起,“打卡”尤其是運動類打卡實踐也成了微信用戶在朋友圈中熱衷分享的內容,本文重點分析朋友圈運動打卡實踐的傳播過程,并從戈夫曼的“擬劇理論”視角出發,對打卡行為的動因進行分析。
1 微信朋友圈的運動打卡實踐
1.1 運動打卡實踐的特征
1)以展示運動成果、側面展示運動行為為主要內容。前者指利用App將運動里程、配速等信息的截圖轉發到朋友圈然后附上文字,如好友H于2018年4月24日發布的“來自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打卡d4”,4月25日發布“路徑圖什么鬼……d5”等。后者指直接發布純文字內容或發布自拍、運動場景等圖片側面表現自己的運動事實。
2)以圖片、文字為表現形式。與現實生活中的打卡方式不同,媒介社會的新技術為話語提供了多元的表達方式,所謂朋友圈的“運動打卡”,指的是用戶連續多日在朋友圈中以圖片、文字、超鏈接或短視頻等多種形式發布自己的運動實踐的
行為。
3)以自發性發布為主。縱觀微信朋友圈發布的運動打卡內容,除了部分是由于用戶使用第三方軟件附加的營銷策略進行的打卡,大部分的用戶都是遵從個人意愿的自主發布。從管理學來看,打卡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行為,是企事業單位的管理者為了強化職工的組織紀律性,記錄員工的出勤情況從而維護正常工作秩序制定的一種考勤方式,具體來說就是工作人員上下班時把考勤卡放在磁卡機上記錄下到達和離開單位的時間叫打卡。為何現實中對人產生束縛的強制行為在朋友圈這種虛擬社群中頻繁、廣泛的出現,如上文所說,人類社會處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第二媒介時代,這個時代的顯著特征就是對擬仿文化的構建,媒介介入文化改變了虛擬與現實指稱性的同一性,以至于被介入的事物連假裝未受影響都不可能,微信用戶在運動后的自發打卡也可以看成是在虛擬現實中自發的對自己進行約束的過程。
1.2 運動打卡實踐中的人際傳播
當網絡介入個人生活,最早的承載形態就是人際傳播,即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微信的強社交功能給用戶提供了可供一對一交流的途徑,朋友圈的功能如同現實中的團體組織,給用戶提供了可供交往的虛擬社群,社群中的傳播主體就是用戶個人。第二媒介時代的主體構建是通過互動性這一機制發生的,用戶對網絡的衷情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對信息的獲取,而是立即就能進入另外一大批人正在形成的交往關系[1],個人在朋友圈發布運動打卡內容,在此過程中通過點贊、評論與回復的方式與他人形成互動。
互聯網和虛擬現實打開了新型互動性的可能,個人把自己的身份簡化并編碼為顯示屏上的文字對他們身份進行解碼,點開別人的朋友圈就像打開他人身份的文件包,打卡的實踐者與觀察者在朋友圈這個特有的虛擬社群中的互動實際上就是編碼與解碼的過程,由于虛擬社群被當作一般社群看待,故而它們衍生出一些似真性,因此用戶把網絡空間中的交流經驗當作具體化了的社交互動加以體驗,一個社群之所以對其成員具有意義,是因為他們認為該社群中的交流既有意義又很重要。
2 網絡空間中個體的表演與表達
2.1 基于訪談基礎上的事實呈現
筆者對參與運動打卡實踐的三位朋友圈好友H、D、Y進行了訪談,在發布此類內容的動因問題上,在排除運動App營銷等非自愿轉發的原因之后,將三人的回答整理如下:
H:“想通過打卡的方式接受朋友圈朋友的監督,就像是對他們的承諾一樣使自己更有動力去堅持運動。”
D:“打卡是發給自己看的,表明這件事對自己非常重要,鼓勵自己認真執行。”
Y:“打卡可以培養一種我的自律、堅持的習慣。”
2.2 基于“擬劇理論”的自我呈現
作為符號互動理論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歐文·戈夫曼尤其關注人與人之間的符號互動,他認為人際傳播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人們利用符號進行自我表演的過程,由此產生了“擬劇理論”,理論關注的重點是日常生活中人們如何運用符號預先設計或展示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即如何利用符號進行表演并取得良好效果[2]。根據他的觀點,真誠固然是人類美德,但是人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在為贏得別人的認可、喝彩進行表演。從這個角度看,朋友圈的運動打卡實踐何嘗不是一種獲得他人認可的表演,那么這些實踐者根據什么來表演?為什么而表演?
陳力丹認為,人際傳播出于三種需求,首先是情感需求,包括愛、敬仰、恨、渴望等;第二種是歸屬需求,希望通過與他人交往建立某種聯系,獲得“我們”的心理安全感;第三種是控制需求,每個人在不同的問題上或多或少都有影響(關注或支配)他人的需求[3]。無論是在現實還是在虛擬的人際交往中,但凡個人與他人產生聯系就不得不考慮他人對自己的印象,正是這些印象構成了這個人的真實的社會存在,人際互動中,人們不管自己的具體目標以及達到目標的動機是什么,總是熱衷于控制他人的行為和他人對自己的反應。從朋友圈的運動打卡實踐來看,這種控制是通過運用各種符號展現自己堅持不懈的運動事實,從而在他人心中塑造自己的健康積極、自律堅持的形象。
2.3 基于他人在場的社會表現
根據上文來看,無論是接受他人監督還是承諾自我,運動打卡的實踐者將運動事實展現到網絡公共空間,都是企圖通過一種他人在場的方式促進自己達到既定目標,這也可以看成是一種尋找社會認同的過程,社會心理學家拉塔尼認為,“因受到他人在場和他人行為的影響,個人在心里狀態和主觀感受、動機和情緒、認知和信念、價值和行為等方面會發生改變,他人在場和他人的行為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暗示的或想象的”[4]。
個人的自我覺知讓人們注意到自己的實際狀態和期望狀態之間存在差距,一般來說,個人表現的提升不是來自于驅力,而是來自于自我評價的過程,當自我被當作他人關注的客體時,個體會以更加積極的狀態進行表現,并根據他人對自己的反饋進行行為調整,朋友圈中他人對發布者運動行為的點贊、評論對發布者來說是一種社會贊許性的表現,從而也更加鼓勵他們繼續堅持運動打卡實踐。
3 結語和思考
本文以戈夫曼的“擬劇理論”視角對微信朋友圈發布的運動打卡類內容進行分析,探討在人際傳播中人們不愿提及和承認的問題,即人際交往可能只是個體對他人的虛假的表演。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實踐活動只有符合社會公認的道德標準、行為規范、價值準則時才能得到觀眾的認可,這套社會準則挪用到虛擬社群中也同樣適用,因此,人們交往中表演的意義除了獲得認同外,還具有對自己內心的反叛、沖動等不安因素進行約束的作用。
注釋
①數據來源于2017年微信團隊在微信公開課上公布的微信數據報告。
參考文獻
[1]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M].范靜曄,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44-45.
[2]芮必峰.人際傳播:表演的藝術——歐文·戈夫曼的傳播思想[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4):464.
[3]陳力丹.試論人際傳播[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10):191.
[4]Michael A·Hogg,Dominic Abrams.社會認同過程[M].高明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