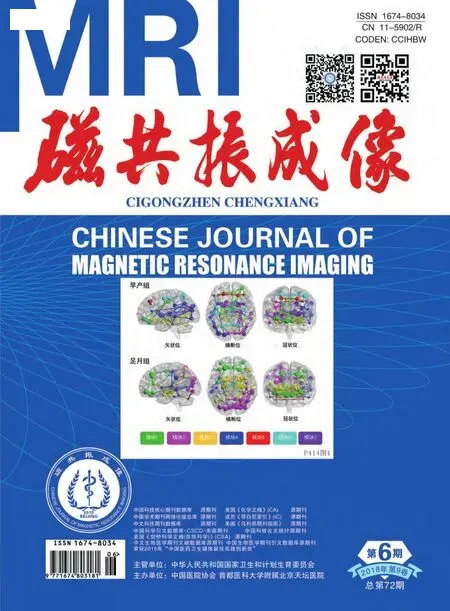急性腦梗死磁共振擴散加權成像與TOAST分型、傳統危險因素的關系探討
耿文,姜亮,陳慧鈾,許權,殷信道*,周俊山,張穎冬
作者單位:1.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南京醫院(南京市第一醫院)醫學影像科,南京 210006 2.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南京醫院(南京市第一醫院)神經內科,南京 210006
腦血管病具有高致死、致殘率及高復發率[1],其中80%為缺血性腦卒中[2]。急性腦卒中的病因對其治療及預后具有較大的影響,急性腦梗死發病機制不同,其臨床治療方法也不同[3],因此,及時準確地判斷急性腦梗死的發病機制很有必要。TOAST分型標準簡單明確,評價者間一致性高、可靠性強,是目前國際上較為成熟的腦梗死分類方法,其將急性腦梗死患者分為5個亞型:大動脈粥樣硬化型(large artery atherosclerosis,LAA)、心源性栓塞型(cardioembolism,CE)、小動脈閉塞型(small artery occlusion,SAO)、不明原因型(undetermined etiology,UND)和其他原因型(other determined etiology,OC),其側重于缺血性腦卒中的病因學分型,對腦梗死的發病機制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是評價急性腦梗死最敏感的方法,其在指導急性缺血性腦梗死早期診療中具有重要的作用[4]。已有較多學者對急性腦梗死患者DWI病因分型及TOAST分型與傳統危險因素的關系進行了報道[5-10],而未對DWI表現與傳統危險因素的關系進行探討。本文旨在全面探討急性腦梗死患者的DWI影像學特點與TOAST分型、傳統危險因素的關系,提高臨床診療的針對性,降低患者的病死率和致殘率。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2012年5月至2016年3月在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南京醫院神經內科住院的急性腦卒中患者942例,其中男性603例,女性339例,平均年齡(67.46±11.63)歲。納入標準:(1)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斷符合《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斷指南》[11]診斷標準;(2)腦CT無早期大面積腦梗死影像學改變;(3)入院24 h內行磁共振檢查。排除及剔除標準:存在體內金屬支架等MRI檢查禁忌證或拒絕或未能按要求接受多模磁共振檢查者。本研究符合倫理學要求,所有患者于檢查前均已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影像學檢查
所有急性腦梗死患者CT檢查排除出血后立刻行MRI檢查,采用3.0 T MR全身成像設備(Philips,Achieva Tx 3.0 T),掃描基線與前、后聯合平行。掃描序列包括:T1WI、T2WI、液體衰減反轉恢復(fluid-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FLAIR)軸位、T1WI矢狀位掃描和DWI軸位掃描。掃描參數如下:T1WI:TR=250 ms,TE=2.3 ms;T2WI:TR=3000 ms,TE=80 ms;FLAIR:TR=11000 ms,TE=125 ms,TI=2800 ms;DWI:TR=2245 ms,TE=90 ms,FOV 210×210×118,矩陣140×109,層厚6 mm,層間距0.6 mm,bmax=1000 s/mm2。
1.3 DWI影像學分型[5]及圖像分析
根據DWI序列將病灶分為單發病灶和多發病灶,單發病灶分為皮質梗死(A組)、皮質-皮質下梗死(B組)、大穿通支梗死(病灶直徑>20 mm)(C組)、小穿通支梗死(病灶直徑≤20 mm)(D組);多發病灶分為單側前循環多發梗死(E組)、雙側前循環多發梗死(F組)、后循環多發梗死(G組)、前-后循環多發梗死(H組)。在DWI圖像上,根據病灶高信號所處區域進行DWI影像學分型并測量病灶直徑大小,單發病灶選取病灶最大層面測量最大徑,多發病灶分別選取最大病灶最大層面測量最大徑及最小病灶最大層面測量最大徑,詳見圖1。DWI影像學分型及測量均由2名具有5年以上工作經驗的神經放射診斷醫師單獨進行分型,對存在爭議的結果,經2名醫師討論后達成統一意見,測量結果取兩者的平均值。
1.4 TOAST分型
TOAST共分為5型[12]:LAA、CE、SAO、OC、UND。各項檢查均在診治過程中逐步完善,TOAST分型由2名具有5年以上工作經驗的神經內科專業副主任醫師根據患者臨床表現及輔助檢查評定,對存在爭議的結果經2名醫師討論后達成統一意見。
1.5 一般臨床資料收集
采集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及完善常規檢查,記錄患者年齡、性別、吸煙及飲酒史、入院NIHSS評分、高血壓史(收縮壓及舒張壓)、同型半胱氨酸及血脂異常史、糖尿病史、有無冠心病、心肌梗死、房顫及心臟瓣膜病等。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9.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雙向有序的R×C列聯表表示,采用R×C列表χ2檢驗,然后進一步行四格表Pearsonχ2或Fisher精確概率檢驗,對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進行組內兩兩比較。一般臨床資料中,連續變量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非連續變量采用例(%)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TOAST分型結果
本研究以LAA型所占比例最高(462例,49.04%),其次為SAO(372例,39.49%)、CE (58例,6.16%)、UND (49例,5.20%)、OC (1例,0.11%),這1例患者為血液病患者,無其他動脈粥樣硬化、房顫等異常表現。
2.2 DWI表現與TOAST分型關系比較

圖1 A、B為多發腦梗死患者(同一患者)。A:最大病灶最大層面最大徑的測量,B:最小病灶最大層面最大徑的測量;C:為單發腦梗死患者(另一患者),單發病灶最大層面最大徑的測量Fig. 1 A and B are multiple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the same patient). A: Measurement of maximum lesion maximum diameter of the largest lesion, B: The measurement of the maximum dimension of the maximum level of the smallest lesion; C: Single cerebral infarction (another patient), maximum lesion diameter measurement of single lesion.

表1 所有患者DWI表現與TOAST分型關系比較Tab.1 Comparison of DWI expression and TOAST classification in all patients
942例患者中,DWI單發病灶434例(46.07%),多發病灶508例(53.93%),DWI影像學分型與TOAST分型相關(χ2=397.785,P=0.000)。皮質-皮質下梗死、大的穿通支梗死、單側前循環梗死、前-后循環梗死多與LAA型有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17.205,P=0.000;χ2=171.172,P=0.000;χ2=53.487,P=0.000;χ2=113.830,P=0.000);小的穿通支梗死多與SAO型有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8.112,P=0.000)。此外,部分小穿通支梗死與LAA型有關(χ2=5.237,P=0.030);部分皮質-皮質下梗死、前-后循環梗死與CE型有關(χ2=3.526,P=0.039;χ2=7.676,P=0.008);部分大穿通支梗死、前-后循環梗死與SAO有關(χ2=12.644,P=0.002;χ2=11.010,P=0.003)。皮質梗死、雙側前循環梗死及后循環梗死與TOAST分型無明顯相關性(P>0.05)(表1)。
2.3 DWI分型與傳統危險因素的關系比較
在942例急性腦梗死DWI分型中,年齡、NIHSS評分、冠心病、房顫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皮質-皮質下組的平均年齡最大,為(71.25±12.04)歲,NIHSS評分最高,為6.18±5.40;冠心病、房顫所占比例最高,分別為23.53%、37.25%(詳見表2、圖2)。對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進行組內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組內比較結果詳見表3~6。
2.4 DWI不同分型病灶大小比較

圖2 不同DWI分型年齡、NIHSS評分、冠心病、房顫的均值散點圖Fig. 2 The mean scatter diagram of age, NIHSS sco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trial fibrillation with different DWI type.

表2 DWI分型與傳統危險因素的關系比較Tab.2 Comparis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WI type and traditional risk factors

續表2 DWI分型與傳統危險因素的關系比較Tab.2 (Cont) Comparis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WI type and traditional risk factors
942例患者中,DWI單發病灶434例,平均直徑為(20.75±19.81) mm,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0),其中前-后循環急性腦梗死的平均直徑最大,為(56.20±65.27) mm;多發病灶508例,平均最大直徑為(33.39±26.92) mm,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0),其中前-后循環急性腦梗死的平均最大直徑最大,為(43.57±32.33) mm;平均最小直徑為(5.20±3.27) mm,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513)(表7)。

表3 DWI分型各組間年齡兩兩比較Tab.3 The comparisons of age with different DWI type

表4 DWI分型各組間NIHSS評分兩兩比較Tab.4 The comparisons of NIHSS with different DWI type

表7 不同DWI分型急性腦梗死病灶直徑比較(mm)Tab.7 Comparis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DWI type and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lesion diameter (mm)
3 討論
已有較多研究顯示影像學與病因學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5-7],DWI可從細胞水平早期檢測水分子運動受限的程度,能發現超急性期的病灶,并區分急性病灶和陳舊病灶,95%以上的病灶可由DWI序列發現[13],且部位和范圍較準確,其靈敏度和特異度可達95%~100%。Lee等[14]研究結果顯示,應用DWI可使病因分類診斷的符合率從48%提高到80%。因此,盡早行DWI檢查,可提高急性腦梗死分型的準確度,為臨床治療提供指導。
本研究結果顯示,DWI影像學分型與TOAST分型相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皮質-皮質下梗死、大的穿通支梗死、單側前循環梗死、前-后循環梗死多與LAA型有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LAA的發病機制有動脈到動脈栓塞、低灌注/栓子清除率下降及載體動脈斑塊堵塞穿支開口等。皮質-皮質下梗死的主要原因為腦主要動脈血流障礙引起的灌注不足所致。本研究結果顯示,皮質-皮質下梗死主要與LAA型有關,與王新等[5]、王寶軍等[15]的結果相似,大動脈病變所致重度狹窄或完全閉塞的患者,往往代償能力有限[5],而Kang等[6]、Wessels等[7]認為皮質-皮質下梗死的病因多為CE型,本研究顯示部分皮質-皮質下梗死也與CE型有關,造成該結果差異的可能原因為樣本量大小、病例來源不同。本研究結果還顯示,單側前循環梗死、前-后循環梗死多與LAA型有關,這與劉又榕等[16]的研究結果相似,脫落后的大動脈粥樣硬化斑塊,易隨血流堵塞大腦前循環的各個血管,常導致前循環梗死。大穿通支梗死多與LAA型有關,目前,影像學發現大部分大穿通支梗死伴載體動脈的粥樣硬化或狹窄≥50%[15]。小的穿通支梗死多與SAO型有關,與國內外報道結果一致[8-9]。本研究結果還顯示,部分皮質-皮質下梗死、前-后循環梗死還與CE型有關,心房顫動是心源性梗死的高度危險因素,在所有腦卒中患者中約16%的病因與房顫有關。心房顫動等心源性病變易導致栓子形成,而栓子易破碎脫落導致遠處器官的多發病灶,形成腦梗死。本研究結果顯示,皮質梗死、雙側前循環梗死及后循環梗死與TOAST分型無明顯相關性。
本研究通過對DWI分型與傳統危險因素的關系比較發現,在942例急性腦梗死DWI分型中,年齡、NIHSS評分、冠心病、房顫組間差異顯著。其中,皮質-皮質下急性腦梗死的平均年齡最大;NIHSS評分最高,Ay等[17]認為年齡在腦組織缺血性改變中占有重要的作用,隨著年齡增加,缺血性腦組織會轉變成腦梗死,腦梗死體積與年齡之間具有相關性,每增加1歲,將會有額外的0.65%腦組織轉變為梗死。此外,皮質-皮質下急性腦梗死患者的冠心病、房顫所占比例最高,這與前面所述結果皮質-皮質下急性腦梗死與LAA、CE有關相一致。此外,雙側前循環急性腦梗死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所占比例最高,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是動脈粥樣硬化的高危因素[18-19],可能機制有血管內皮細胞的損傷;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及甘油三酯的代謝異常;氧化應激;激活血小板、促進血管平滑肌細胞增殖等。本研究還對942例患者病灶最大直徑進行了測量,急性腦梗死的梗死體積與最終預后具有較大相關性[20],本研究結果顯示434例單發病灶的平均直徑為(20.75±19.81) mm,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508例多發病灶的平均最大直徑為(33.39±26.92) mm,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其中,無論是單發病灶還是多發病灶,前-后循環急性腦梗死的平均直徑均較其他組大。Alqahtani等[21]認為梗死灶直徑較大時往往存在較大的灌注異常,而灌注異常的出現往往較沒有灌注異常的患者預后不好,由此可見,病灶直徑大小可能與預后密切相關,筆者將在后續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DWI影像學分型與急性腦梗死患者的TOAST分型有關,年齡、NIHSS評分、冠心病、房顫等傳統危險因素對DWI影像學分型具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急性腦梗死患者早期行DWI影像學檢查,結合臨床傳統危險因素,可以指導臨床診治,降低致殘率和致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