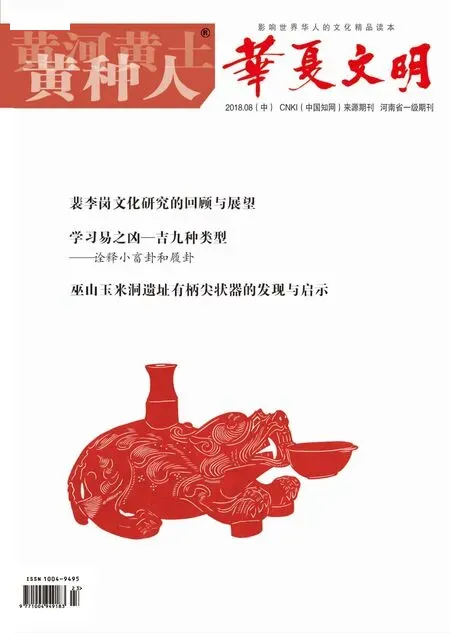巫山玉米洞遺址有柄尖狀器的發現與啟示
□賀存定
一、引言
有柄尖狀器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代表性狩獵工具或武器,以能夠遠距離投擲并造成致命創傷而實現安全狩獵著稱,被認為與現代的矛頭或標槍頭具有淵源關系,是一種非常特殊且具有文化指示意義的工具類型。這類工具的英文名稱主要有projectile point、ttanged point和stemmed point,中文名稱主要有有柄尖刃(狀)器、帶鋌石鏃、投擲尖狀器、矛形器等,本文暫以更具廣義特征的“有柄尖狀器”統稱。有柄尖狀器主要由石葉或石片制成,原料和類型均較多樣,整體形態較狹長,一端呈尖狀形態,另一端具有修柄處理,可捆綁裝柄用于手執或投擲使用。此類工具為復合工具的一種早期形態,但一般認為與石鏃類似的遠射工具在形制功能和加工技術上明顯不同[1]。經模擬實驗和民族學對比研究認為,這類工具在大型狩獵或戰爭沖突時可作為投擊、插刺的鏢頭或矛頭使用[2][3],但也有學者認為它是兼具投殺、切割、刮削等多功能的復合工具[4]。目前,從世界范圍看,有柄尖狀器主要分布于非洲北部、黎凡特、歐洲、朝鮮半島、俄羅斯遠東和日本地區,印度、中國、俄羅斯阿爾泰地區僅有零星發現且有些尚未得到普遍認可。其中除北非的Aterian Culture遺址(距今14.5萬年—4萬年之間)[5]、印度的Jwalapuran遺址(距今74萬年)[6]發現的有柄尖狀器時代可追溯至舊石器時代中期,其余幾乎全部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另外,雖然有柄尖狀器在石葉技術出現之前已經存在,但有柄尖狀器盛行的時間與石葉技術大致相同,甚至有學者以石葉或長石片制作、背部有鮮明棱脊而定義出更為狹義的有柄尖狀器[7]。因此,在缺失石葉技術的中國南方發現時代可能早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有柄尖狀器,其學術價值和啟示意義非凡。本文主要對巫山玉米洞遺址2013年出土的有柄尖狀器進行類型、加工技術分析及相關問題探討。
二、有柄尖狀器的發現
到目前為止,與中國鄰近的朝鮮半島、日本、俄羅斯遠東地區不斷發現有柄尖狀器,而中國卻鮮見這類工具的報道,但一些跡象表明,中國發現有柄尖狀器的可能性在增加。一方面,隨著工作的開展,中國舊石器考古新發現不斷涌現,尤其在北方地區發現越來越多的含石葉遺址,在客觀條件上為發現有柄尖狀器增加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已有學者開始關注這種工具類型并進行了相關研究,尤其是在原有的材料中重新識讀這種工具類型,在主觀條件上推動這類工具的發現和認知。劉楊報道了鄂爾多斯烏蘭木倫遺址2012年發掘出土的一件“帶鋌石鏃”,認為其與Aterian Culture的tanged point非常相似,加工和修理技術相同,極有可能是文化傳播與交流的結果,他還針對周口店第15地點出土的一件“尖狀器”重新進行審視,認為這件尖狀器底部的凹缺是有意打制的,是為了捆綁而進行的修柄[8]。崔哲慜也在周口店第1地點重新識讀了一件“長尖石錐”,認為這件石錐的石料與形態和朝鮮半島出土的有柄尖狀器極為相似[9]。 (圖 1)
玉米洞遺址有柄尖狀器的識別也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該遺址位于重慶巫山縣廟宇鎮,2012年被確認為舊石器遺址,以其時代跨度大而連續的地層堆積和特殊的石器工業面貌而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在2013年出土的石制品中,有一件尖狀器的柄部有專門的修柄處理,捆綁意圖明顯,尖端有殘損,當時推測應是一件捆綁裝柄的復合工具。據此,將這件工具特殊對待,單列一個類型并命名為“矛形器”。后來在玉米洞遺址的研究過程中發現,該遺址的工具中其實不乏一些特殊的修理方式,如把手修理、修柄、有意截斷等,但由于數量較少,在起初的研究中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然而,由于這件矛形器的出現和對有柄尖狀器的興趣使得我們有意識地注意類似器物的觀察和研究。后來經過仔細辨別和分析,在工具中又識別出18件可能具有裝柄意圖的有尖類工具,我們暫且將這類工具都稱為有柄尖狀器,它在形制和加工技術上均不同于以石葉或長石片為毛坯制作的狹義有柄尖狀器,時代上可能也并不局限于舊石器時代晚期。這類工具來自玉米洞遺址2013年發掘的不同文化層 (表1),其中第2層數量最多,第7層次之,其他層零星發現,在時代上可能存在著歷時性發展或傳承。
三、類型及加工技術
復合工具的裝柄方式多樣,根據工具形制的不同可能會采用不同的裝柄和捆綁方式,有柄尖狀器也不例外。據奧德爾對屬于中石器時代弗里辛文化(Friesian)的貝赫姆湖遺址(Bergumermeer)有柄石鏃(有柄尖狀器)的裝柄復原情況(圖2)[10],我們將玉米洞遺址出土的可能具有裝柄意圖的有尖類工具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柄部修理的修柄型有柄尖狀器,這種器形是在器身底端修理出兩個較為對稱的凹缺或修理出兩側收縮的鋌;另一種是截斷型有柄尖狀器,這種器形底端有意截斷形成類似柄部的收窄效果,截斷方向與工具縱軸斜交。顯然修柄型有柄尖狀器與截斷型有柄尖狀器在綁柄方式上明顯不同,分別屬于嵌入式和倚靠式[11],截斷型有柄尖狀器需要對柄桿做更多的改造來適應和貼合截斷型有柄尖狀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裝柄方式對有柄尖狀器進行分類是基于可能性使用方式的復原所做出的推定,這種推定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證實, 而且本文所列有柄尖狀器也并非一定特指裝柄的復合工具,有些有柄尖狀器柄部特殊處理的作用也可能屬于把手修理的范疇。現將部分較典型的有柄尖狀器描述如下:

圖1 國內發現的有柄尖狀器(修改自參考文獻[8][9])

表1 玉米洞遺址出土有柄尖狀器情況

圖2 貝赫姆湖遺址不同類別的石鏃(有柄尖狀器)裝柄復原圖(據Odell,1978)
13YMDT8 ② ∶375,修柄型有柄尖狀器。長12.27厘米,寬7.8厘米,厚2.32厘米,重241.4克。出自第2層,出土深度87厘米。原型毛坯為石灰巖石片,器形較為規整。兩側邊錯向加工夾成一尖角,尖部殘損;底端兩側有深而對稱的大片疤,形成捆綁裝柄的凹缺型鋌部。(圖3∶9)。
13YMDT8②∶117,修柄型有柄尖狀器。 長7.95厘米,寬5.95厘米,厚1.76厘米,重65.84克。出自第2層,出土深度30厘米。原型毛坯為石灰巖石片,整體形態略呈三角形,在毛坯的邊緣加工,形成兩個修理尖,尖角分別為 60°、80°,底端對向加工,形成收縮明顯的鋌部。 (圖 3∶4)
13YMDT6②∶190,截斷型有柄尖狀器。長11.8厘米,寬7.69厘米,厚2.31厘米,重229.2克。出自第2層,出土深度67厘米。以石灰巖石片為毛坯,形狀略呈矛頭形,沿毛坯兩薄銳邊均勻連續加工形成圓凸刃,刃角65°~75°;底端斜向截斷,斷口不齊整,與長邊形成鋌狀收窄效果。 (圖 4∶6)

圖3 修柄型有柄尖狀器
13YMDT6②∶50,修柄型有柄尖狀器。長33.7厘米,寬13.3厘米,厚7.53厘米,重超過2000克。出自第2層,出土深度43厘米。以石灰巖塊狀毛坯加工,正反兩面各有一條縱脊;沿兩狹長邊加工形成一尖,尖部殘斷。底端呈三棱狀,一側為天然肩部稍作修理,一側加工修整成溜肩,形成兩側明顯收縮的鋌。(圖3:1)
13YMDT7⑤∶767,截斷型有柄尖狀器。長12.46厘米,寬7.6厘米,厚2.69厘米,重262.91克。出自第5層,出土深度260厘米。以具有平行節理面的石灰巖片狀毛坯加工,一面平坦,一面凸起,兩邊單向加工形成較尖銳的尖角,尖角殘斷,修疤連續。底端斜向截斷,斷口與側邊形成長尖狀柄部,斷口較齊整。 (圖 4∶9)
13YMDT5⑦∶508,修柄型有柄尖狀器。長10.49厘米,寬8.59厘米,厚2.79厘米,重191.95克。出自第7層,出土深度302厘米。以石灰巖矛頭形石片為毛坯,形制大體對稱。兩側對向加工形成一短尖,尖角52°。器身中底端有兩個較深凹且均勻的對稱片疤,底端亦有單向連續修疤形成的刃緣,以尖部為功能單元可作為修柄尖狀器,以底端刃緣為功能單元也可視為綁柄的鏟形器。 (圖 3∶7)
13YMDT6⑩∶1048,截斷型有柄尖狀器。長15.19厘米,寬 9.12厘米,厚 5.89厘米,重702.76克。出自第10層,出土深度338厘米。以石灰巖石片為毛坯,石片遠端與相鄰的側邊加工成一鈍尖,尖部有多層殘損疤,石片遠端中部也有一個凹缺。底端斜向截斷,斷口與石片遠端形成較狹長柄部,柄部底端有修理。 (圖 4∶7)
13YMDT611∶1404,截斷型有柄尖狀器。長14.87厘米,寬 6.91厘米,厚 3.64厘米,重564.33克。出自第11層,出土深度379厘米。石灰巖片狀毛坯,整體形狀呈三角形,兩面均較平坦;一長邊和一短邊對向加工成一尖,尖部殘損;底部斜向截斷,斷口與長邊形成較狹長的柄部,斷口也有連續而淺平的大修疤。 (圖 4∶4)
崔哲慜等以操作鏈理論對朝鮮半島考古發現以石葉為毛坯加工狹義有柄尖狀器的制作過程及技術進行了探討,認為有柄尖狀器主要經歷原料采備→打制石葉→選擇石葉并加工修理→使用殘損→廢棄再利用等幾個過程。有柄尖狀器的加工修理建立在選取適合的石葉基礎上,石葉選取得當,加工修理則顯得較為簡單,主要分為單側或兩側修鋌和刃部修理,有時選擇尖銳石葉為毛坯,只對柄部簡單修整,刃部維持原狀[12]。通過類型及加工技術的觀察研究,玉米洞遺址并沒有典型的石葉技術,有柄尖狀器在加工程序上顯然與朝鮮半島考古的發現截然不同,但在加工理念上卻有相似性。玉米洞遺址的原料形態較為特殊,有柄尖狀器是以石片、片狀毛坯甚至個別塊狀毛坯加工而成,在加工程序上至少可分為兩種:一是原料采備→剝片→選取石片并加工修理→使用殘損→廢棄再利用;二是適合毛坯選取→加工修理→使用殘損→廢棄再利用。由于部分片狀或塊狀毛坯并不具備石葉的形態和薄銳側緣,玉米洞遺址的有柄尖狀器需對毛坯進行更為精細的選擇,充分利用毛坯自身優勢稍作加工。對柄部的處理也是因材而異,除加工對稱的凹槽和兩側收窄的修理鋌外,還采用有意截斷的方式形成單側加工修鋌的效果,反映了簡單實用而又靈活多樣的應對技術策略。

圖4 截斷型有柄尖狀器
四、時代源流及啟示意義
狹義有柄尖狀器的時代一般認為主要集中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與石葉技術伴存。即使廣義的有柄尖狀器,目前也只有少數地區可追溯至舊石器時代中期。玉米洞遺址的有柄尖狀器來自第2~12層的大部分層位,其時代跨度大,延續時間長。據鈾系法和光釋光測年結果綜合來看,第3層時代應為距今8萬年左右,第2層地層較厚,時代應介于距今0.8萬年-8萬年之間,而第4層及以下地層時代可能接近或超過距今20萬年[13]。 因此,測年結果準確的話,玉米洞遺址的有柄尖狀器的時代應跨越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烏蘭木倫遺址有柄尖狀器的時代被認為距今6.5萬年~5萬年[14],周口店第15地點有柄尖狀器的時代距今14萬年—11萬年[15],而周口店第1地點有柄尖狀器的時代則可能超過距今40萬年[16]。相較而言,玉米洞遺址有柄尖狀器的時代顯得并不那么突兀。從溯源視角來看,玉米洞遺址的有柄尖狀器應源于舊石器時代早期尖狀器的演變,屬于尖狀器的特殊形式,是在尖狀器把手修理基礎上的進一步分化,表現了時代和技術的進步。有柄尖狀器和尖狀器雖然在使用方式上分道揚鑣,但在部分功能上仍存在重疊,一些有柄尖狀器可能仍隱匿于尖狀器中而未被識別。張森水先生也曾認為下川發現的尖底形鏃(有柄尖狀器)與同時期的尖狀器難以區分[17],二者應具有淵源關系。從流向來看,隨著技術的發展,有柄尖狀器的形制、功能進一步分化,與后來廣為流行的標槍頭、矛頭、石鏃等應具有演變關系,代表了復合工具發展的復雜化、專門化。玉米洞遺址的最晚地層出土有柄尖狀器的時代可能接近全新世,與新石器時代廣泛使用的石鏃、矛頭等狩獵工具已沒有時代隔閡。
狩獵是人類適應生存的最基本形式,狩獵的形式當然也因時因地而呈現多樣化。按照最佳覓食模式的觀點,大型動物以產出最大化而成為史前人類狩獵的首選,但以大型動物為代表的肉食資源屬于機會狩獵,需增加工具的效能來提高狩獵成功的概率[18]。有柄尖狀器被公認為一種狩獵工具,在技術上表現了近距離刺殺工具向遠距離投殺工具的發展[19],功能上滿足了能夠在安全距離(safe distance)內造成致命創傷(lethal wound)的要求,從而實現狩獵的安全高效。因此,有柄尖狀器被認為反映了人類較為進步的認知和行為能力,極具指示意義[20]。基于有柄尖狀器在文化上的特殊指示意義,這種工具類型通常被認為是現代人(晚期智人)行為的重要表征,這種技術也通常被認為與文化傳播和交流有關[21]。而來自玉米洞遺址第4~12層的有柄尖狀器和周口店第1地點的有柄尖狀器,時代上已然超出現代人的范疇,文化和技術來自西方的傳播交流顯然無從談起。同樣值得關注的是,玉米洞遺址還出土了數量可觀的同樣表征行為現代性的骨角牙器,其出土層位、時代與有柄尖狀器極為相近[22],這將極大地豐富我們對早期現代人及其行為能力的認知。而且,從玉米洞遺址地層堆積的連續性、文化面貌的統一性和石器技術的傳承性來看,該遺址文化面貌均指向相對獨立的發展演化,沒有發現明顯的外來人群交替和文化傳播證據。
五、結語
有柄尖狀器在北非、歐洲和朝鮮半島等地區較為流行,時代主要集中在舊石器時代中晚期,而中國則少見這類工具的發現。近年來,在烏蘭木倫、周口店第1地點和第15地點等陸續識別出廣義的有柄尖狀器,但其時代可能超出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玉米洞遺址有柄尖狀器的發現進一步證實了有柄尖狀器在中國的分布和時代的久遠。通過類型和加工技術的研究,玉米洞遺址存在修柄型和截斷型兩種有柄尖狀器,其加工技術與狹義的有柄尖狀器不同,但制作理念卻極為相近。玉米洞遺址的有柄尖狀器應源于尖狀器的發展演變,時代可能追溯至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晚段,經歷較為連續的發展,時代的下限可能延伸至全新世,最終演變為矛頭、石鏃等新石器時代典型的狩獵工具。有柄尖狀器因實現安全高效的狩獵效果而被貼上現代人行為表征的標簽,同時還具有人群交流、文化傳播的指示意義,而玉米洞遺址發現的有柄尖狀器和骨角牙器似乎并不支持其作為行為現代性和文化傳播交流的表征,這警示我們需對中國現代人行為及其文化進行重新審視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