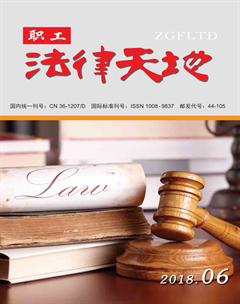淺議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摘 要:近年來,我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案件的發展聲勢迅猛,危害后果十分嚴重。因此,深入探究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演進歷程和行為特征,對于有效規制和打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演進歷程;行為特征
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演進歷程
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對資本和貨幣流動的限制十分嚴格,單位和個人并無過多閑置資金。因此,尚不具備產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的客觀環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后,市場經營活動日益活躍,經濟愈加繁榮,民眾手里的自由資產日益增多,部分公司、企業和個人的資金需求也隨之增大。礙于國家在金融領域對于不同性質企業的差別對待,大多數民營企業難以從正規渠道融入資金,被迫轉向民間借貸。此外,部分金融機構迫于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為實現利益最大化,往往不得不通過擅自提高存款利率等不正當手段吸募社會資金。資本供需之間的互動,加上不良的市場環境,客觀上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活動提供了滋生環境,隨著時間的流逝,其發展聲勢也愈加浩大。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活動產生之初,我國在金融領域的法律法規尚不完備,只能借助于條例、規定等來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進行規制,“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這一完整性概念在當時也并未產生,對于該類行為大都是通過“儲蓄存款”這一術語來表達。[1]
首次明確提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這一概念,是在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商業銀行法》第79條中,這是我國首次在法條中使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概念。
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正式納入刑事范疇,是在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第7條中,這是我國第一次以單行刑法的方式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進行刑事規制。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罪名的正式確立是在1997年《刑法》第176條中。至此,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演進歷程正式完成了從零到經濟性法律到單行刑法最終到刑法的傳導。
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行為特征
2011年最高院施行的《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從社會性、利誘性、公開性和非法性四個方面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特征進行了明確和細化,四者在司法認定中缺一不可。
(一)非法性
非法性主要是針對吸資主體的不合法而言,具體包括不具備吸收存款資格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采取非法形式吸收公眾存款的金融機構兩類。[2]不具備吸收存款資格的非法金融機構在實踐中的非法吸款行為一般較為容易認定且鮮有爭議,而針對具備吸收存款資格的銀行等金融機構是否可以認定為本罪的行為主體,則爭議較大。該類主體主要是通過不恰當提高存款利率、承諾給予其他高額回報等方式從事非法吸款活動。筆者認為,金融機構可以構成本罪的單位主體:其一,法條規定并未當然排除此類主體;其二,事實證明金融機構的非法吸款行為也會擾亂我國金融秩序,侵害相關法益;最后,若不對金融機構的非法吸款行為進行刑事規制,有礙于實現法益保護目的。
(二)公開性
公開性是指通過各種形式向社會公眾公開宣傳吸收存款的信息。《解釋》列舉了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向社會公眾公開宣傳的方式,當然,實踐中的公開宣傳方式是層出不窮的,在公共活動場所設立展臺、宣傳板或是通過熟人、公司員工之間相互介紹等方式進行宣傳也并非罕見。另外,司法實踐中針對一些并未借助任何媒介,僅僅是通過相互間口耳相傳、人人相傳等方式進行吸資的行為,若同時具備吸資人數眾多、涉案金額較大、危害后果嚴重等情形,最后都予以認定為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三)利誘性
利誘性是指非法吸款行為人承諾在一定期限內歸還本息或給予其他高額回報。針對直接以“存款”名義吸收公眾資金的行為而言,一般是承諾在一定期限內給予被害人可以預見的利息回報,所承諾的回報率往往遠高于市場平均回報率和收益率。在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中,吸款行為一般并不是直接以“存款”的名義出現,需要進行實質理解。[3]司法解釋和實踐中對此也是作出了擴大解釋,在《解釋》中就將利誘性認定為“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通常,吸款行為人還會承諾只要出資就一定會給予回報,而且是高額回報,有的甚至還可能約定保底收益。此外,并不需要投資人做出其他任何努力。注意,承諾不限于書面或口頭,只要雙方就此協商一致即可,也不必考慮承諾的真實性或是否真正兌現了承諾。
(四)社會性
社會性是指行為人向社會不特定多數群體吸收存款。對于“社會公眾”的理解,一直存有爭議,主要集中于合理界定“親友”的概念和范圍以及是否應該將單位吸收內部成員存款的行為認定為本罪。[4]因為對象是否特定具有相對性,一般是在事前依據一定標準來判斷是否能將對象特定化,但這個標準并沒有在法律上進行細化和具化,不同法院對于“社會公眾”認定標準的不一致就會導致判決結果的差別化,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不少案件類似但判決結果卻大相徑庭的情況。筆者認為,對于“親友”概念本身的確認和范圍劃分,應通過法律條文的形式來統一進行認定和明確,以便為實務部門提供操作指引。至于是否應該將單位吸收內部成員存款的行為認定為本罪,則應結合具體案情中的行為對象、行為方式、波及范圍等因素來進行認定,例如,若出現對集資規模和對象并無預設,只要有資金,不論是誰出借均予以吸收,對集資行為的輻射面事先也不加以限制、事中不作控制,在蔓延至其他人后聽之任之,不設法加以阻止等類似情形且符合其他構成要件的,可以認定為本罪,否之,則不能夠認定為本罪。
參考文獻:
[1]黃韜.刑法完不成的任務——治理非法集資刑事司法實踐的現實制度困境.中國刑事雜志,2011年第11期.
[2]彭少輝.非法集資的刑法規制與金融對策.中國刑事法雜志,2011年第2期.
[3]劉憲權.刑法嚴懲非法集資行為之反思.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
[4]劉志偉.非法集資行為的法律規制:理念檢視與路徑轉換.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作者簡介:
張貴湘,女,中央民族大學,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學。
注:中央民族大學一流大學一流學科經費資助,編號:10301-0170040601-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