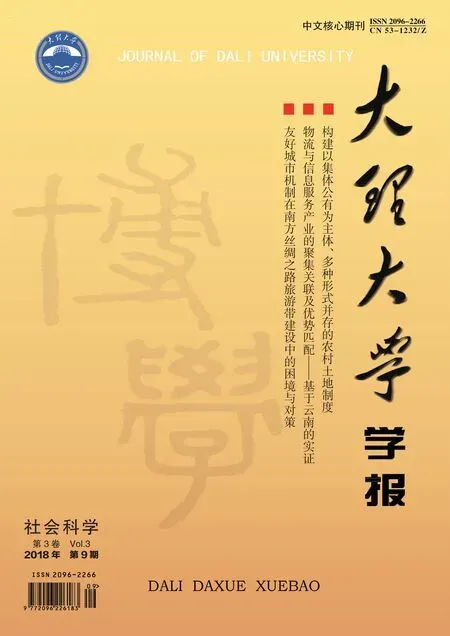《西廂記》重刻現象下的利益與話語權
田 威
(大理大學藝術學院,云南大理 671003)
以今天的常識來看,當一本書被不斷地再版重印時,它一定是一本好書或是暢銷書,更是一本給出版商帶來豐厚利潤的書。而四百年前的晚明社會,也同樣出現了這種不斷重刻同一本書的現象。
晚明刊刻的戲曲唱本、話本小說類書籍常常冠以“校注”“音釋”“批評”“評點”等字樣,甚至不惜搬上一些名人的名諱。這其中不乏假借名人博取商業利益的行為,但也有部分名人實際參與到一些書籍的“批評”“評點”中,如陳繼儒、李贄、徐渭等。當然,一部分人表現出積極參與的態度,而另一部分人則在冷眼旁觀,甚至認為是一種泛濫。時人葉盛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水東日記》中寫到:
……甚者晉王休徵、宋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至百態誣飾,作為戲劇,以為佐酒樂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為禁,士大夫不以為非;或者以為警世之為,而忍為推波助瀾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出于輕薄子一時好惡之為,如西廂記、碧云騢之類,流傳之久,遂以汎濫而莫之捄歟。〔1〕214
從葉盛的言論中可以看到他對明代大眾文化興盛的態度,而他更認為這種流傳與泛濫是因為官方沒有對“佐酒樂客”的形式加以禁止,即“官者不以為禁”。明洪武時期對于文化娛樂上的管控相當的嚴苛。為了盡快恢復社會生產,保障農業人口的充沛,嚴禁業外人員參與文化娛樂活動。同時,相關的文化娛樂活動所涉及的內容亦必須是具有教化功能,但正德以后這種禁錮逐漸廢弛。其中,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重要因素,而來自上層的喜好,甚至是帝王本身癡迷其中而致禁令廢弛是另一個因素〔2〕。
葉盛歷經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四朝〔1〕1,他所說的“官者不以為禁”的松動,大概在這段時期已經開始了。而時人陸采也曾記載了發生在天順朝的類似事情:
吳優有為南戲于京師者,門達錦衣奏其以男裝女,惑亂風俗。英宗親逮問之。優具陳勸化風俗狀。上命解縛,面令演之。一優前云,“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悅,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優于教坊。〔3〕
從陸采的記述中,天順年間應該尚存在這類的禁令,但即便是禁令尚存,當明英宗親自審問時,伶人們僅僅一句“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的話語,令英宗龍顏大悅,也就相安無事了,可見禁令雖尚存但已然松弛了。顯然,葉盛眼中的“官者不以為禁”并非明代沒有相應的文化娛樂政策,只是明初期制定的相關政策到明中期以后由于社會、經濟的變化,這些禁令不過是名存實亡。隨著政府禁令的寬松或消亡,戲曲演繹逐漸繁榮,隨之戲曲唱本的需求增大。這種變化也帶動了書籍刊刻的發展,明代的書籍刊刻是不需要任何部門審核的〔4〕,可以說,只要有充足的經費就能刊刻〔5〕。隨著明代文化相關的禁令逐漸寬松和消亡,不僅促進了明代戲曲的繁榮,也帶來了一個書籍印刷的時代。
明中期以后書籍的刊刻逐漸繁榮,到萬歷朝時期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這一時期刊刻了種類繁多的書籍并大量重刻、翻刻了各類流行、暢銷書籍。其中,以《西廂記》為例,現存就多達44種版本〔6〕1-10;此外,《牡丹亭還魂記》也刊刻了很多版本,在《吳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的“牡丹亭還魂記序”中就提到了5種不同的版本〔7〕,而實際情況應該遠不止這5種版本。在這些不斷地重刻和翻刻的背后,利益的驅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除此而外,是否還存在其他的因素呢?
一、重刻的理由
晚明時期相同的書籍被重新編定、刪減后再次刊刻,并不只出現在唱本、小說類書籍中,其他書籍也存在這類現象。
故事書,坊印本行世頗多,而善本甚鮮,惟建安虞韶日記故事以為一主楊文公、朱晦庵先生之遺意。穎考叔輟羹遺母,不失純孝,未免昭君之過;……凡矯枉害正之事,一切不取。又如楚王戊之醴酒忘設,邊孝先之書眠見嘲,……事雖反正,亦足為來者之戒,各存本類之后。近歲襄城李公重刊此書,又為易生知為幼悟,且標目卻去對偶,一以年代為先后,亦善矣。惜乎去取標目皆尚有未精純處,且不著事出某書某文,其間刪削亦不一。〔1〕131
《建安虞韶日記故事》在葉盛眼中總體上是一本有關教化的好書,襄城李公為了讓幼童、學生易知易曉進行了簡化、刪削后重新刊刻。同時,他也認為有不夠精純的地方。葉盛原本只是記錄對“日記故事”類書籍的看法。無意間,卻留下了襄城李公重刻此書的另一種想法,李公重刻此書似乎是“為易生知為幼悟”的目的,他認為孩童啟蒙的書不宜深奧,而原書卻過于深奧,所以要去繁就簡讓孩童們更容易理解。于是,他借著重新編輯刊刻的機會,將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付之于新書之中。隨著新書的流通,李公的觀點會讓更多的人看到并接受,這顯然具有借書籍的重刻發表對蒙童書籍的話語權。而反觀葉盛,他在這則故事的論述中,從原本的《建安虞韶日記故事》到襄城李公重刊都進行了一番評論,這顯然也是他對話語權的一種表達。如果說,葉盛的記載中尚存一絲話語權的痕跡。那么,現存的明版《西廂記》中卻留下了很多這類的痕跡。
現存的44種明版《西廂記》中,萬歷前期的刊本多呈現以校正、訂正、音釋等校勘為主的特征;而萬歷后期至明末以批評、批點的版本較多。蔣星煜先生認為明刊本《西廂記》有一個由“校為重點”轉移到以“論為重點”的過程〔8〕。
如萬歷戊戌年(公元1598年)陳邦泰刊刻的繼志齋本《重校北西廂記》,他重刻時保留了萬歷壬午年(公元1582年)龍洞山農刊刻《重校北西廂記》時所撰的“序”。“序”中寫到:“妄庸者率恣意點竄,半失其舊,識者恨之”。顯然,龍洞山農本認為這些擅場絕代的佳作,因其他諸本任由庸者恣意點竄而半失其舊,令原作盡失,全然沒有了佳作的風貌。同時,“序”中對于“半失其舊”還提到了另一個原因,即在不斷轉刻、重刻中出現一些錯誤與疏漏。即使“序”中認定的3種好版本顧玄緯本、徐士范本、金在衡本同樣存在“詞句增損,互有得失”的問題。面對諸版本中所出現的問題,于是,就有了“序”最后的“余園廬多睱,粗為點定,其援據稍僻者,略加詮釋,題于卷額”。這是萬歷十年版本的點校者,所看到的“半失其舊”的原因,也是他重新點校的原由。而陳邦泰在他的重刻本“凡例”中寫到:“諸本釋義淺膚訛舛,不足多據,予以用事稍僻者,而詮釋之,題于卷額,余不復贅。”〔6〕39-42顯然,繼志齋本與龍洞山農本如出一轍,重刻的目的均是要糾正其他版本詞句上的錯誤并增加釋義。
現存的明版《西廂記》中出現的詞句、注音以及釋義的錯誤,一是由于版本在轉刻、重刻時出現較多的筆誤或庸者的恣意評點;二是原劇中的唱詞、念白多為市語、謔語、方言,甚至還有金元時期的習音。類似的情形在不同版本的“凡例”中均有提到,如《繼志齋本》“凡例”中這樣寫“曲中多市語、謔語、方言,又有隱語、反語,有折白,有調侃。不善讀者率以己意妄解,或竄易舊句,今悉正之”。而在萬歷庚戌年(公元1610年)起鳳館本《元本出相北西廂記》“凡例”中同樣寫到:“奇中有市語、方言、隱語、反語,又有折白、調侃等語。要皆金元一時之習音也,似無貴于洞曉。不諳者率以己意強解,或至妄易佳句,今盡依舊本正之。”〔6〕102另,刊刻于萬歷辛亥年(公元1611年)的《重刻訂正元本批點畫意北西廂》“凡例”幾乎照抄了繼志齋本“凡例”中的這一條,僅少了“不善讀者”四字。
萬歷前期的《西廂記》點校除了普遍注重注音、釋義之外,對于劇中曲調與音律的探討,各版本亦有自己的表述。如繼志齋本“凡例”中這樣寫:
《中原音韻》有陰陽、有開合,不容混用。第八出【綿搭絮】“幽室燈清”、“幾棍疏欞”,八庚入一東;十二出“秋水無塵”,十一真入十二侵。俱屬白璧微瑕,恨無的本正之,姑仍其舊。
雜劇與南曲,各有體式,迥然不同。不知者于《西廂》賓白間效南調,增【臨江仙】、【鷓鴣天】之類。又增偶語,欲雅反俗。今從元本一洗之。〔6〕41
而萬歷庚子年(公元1600年)《新刊合并王實甫西廂記》上卷“王實父西廂記敘”中寫:
……于是,薄海內外咸歌樂之,即其傳寫豈下千百。惜乎梓行者未免于亥豕,口授者莫辨乎黃王。甚有曲是而名則非,曲非而名則是。亦或迂儒附會,妄自援引,強為臆說。因仍既久,牢不可破。故雖老于詞宗者,且將忽之,矧其它乎!其尤甚者,淮本是也。至吳本之出,號稱詳訂,自今觀之,得不補失。何也!蓋由南人不諳乎北律,風氣使之然耳。故求調于聲者,則協以和;求聲于調者,則舛以謬。然則是刻也,固可茍乎?且以一字訛病及一句,一句之訛病及一篇。姑舉其大者而正之,如以【村里迓鼓】為【節節高】,并【耍孩兒】為【白鶴子】,引【后庭花】中段入【元和令】,分【滿庭芳】一曲而為二,合【錦上花】二篇而為一,【小桃紅】則竄附【么篇】,【攪箏琶】則混增五句。〔6〕79
萬歷辛亥年《重刻訂正元本批點畫意北西廂》“序”中寫:
……且南北之人,情同而音則殊。北人之音雄闊直截,內含雅騷;南人之音優柔凄婉,難一律齊。今以南調釋北音,舍房闥態度而求以艱湥,無怪乎愈遠愈失其真也。吾鄉徐文長則不然,不艷其鋪張綺麗,而務探其神情,即景會真,宛若身處。故微辭隱語發所未發者,多得之燕趙俚諺謔浪之中,吾故謂實甫遇文長,庶幾乎千載一知音哉!〔6〕117
從這些考據辨析中,不難看到編輯校訂者的良苦用心,他們各自都希望能還一部佳作的原貌,也似乎成為了重刻《西廂記》的原由和目的。他們詬病其他版本訛誤,也極力宣揚自己所校勘的版本如何之完整正確,均稱自己是依據元本或古本來校訂、正之。重新校訂后的版本的確修正了一些訛誤,但也發表自己的觀點,彰顯了學識。而這種自我觀點的闡述,可否理解為他們的話語權呢?雖然不是很明確,但一定包含了。至于他們普遍提到的“元本”或“古本”,是否存在或又是否見過尚且不一定。在王驥德校注的萬歷甲寅年(公元1614年)刊刻的《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凡例”第一條將碧筠齋本、朱石津本定義為古本;將天池先生本、金在衡本、顧玄緯本定義為舊本;其他則定義為今本或俗本。第二條則進一步說碧筠齋本雖刊刻于嘉靖癸卯,但序言是前元舊本,而朱石津本刻于萬歷戊子,但較碧筠齋本只有一二字異同,所以此二本屬古本外,其余皆是“訛本”。同時,“凡例”最后申明:“今刻本動稱古本云云,皆呼鼠作樸,實未嘗見古本也。”〔6〕133顯然,所謂古本的稱謂很大程度上是書坊商業利益考量下的一個噱頭。當然,還存在校訂者為明自己的權威性而假借古本之名。
而在繼志齋本《重校北西廂記》“凡例”中,這種借古本或元本之名似乎更明顯。“凡例”前一條認為書中“第八出”與“第十二出”存在問題,屬于“俱屬白璧微瑕,恨無的本正之,姑仍其舊。”而后一條對于龍洞山農本《重校北西廂記》中所新增的【臨江仙】【鷓鴣天】之類欲雅反俗的內容進行刪減時,卻又言是“今從元本一洗之”。龍洞山農本中的問題,一種因“恨無的本正之而姑仍其舊”,而另一種卻能“從元本一洗之”。那么繼志齋本在校訂過程中是有元本參照呢?還是無底本正之呢?這種疑惑應該很明顯。前后矛盾的“凡例”應該不是筆誤,出現這種狀況應該有兩種可能,一是的確在校注中有元本作為參照,也的確借助元本對“欲雅反俗的內容”進行了刪減,而“白璧微瑕”的地方沒能在元本中找到參照。如果情況真是如此,那么“凡例”中應該都寫作“元本”而非“凡例”中出現的一個寫成“的本”,另一個寫成“元本”,這或許是一種筆誤;而另一種可能是在校注過程中,既沒有所謂的“的本”也沒有什么“元本”,一切都是校訂者自己的理解與認知。他不便明說,只好某些假借“元本說”,某些又稱其無底本正之,而這種假借“元本”或“的本”的說法對于閱讀者應該有一定的說服力。當然,這兩種可能是基于凡例中的矛盾來推測,但在王驥德校注本“凡例”中,他認為真正見過古本的人并不多,而借用古本或元本之名的卻不在少數。因此,在這些刊本中應該存在校訂者假借“元本”或“古本”之名表達自己的觀點。
二、話語權的表達
如果說,從“注音”“釋義”“音律”上,尚不能充分顯現或反映出重刻者對于話語權的攫取。那么,從萬歷丙辰年(公元1616年)刊刻的何壁本《北西廂記》中,則能進一步感受到校訂者借重刻《西廂記》來表達自己的話語權。
何壁本“凡例”僅僅四條,遠少于他本中的“凡例”數量,但僅此四條卻擲地有聲,絕不附會他人,更沒有借鑒、抄襲他本“凡例”之舉。何壁本的四條“凡例”完全表達出,他在重新校訂時所持的態度與理解。
一、《西廂》為士林一部奇文字,如市刻用點板者,便是俳優唱本,今并不用。置之鄴籖蔡帳,與麗賦艷文何必有間。
二、坊本多用圈點,兼作批評,或污旁行,或題眉額,灑灑滿楮,終落穢道。夫會心者自有法眼,何至矮人觀場邪?故并不以炎木。
三、市刻皆有詩在后,如鶯紅問答諸句,調俚語腐,非唯添蛇,真是續狗。茲并芟去之,只附《會真記》而已,即元白《會真詩》亦不贅入。
四、舊本有音釋,且有郢書夜說之訛,殆似鄉塾訓詁者。今皆不刻,使開帙者更覺瑩然。〔6〕90-91
這四條凡例讓人耳目一新。首先,何壁將《西廂記》按照一部文學作品來校訂,而非一般的戲曲唱本;其次,則認為圈點、批評是多余的,面對這樣一部奇書應該有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態度,而非一定要有人去評點、詮釋,更何況評點者又并非能完全理解全文,這種評點無異于“矮人觀場”,反倒是令整潔的書頁密密麻麻地布滿了文字;其三,對于坊本、市刻所較為流行的注音、附錄相關的詩詞歌賦一概刪除,僅保留了元稹的《會真記》。
蔣星煜先生認為何壁在校訂此本時參考了多種版本,但沒有選定哪一種為底本,同時還依據自己的理解做出了部分的改動與刪削。那么,何壁在《西廂記》的校勘、編輯上,不僅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了校訂,同時對于《西廂記》的內容也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從他親自撰寫的“序文”中就能感受到:
《西廂》者,字字皆鑿開情竅,刮出情腸。故自邊會都,鄙及荒海窮壤,豈有不傳乎?自王侯士農,而商賈卒隸,豈有不知乎?然一登場,即耆耋婦孺、喑瞽疲癃皆能拍掌,此豈有曉諭之耶?情也!〔6〕90
序文的開篇,他就表達出對《西廂記》流行所持的不同看法。他認為《西廂記》之所以在繁華都會、荒海窮壤均能廣泛傳播與流行,而喜愛的人群從王公大臣到士農工商,從老少婦孺到盲啞的疲癃之人,可謂波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這種現象不禁令他懷疑“此豈有曉諭之耶?”顯然,他并不認為有人命令大眾去喜愛《西廂記》,而是劇中至情、至真的兒女情感染了所有人,也感染了他。因此,他借白居易所云:“人非土木終有情”〔6〕90,成為立論西廂之“情”的論點。在何壁眼中,兒女情是一種自然的流露,是人皆有之的,并無什么神秘或特別之處,而是一種自然的真情流露。他對待兒女情的態度與李贄、湯顯祖、馮夢龍等所持的觀點相似。
他的“序文”并不只著墨于劇中的兒女情,而對于何為情!又何謂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均有自己的觀點。對于何為情!他寫到:
客曰:“然則世之窰窕于枕席者,皆□□(情乎)?”予曰:不!此禪家所謂觸也。夫倚翠偎紅者,知淫而不知好色;偷香竊玉者,知好色而不知風流矣。名非司馬,詎許挑琴?才不陳思,豈堪留枕?此則可語風流。風流,故情也。〔6〕90
他認為“窰窕于枕席者”“倚翠偎紅者”“偷香竊玉者”皆不是為情,也不懂“情”,在他看來,如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般才是“情”,而在更進一步談到“情”與“欲”時,則毫不諱言地說:“名非司馬,豈堪留枕”,沒有“情”又何來“欲”呢!他的這種先“情”后“欲”的觀點與晚明社會普遍所持的情欲觀似有所不同。同時對于“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他亦有自己的看法。
世之論情者何瞶也,曰:“英雄氣少,兒女情多”,此不及情之語也。予謂天下有心人便是情癡,便堪情死;惟有英雄氣,然后有兒女情。古今如劉、項,何等氣魄,而一戚一虞,不覺作嚅呢軟態,百煉剛化繞指柔矣。惟其為百煉剛,方能作繞指柔,此固未易與羅幃錦瑟中人道也。〔6〕90
顯然,他的觀點是針對詬病《西廂記》的人們而言,尖銳者認為《西廂記》實則是一部“淫書”,而普遍的反對者認為書中太多兒女情長,如果沉溺于兒女情中會幻滅人的英雄氣。但他完全否定了這些觀點,認為英雄氣與兒女情并不矛盾,并以劉、項二人舉例,在他的眼中,此二人因“百煉剛化繞指柔”所以成就了英雄氣。換而言之,只有真柔情才有英雄氣。他將兒女情與英雄氣理解成辯證統一的關系,而非對立的矛盾體。雖然,在蔣星煜先生看來“序文”是一篇出色的文學理論和戲劇理論文章,但更像是何壁對晚明社會發出的一份情感宣言。何壁借重新校訂《西廂記》的機會,透過書中的愛情故事來闡述自己的情感觀。這種不附會他人的見解,顯然是何壁所期望的話語權。
晚明的校訂者、編輯者希望借助重新刊刻書籍的機會獲得話語權,應該是晚明重刻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其他人同樣會對話語權有所渴望,如唱本的實施者——優人,只不過他們的話語權往往被忽視或是沒有機會表達。
明天啟辛酉年(公元1621年)本《詞壇清玩·槃薖碩人增改定本》(又名《西廂定本》)“凡例”中寫到:
此中詞調原極清麗,且多含有神趣。特近來刻本,錯以陶陰豕亥,大失其初。而梨園家優人不通文義,其登臺演習,妄于曲中插入渾語,且諸丑態雜出。如念“小生只身獨自”處,捏為紅教生跪見形狀,并不想曲中是如何唱來意義,而且惡濁難觀。至于佳期之會,作生跪迎態,何等陋惡!茲一換而空之,庶成雅局。〔6〕192
“凡例”本意是指責一些優人在演劇時,妄自加入的一些“渾語”,甚至恣意篡改一些表演程式或動作等不良行為。無意間,留出了對優人話語權的想象。“凡例”中所謂“妄于曲中插入渾語”,應該屬于優人們在表演中的一種即興發揮,或是表演中忘詞了,或是刻意加上一句“渾語”助興,這只是一種推測。當然,還存在一種可能:晚明的劇作家往往與名優過從甚密,而優人們之所以在演劇時加入一些“渾語”,或許是征詢了劇作家的建議。晚明時期,校訂唱本時去征詢意見是比較普遍的現象,王驥德就曾在校注《新校注古本西廂記》時與沈璟通過書信交換意見。而他在校訂過程中是否征詢了優人的意見,尚無直接的證據。但是,他們與優人之間的交往是存在的。因此,從《西廂定本》“凡例”中,不難感受到優人們在尋找話語權的表達。
此外,《西廂定本》“凡例”中,除了對優人所加的詞句鄙夷不屑,更對于他們將佳期之會中的張生,改成跪迎狀,嚴加批駁并稱其為“何等陋惡”。顯然,《西廂定本》的校訂者認為改自優人演繹下的詞句與動作,既丑陋不堪也無法接受。他希望以自己的話語權否定或掩蓋出自優人的話語,但萬歷年間的環翠堂本《袁了凡先生釋義西廂記》卻是另一番選擇。在環翠堂本第十三出“月下佳期”的插圖中,張生跪在門口迎接鶯鶯的到來(見圖1)。同時,在晚明畫家王文衡所繪的《西廂記》第四本“小紅娘成好事”插圖中,同樣繪出了張生跪在了鶯鶯的面前(見圖2)。顯然,這兩個版本的《西廂記》是認同了優人在演劇中的改變。換而言之,優人的話語被人們看到了,也接受了。
這兩幅插圖既是對晚明優人話語權的肯定,也進一步反映出晚明重刻現象背后有著話語權的訴求。如果說《西廂定本》是完全否定“佳期之會,作生跪迎狀”的表演。那么環翠堂本應該是全面肯定這一表演。表面看是兩個完全相左的態度,實質是大家借助重復刊刻同一本書來表達各自不同的立場和觀點。
在這場關于“佳期之會,作生跪迎狀”的表演形式大討論中,環翠堂本的校訂者運用插圖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可以說,“插圖”成了校訂者的另一種表達話語權的方式。在天啟年間《凌濛初本·西廂記》“凡例”寫到:“故以每本題目、正名四句,句繪一幅,亦獵較之意云爾”〔9〕。“凡例”中校訂者對于即將刊刻插圖的數量、原則有著一套清晰的思路。在不同的《西廂記》版本中,刊刻者對于“插圖”的數量,所要表達的內容均有所不同。如萬歷庚戌年容與堂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有插圖20幅,此本沒有依據其他版本中常見的以《西廂記》情節內容為構圖主題的做法。而是選擇了《西廂記》中的經典曲文、詩句的意境作為構圖依據(見圖3)。而在明萬歷辛亥年本《重刻訂正元本批點畫意北西廂》的10幅插圖中,每圖均配以張楷的《浦東詩》中的詩句來表現(見圖4)。而一套現藏于德國科隆東方藝術博物館的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吳興寓五本《西廂記》,全套20幅插圖,采用了明代刻本中常見的“一畫一折”的形式,插圖內容以描繪劇中情節為主。但此套插圖在畫面構圖上卻別有新意,如在表現鶯鶯與張生初次會面以及紅娘傳書時,均是將人物形象繪制在器皿上,而第五出則更是將僧人惠明、杜將軍以及孫飛虎等人物巧妙地安排在一盞旋轉的走馬燈上。除此而外,還有將人物、場景安置在折扇、手卷、掛軸、箋紙等各類形式中。在這些截然不同的《西廂記》插圖上,表現出的不僅是形式內容上的差異,更應該看到重刻者也希望借助“插圖”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

圖1 《環翠堂本·西廂記》“月下佳期”插圖

圖2 《明刻傳奇圖像十種》之《西廂記》“小紅娘成好事”插圖

圖3 《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插圖

圖4 《重刻訂正元本批點畫意北西廂》插圖
在《西廂記》的重刻中,重刻者借助校注、評點、批評等文本形式表達著自己對于《西廂記》的觀點和看法。同時,他們還透過插圖數量、構圖形式、繪制內容表達不同的認知與理解。表面上,他們對于《西廂記》這本奇書熱烈、自由地抒發著自己的觀點,實則是借《西廂記》的重刻攫取自己的話語權。
三、利益的驅使
晚明書坊延請名人批評、校訂書籍是出于對他們學識、地位的尊崇。就名人而言,原本個人化的批評、校訂,現在能透過印刷的手段傳播給更多的人,這不僅彰顯了學識,收獲了話語權,此外利潤應該可觀,何樂而不為呢?而書坊主們更是樂見其成,原本就熱門的書籍加上名人的批評、點校后重刻一定能獲得一個好的商業利潤。如果說,在晚明不斷的重刻現象中,批評者、校訂者攫取的是話語權,那么書坊間爭奪的只是利益。
時人郎瑛就曾詬病建陽書坊唯利是圖翻刻別家的書籍〔10〕。實際上,唯利是圖的不只是建陽的書坊,晚明時書坊間競相翻刻別家的書籍是較普遍的現象。特別是《西廂記》這類熱門的書籍,更是能從重刻和翻刻中獲取豐厚的利潤。所以,“射利”成為了驅動晚明重刻和翻刻現象的另一因素。
刊刻于崇禎辛未年(公元1631年)的《北西廂》“凡例”中寫到:“評以人貴”〔6〕218。顯然,名人效應能給書坊帶來較好的經濟效益,而長遠看更能提升書坊的名譽與地位。因此,有的書坊甚至不惜假借名人的名諱出版熱門書籍,刊刻于崇禎庚辰年(公元1640年)的《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真本》“題卓老批點西廂記”中寫到:“如假卓老、假文長、假眉公,種種諸刻盛行不諱”〔6〕233。另,明后期刻本《新刻魏仲雪先生批點西廂記》,上卷次行署“上虞魏浣初仲雪父批評,門人李裔蕃九仙注釋”。而據陳旭耀的研究表明,在現存各種魏仲雪所批評的戲曲唱本均標有李裔蕃注釋,他認為這些版本應該是李裔蕃與書商合作,假借魏仲雪之名,刊行射利〔6〕176-180。由此,晚明時真正由名人批評的書籍,并不如實際的那樣多。更多是假借名人名諱,或是直接將別家的名人批評本拿來稍加改動進行翻刻。
而在書籍的刊刻中是否添加插圖,同樣表現出一種趨利、迎合的態度。如明濛初朱墨印本《西廂記》“西廂記凡例十則”中這樣寫到:
是刻實供博雅之助,當作文章觀,不當作戲曲相也,自可不必圖畫。但世人重脂粉,恐反有嫌無像之為缺事者,故以每本題目、正名四句,句繪一幅,亦獵較之意云爾。
“凡例”中準確地表達了三層意思:一、重刻者認為《西廂記》是作為“文章觀”而非“戲曲相”,故無需附圖。二、主觀愿望與現實差異太大,作為“博雅之助”的清雅之物,此時已然成為了大眾讀本。由于大眾尚俗,如果書籍之中沒有配屬圖像,世人會認為是一種“缺事”。三、明確提出了刊刻插圖的原則、數量以及畫面構圖的依據。在這三層意思中,從主觀不必配圖到沒圖成為“缺事”,最后明確插圖的數量與原則。重刻者的轉變,顯然源于現實中無圖則無法迎合讀者的理由,在他們的眼中,如果沒有讀者的追捧,重刻此本的意義何在?而書坊的利益又何來?
從真名人到假名人的參與;從不必配圖到無圖成為一種缺憾,變化的是書坊刊刻的手段,不變的是他們驅利的心態與原則。
綜上,《西廂記》重刻背后隱含的話語權,在明代的繪畫中同樣存在。巫鴻曾比較了幾幅宋元時期的畫作到明代重繪者手中所產生的不同表現,如南唐宮廷待詔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在明代的重繪者手中將畫面中“不合邏輯”的畫屏透視,糾正成完全合理的表現〔11〕70-73。再如元代畫家劉貫道的《消夏圖》中所表現的士大夫生活中社會責任與內室生活,二者并置的情境所帶來的視覺欺騙與迷惑,而在明代的重繪者手中一變成一幅單純的園中《消夏圖》〔11〕105-108。巫鴻不僅解讀了這些變化,同時借宋代一位摹仿者的仿作對于仿作的變化給出一種新的判斷:“一位宋代的摹仿者通過修改屏風圖像能夠立刻達到兩個目的:他一方面在制作一幅古代杰作的摹本,同時也能夠把一個或更多的‘當代繪畫’插入作品中”〔11〕143。巫鴻所說的“當代繪畫”應該是指一種符合當時流行的繪畫語言、形式和觀念,而這對于繪畫者而言是他們行使話語權的基本方式。一方面,摹仿者借摹仿向古代杰作、大師致敬;另一方面亦將自己的主張與觀念置入摹本中,借此向觀者傳遞出自己的話語權。雖然巫鴻描述的是一位宋代摹仿者的心態,但這種表述應該具有共通性。如果說宋人尚且存有如此心態,那么明人似乎更應該具有這種心態。明中期以來,隨著心學的興起與活躍,明人的思想亦隨之變化,表面上帶來了言情縱欲的生活,實質上,是對個體尊重以及自我表達的關注。而明人對于話語權的渴望,應該是心學思想影響下自我意識的自覺與自醒。
此外,到明中后期,書籍的刊刻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印刷技術行為,而是隨著一些失落文人〔12〕逐漸轉向一種復雜、多變,且具有時代特性的文化行為。他們認同印刷復制所帶來的廣范圍而有效的傳播性。于是,他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批評、校訂等這一文化行為中,藉此發表見解、展現才學,撿回游走于朝堂之外的失落感。
這些失落文人不斷借助批評、校訂的機會,在話語權上找回一些顏面。而商人們則通過這一文化行為來獲取利益,甚至不惜弄虛作假。這些或基于話語權的攫取,或基于利益驅使的行為,在晚明的印刷文化行為中似乎都變得自然而合理。于是,晚明人用不斷重復刊刻同一種書籍的行為,來肯定其利益攫取的合理性。并將失落文人所隱含的話語權,自然而然地填充到一次次的重刻中。他們以重復的行為滿足著晚明社會對大眾文化的需求,也成就了晚明獨特的印刷文化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