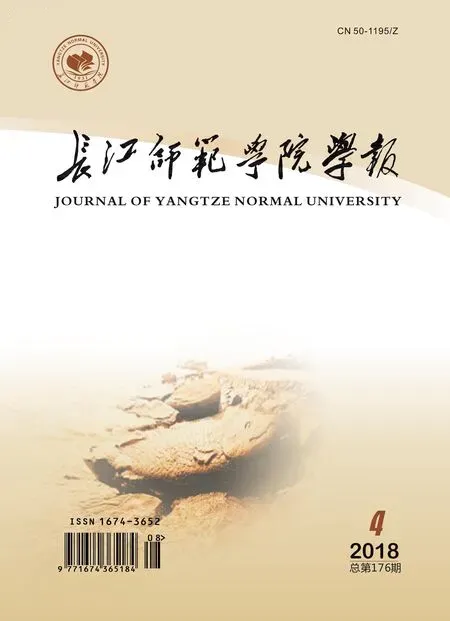試論比喻義
張薇薇,化振紅
(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南京 210023)
漢語詞義與修辭手法有著密切的關系,王力在《漢語史稿》就曾提到:“詞義的變遷和修辭學的關系是很密切的。在許多情況下,由于修辭手段的經常運用,引起了詞義的變遷。”[1]韓陳其在《漢語詞匯論稿》中作了進一步說明,他認為引起詞義變遷的修辭手法有很多,最常見的是借代,其次是比喻以及委婉、夸張,等等[2]。借代、比喻等修辭手法在整個詞義演變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那么作為修辭手法的比喻到底是如何影響詞義的呢?
一、比喻造詞和比喻生義
符淮青在《詞的釋義》中指出,比喻義是指詞的比喻用法固定下來形成的意義。比喻義的來源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從本義、基本義產生的比喻義,二是從引申義產生的比喻義[3]。可以得出,比喻義是由詞的本義、基本義或者其他引申義通過比喻的修辭手法引申并固定下來的新意義。詞的比喻義不是一個詞在某個臨時性語境中的比喻用法。比喻用法是修辭上的打比方,它所產生的意義具有時過境遷的特性,沒有穩定性可言。如:
(1)魯迅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斗爭精神。……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毛澤東《論魯迅》)
這里的“大樹”比喻魯迅,也包括了那些具有斗爭精神的人。“小草”則比喻那些立場不堅定的人。但這樣的釋義只是“大樹”和“小草”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通過比喻手段所獲得的臨時語境義,離開了這個語境,這樣的意義也就不存在了。這種臨時語境比喻義既不會被人們經常拿來運用,更不會被收入詞典作為詞語的義項。
但是,當詞語的比喻用法固定下來,就會形成一個能夠脫離語境而意義不會發生改變的比喻義。一個在詞義系統中占據了一席之地的并得到了人們認可的比喻義,它的意義內容在詞語形式中,可以表現為一個新的詞語或者增加原有詞語的義項。比如“佛手”,就是指一種果樹,它的果實的形狀如半握之手,因此而得名。這個比喻義使得“佛手”這個新詞語產生了。又如“知音”,本指通曉音律,后來喻為知己。比喻義“知己”的產生,僅僅是使得“知音”這個詞語增加了一個新的義項。前者因為比喻義的固定而產生了新的詞語,可以叫比喻造詞,而后者則可以叫做比喻生義,因為僅僅是詞語的本義或者其他引申義的比喻用法穩定下來,形成一個新的義項,沒有增加新的詞語。
關于比喻造詞,任學良在《漢語造詞法》一書中說:“比喻造詞法的特點是,用他事物的形象來指稱本事物,而且本事物并不出現。這是修辭學上的‘借喻’。”[4]205修辭學上的借喻是指全然不出現本體,也不出現比喻詞,而只用喻體來作為本體的代表,即只出現喻體。如:
(2)我一早晨跳上火車,撲著祖國的心窩奔去。(《楊朔散文選·用生命建設祖國的人們》)
(3)大赤包臉上的雀斑一粒粒的都發著光,像無數的小黑槍彈似的。(老舍《四世同堂》)
例句中的“雀斑”是指人臉上生的一種黃褐色或黑色小斑點,因其類似麻雀身上的斑點而得名,并不是指真正的麻雀身上的斑點。從“雀斑”的詞匯意義可以看出本體和喻體已經融為一體,修辭手法已經固定在了詞匯意義中。例句中老舍甚至又將其作為一個新的本體比喻成“小黑槍彈”,但是這還
例句就屬于借喻的情況,直接用喻體“祖國的心窩”代表了本體“首都北京”。這種修辭學上的借喻在詞匯學中,有時候可以直接導致一個新詞產生。只是處在修辭用法的階段。
任學良將這種通過比喻用法而產生的詞叫做比喻詞,他還提出比喻詞所必須具備的三個條件:喻體能直接代表本體,甚至和本體合二為一的;比喻義已經在語言里扎根兒,詞典可以收進去列為一個義項的;喻體已經抽象成詞的[4]216-217。除此之外,他還介紹了兩種比喻造詞法,一種是完全新造,另一種是采取移花接木的辦法。“移花接木”就是指利用舊詞創造新詞[4]217-218,屬于完全新造詞一類。他以“仙人掌”舉例,認為這是詞匯里原來沒有的,是人們憑借著想象,認為這種植物像仙人的手掌,于是就造出來新的詞語,這屬于比喻造詞。所謂的“移花接木”,他舉了“醞釀”一詞,并通過詞義模型圖明確指出,“醞釀”是把表示酒的“發酵的過程”移到“準備工作上去”,這就是“移花接木”一類的造詞。但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醞釀”一詞的本義和比喻義之間是有引申過程的,而且表示“制酒”的本義并沒有消亡,甚至我們今天還在使用。如“這壇酒醞釀了很久”,從本義引申出來的“做準備工作”這個比喻義,僅僅是使“醞釀”這個詞語增加了一個新的義項,并沒有產生新詞語。所以,認為這種情況仍然屬于比喻生義的范疇。
二、比喻造詞和比喻生義的辨析
關于比喻造詞和比喻生義的辨析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比喻義在詞義鏈條上所處的環節,比喻義的固定是否使得詞語的數量發生變化。
當比喻義是在至少有兩個義項的詞語內部產生時,比喻義產生的結果僅僅是使得一個詞語內部的詞匯義增多。比喻義產生的基礎是本義、基本義或者其他引申義。
關于比喻義與引申義之間的關系,學界大致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認為比喻義和引申義在詞義系統中是處在同一平面的。周光慶在《古漢語詞匯學簡論》中指出:“詞義的派生方式,是根據客觀事物之間的這種關聯,和由這種關聯所引起的相應聯想的形式來區分的。概而言之,主要有比喻的方式,借代的方式和引申的方式三種。”[5]周光慶將比喻、借代和引申放在同一個平面來分析詞義的演變。另一種是認為比喻義是眾多引申義中的一種,如羅正堅在《漢語詞義引申導論》中提出:“比喻引申只是詞義引申中的一種,比喻引申和借代引申才是在一個平面上相互并列平行的,用同一個標準分類的,都統屬于詞義引申之內,這是從修辭角度來分類的……漢語的詞義引申雖然不完全都與修辭上的比喻和借代有關,但是從修辭角度來談引申詞義,主要是比喻引申和借代引申。”[6]肖模艷也認為,比喻義應該與本義有衍生關系,所以比喻義應該屬于引申義,是其下位概念[7]。這兩種觀點形成的前提條件都是針對某一個詞語至少有兩個意義而言的,比喻義的產生只是增加了某一個詞的詞匯義項。在這一前提下,很顯然羅正堅的說法要比周模艷的說法更深入一些。詞除了它產生之初所代表的那個意義外,其余的意義大部分都是通過各種途徑引申得來的,都可以叫做引申義。只不過引申的方式從修辭角度來分析,有的屬于比喻,有的屬于借代,有的屬于委婉、夸張等。總之,詞義的演變是和比喻是分不開的。
但是,還應該注意到另一種現象,就是那些依托比喻義而產生的新詞語。比如“猴頭”“狐疑”“影附”,這些詞都只有一個意義,雖然當兩個語素組合在一起時有字面上的表層意義,且符合邏輯常理。“猴頭”就是猴子的頭,“狐疑”就是狐貍懷疑,“影附”就是影子附著形體。但是在實際的語言環境中,人們幾乎不會使用詞形的表層意義,經常使用在語言環境中的是其深層的比喻義。深層的比喻義才是新詞產生最主要的動因,離開這個比喻義,這個詞語也是不存在的。“猴頭”就是指形狀像猴子頭一樣的一種蘑菇,“狐疑”就是指具有像狐貍一樣的品性——懷疑和猜忌,“影附”就是指像影子一樣去附會。誠然,不能否定的是表層意義是深層比喻義產生的基礎,但是比喻義才是新詞形產生的根基,詞語的形式一開始就和比喻義的內容緊緊結合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比喻義是固定的,而且也是人們經常在使用的,但卻是不存在引申關系的,這樣的詞語如“棋跱”“地芥”“魚貫”、“龜縮”,等等。另外,有時候新詞語的產生并不表現為新的詞語形式的增加。比如“龍眼”“雞眼”這一類詞,它的表層意義人們偶爾也在使用,如:
(4)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
(5)布農人家里殺雞,小孩禁食雞的頭部、眼睛、胃、爪和臀等,傳說吃雞頭會生病,吃雞眼會每天流淚,吃雞胃身上會紅腫。
例子中的“龍眼”和“雞眼”都是指真正的龍眼睛和雞眼睛。但是這與表示水果的“龍眼”和表示疾病的“雞眼”之間沒有任何意義上的聯系。《漢語大詞典》對“龍眼”的解釋有兩條:一是常綠喬木。羽狀復葉,小葉橢圓形。花小,黃白色,圓錐花序。木質致密,可以制器具,是我國福建、廣東等地的特產;二是指這種植物的果實,為果中珍品,也稱桂圓。對“雞眼”的解釋也有兩條:一種不符規定的劣等錢幣;一種是病名,由局部表皮久受壓迫或摩擦,腳掌或腳趾上生的小圓形硬結,有壓痛。因此,表示龍眼睛的“龍眼”和雞眼睛的“雞眼”,與表示水果的“龍眼”和表示疾病的“雞眼”應該是屬于同形同音詞,也就是詞語的讀音和寫法一樣,但在意義上沒有任何聯系,對于同形同音詞學界普遍認定為多個詞。這種情況最終也導致了詞語數量的增加。
所以,比喻義在詞義鏈條上所處的環節,應該有兩個層面。一種是以比喻義作為詞語產生時最初的意義,事物或現象象什么就用什么來命名;另一種是比喻義只是某個多義詞的一個義項,是從本義或者其他引申義通過比喻的方式引申得來的。在詞義的鏈條上,前者是處在詞義鏈條的第一環節,后者則處在詞義鏈條上除第一環節以外的任意一節骨眼上。
郭伏良在《漢語比喻造詞的類型與色彩》一文中從詞義現象和新詞產生的角度,對比喻造詞和比喻生義進行了區分:“比喻造詞就是通過比喻手法創造新詞,如‘猴頭、雪白、喇叭花、面包車’等都是用比喻法造出來的新詞語。比喻造詞既不同于已有的詞增加比喻義,也不同于詞的結構分析。已有的詞產生比喻義,如‘起飛’這屬于一詞多義現象,不能看作通過比喻創造了新詞。有的論著認為,某個詞,其比喻義一經形成,人們便相沿習用,天長日久,這個詞的比喻義便成為它的一個義項,這便是比喻構詞的過程,這顯然是把詞義現象與新詞產生混為一談。”[8]郭伏良認為,一個詞語的比喻用法穩定以后,被社會認可,那么這個詞的比喻義就產生了。這是在詞語原有的詞義基礎上增加了一個新的義項,使得一個詞內部的詞義數量增加,是一種詞義現象。然而如果隨著一個新比喻義的產生,一個新的詞語也產生了,那么這就屬于比喻手法創造新詞。其實,新詞語的產生必然會引起詞語數量的增加。增加詞語義項的詞義演變現象并不會引起詞語數量的增加,它所能引起的只不過是使某個詞語內部的義項數量增加罷了。
在《漢語大字典》中,“起飛”有兩個義項:一是飛起來,開始飛行。一是喻飛速發展。很明顯第二個義項是第一個義項通過比喻用法引申得來的,它已經穩定下來,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意義,往往指某件事情的發展過程。如:
(6)作為時代的先行者,廈門人特別是湖里人是多么自豪!然而,經濟起飛的必要前提機場在哪兒?碼頭泊位在哪兒?(陳慧瑛《心若菩提》)
例句中“起飛”是指經濟的飛速發展,可見“飛速發展”這一比喻用法已經穩定下來,形成了固定義,并被人們廣泛使用。這一類詞還包括“光明”“高峰”“暗礁”“骨肉”“項領”,等等。
因此,當一個比喻義最終固定下來是引起詞語數量增加的話,那么它的固定肯定是伴隨著一個新詞語的誕生,這就是比喻造詞。而比喻義的固定沒有引起詞語數量的增加,而導致某個詞語內部的詞義數量增加,這就是比喻生義。
三、比喻造詞和比喻生義產生的機制
一個穩定的比喻義在詞匯系統中往往會產生一個新的詞語或是增加原有詞語的義項,這首先是由比喻義本身所具有的、能夠使事物的形象變得具體生動的本質特性所決定的。我國是一個富于修辭使用的國家,其中比喻的運用歷史最為悠久[9]。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夏桀時代,人們就用比喻來詛咒夏桀:“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這里的“日”是借喻,指暴君夏桀。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也能發現許許多多的比喻蹤跡。“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詩中用“碩鼠”來比喻貪婪的剝削階級。“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詩中用了多個比喻來形容莊姜的美貌:她的手就像剛發芽的嫩草,她的膚色就象那潔白的玉脂,她的脖頸像天牛的幼蟲那樣潔白豐潤,她的牙齒象葫蘆的籽。通過比喻,莊姜的美變得形象又生動。可以說,運用比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使表達的內容變得更加形象和生動。不管是創造新的詞語還是給詞語增加新的意義,它們都屬于表達內容的范疇,同樣具有追求形象、生動的特點。
其次,是由人們在交際過程中追求表意生動、具體的主觀意圖所決定的。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它是為整個人類社會服務的,是人類特有的一套音和義相結合的符號系統,而詞匯又是使語音形式和意義內容能夠在語言中呈現出來的重要載體。詞是最小的能夠獨立運用音義結合體,給詞加上一定的語調,就可以單獨成句。即使是復雜的句子也是由詞按照一定的語法規則,再加上語調組織起來的。在交際中,除了刻意追求表意的晦澀、深奧外,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都會希望自己的表達內容能夠生動具體,使對方能夠準確地接收話語信息。因此,在創造新的詞語和增加詞語的新意義時,為了適應交際的需要,人們往往也會選擇形象、生動的比喻修辭手法。
比喻義能夠使事物變得生更加形象、生動的這一本質特性與人們在創造新的詞語以及增加詞語新意義時,追求表意生動、具體的主觀意圖不謀而合。筆者對詞語的比喻用法、比喻義、比喻造詞以及比喻生義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簡單梳理,圖1所示:

圖1 詞語的比喻用法、比喻義、比喻造詞以及比喻生義之間的關系
總之,一個詞語的比喻義是它的比喻用法經常運用的結果,比喻義的形成必須經過比喻用法這一環節。有的時候,隨著比喻義的產生會誕生相應的新詞語,而有的時候僅僅是增加某個詞的詞匯義項。判斷一個比喻義的產生到底是屬于比喻造詞的范疇,還是比喻生義的范疇,最直接的一個判定標準就是看這個新生的比喻義到底處在詞義鏈條的哪一個環節。如果是處在最開始的那個環節,就屬于比喻造詞的范疇。但如果是處在其他環節,那就屬于比喻生義的范疇。其次是看比喻義的產生到底有沒有增加新詞,如果使得詞匯數量增加,就屬于比喻造詞。如果沒有增加詞匯數量,就屬于比喻生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