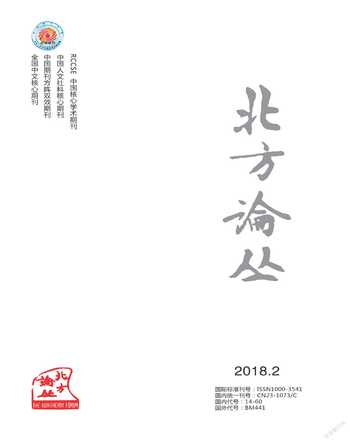近代以降制約中華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論略
趙麗媛
[摘要]自古以來中華文化獨樹一幟、綿延不斷。至18世紀英國完成產業革命前,中華文化及文明盛行于西方長久不衰。然而,于漫長的歲月中,中華文化漸次形成一定的痼疾,如文化上的故步自封,精神上的不思進取,思想上的墨守成規,導致中華文化漸漸落后于西方文化進程,這些致命缺陷終于使古老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落敗,文化自信遭遇動搖。歷經器物、制度變革國家依舊尋不到復興道路,于是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精英將國家復興的出路鎖定在對中華文化的重新構建上,由此形成眾多迥異的中西學觀。然而,種種文化爭論皆有缺陷,文人政客對中華文化的矯枉過正成為動搖中華自信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改革開放國門打開,西方先進的經濟科技優勢逐漸轉化為一種文化上的壓力,對我國形成強大的現實挑戰。
[關鍵詞]近代史;西方優勢;中華文化自信
屈辱的近代史讓國人感到羞辱與義憤,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中華文化自信的凋敝。回顧歷史、深析原因,一方面為曾經的失敗做出反思,即中國不能依賴任何一種文明或文化;另一方面,為今日之中國發展正心,即民族自強和文化自信實乃中華崛起之根本。
一、屈辱的近代史對中華文化自信的巨大影響
文化是國家標識與國民支柱,深藏其中的是穩定的價值觀及其信仰體系。中國近現代百年的屈辱史表面上摧毀的是虛弱、腐朽的政治經濟制度,實則破壞的是中國人對自身長達千年的社會價值觀及文化、文明的信心與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對中華文化自信的影響有歷史和現實原因,歷史因素是主因。
(一)中華文化在近代以前的世界領先地位
春秋時期的“華夏”代表的是一種高度的文明與文化,千百年來,中華文化完成對異質、異域文化的吸納與融合,于公元3-16世紀一直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在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中,漢文化始終處于文化的核心。自漢朝以來形成的以中華文化為核心的文化圈,影響深刻并改變諸如日本、朝鮮、韓國等國家。中華文化由內而外展現出的包容、創新與系統性不僅成就了一個個繁榮鼎盛時代,還使中國自漢朝一統后,即成為唯一能與西方羅馬帝國相較高下的封建大帝國。長久以來,備受青睞的中華文化一直是先進與文明的代名詞,成為當時眾多封建國家建制規范的楷模。亨廷頓曾指出,(18-19世紀)“中國的拒絕主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中國作為中央帝國的自我形象和堅信中國的文化優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
(二)近現代西方列強的侵略對中華文明的沖擊
自19世紀資本主義文化傳人中國,中西方文化關系便逐漸發生逆轉。中國傳統文化不斷被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擠壓,大致經歷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性帶動了文化的拓展延伸。西方傳教士帶去了當時歐洲宗教、天文、數學、立法、地理等方面的新成就,然而,并未引起中國的足夠重視。清朝文化的排外政策使中西文化交流受到巨大阻隔,文化間的差距漸漸增大。
第二階段是1840-1949年,中西文化交流進入高潮。此時,西方將資金、技術、軍事等作為強大后盾,攜藝術、宗教、思想觀念等涌人中國。于18世紀在世界上,率先完成產業革命的英國,在資本的助力下,剔除掉資本主義文明在東方的全部偽裝,不惜一切代價的野蠻擴張成就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巨大成功,西方文化的擴張性強烈沖擊了缺乏進取心、創新和改革精神的中國文化。“中國被無情地蒙上了骯臟、落后的陰影”。鴉片戰爭戰敗后,強大的物質文化擠壓使中國各種力量粉墨登場,頑固派、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于中西文化交鋒中做出不同反應。頑固派盲目排外,拒斥一切外國事物。洋務派力求自強,掀洋務運動。先有林則徐著《四洲志》,后有魏源撰《海國圖志》,明確提出:“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四夷者,外夷制之。”雖然“其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尤未脫離凈盡”,但甲午海戰盡顯中國虛弱,民族危機不斷加劇國人對中華文化的懷疑和否定。于是維新派力主變法圖存,終難抵頑固封建勢力,以失敗告終。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欲于中國實行西式資本主義制度,卻被袁世凱篡奪革命果實,形成長期軍閥混戰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既加劇中華民族的危機,也加劇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鴉片戰爭后每隔40年即淪陷一次的情勢,將國人自信無情打落,于“五四”后30年中,中國人一直陷于對自身文化的又愛又恨之糾結中。其間的兩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及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保命成為個人當務之急,自信嚴重受挫。
二、近現代啟蒙思想家對中華文化建構的矯枉過正
近代以來,思想家、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的建構與爭論不絕于耳,反映在文化上,則形成諸多相異又相關聯的中西學觀。爭論之中,各有缺陷,然矯枉過正亦是動搖中華文化自信之另一個重要因素。
(一)從“西學中源”到“中體西用”的爭論
這是19世紀60-90年代末的西學觀。“西學中源”即西學來源于中學。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20年后,“夷狄之學”才在中國思想界引起巨大反響。守舊派奉中學典章為圭臬,對西學一概貶斥拒之。對西學的無知與恐懼,加之鴉片戰爭失敗后巨大的心理落差,表現在文化上,則是“外夷奇器,其始皆出中華。久之,中華失其傳,而外夷襲之”的偏頗。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鐘天緯等人詳述論證西學并非源于中學,為維新派引入“西學”提供有力依據。“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被視為“中體西用”之雛形。此后,沈壽康、孫家鼎、張之洞等人均有相應闡述。但早期洋務派思想家均將西學視為異學、雜學,中學之輔,且多“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中體西用”之目的原為“善用其議,善發其器,求形下之器,以衛形上之道”。隨著認識加深,洋務派日漸感到形下之器,愈加難衛形上之道。原因是“中體”冗陳時時束縛人的思想與視野。如何超越“中體”,引入西學之真正精髓成為洋務運動后期啟蒙思想家的重點思考。郭嵩燾指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重商賈以為循用西法立基”,此后,王韜、鄭觀應、薛福成等洋務派思想家亦提出類似說法。顯然,鄭觀應等人看到西學之精髓在其本,過多強調“中體”“難臻富強”,因此,主張“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才能“于以拓車書大一統之宏觀而無難矣”。
應該說“西學中源”是強烈的民族自尊與自卑心理的產物,亦是中華傳統文化對近代思想家的心理制約使然,但它“逐漸演化為一種思維定式,釀成了一種惡習……傳統文化成了包羅萬象、涵容一切的膨脹體”,并且“成為一個沉重的思想負擔和文化阻力”。而“中體西用”雖然于洋務運動早期在倡導西學、革新文化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難以跳出儒家思想的倫理束縛,終因封建思想意識對文化的阻抑作用而被縛手腳,難圓其說。
(二)從“充分的西化”到“中國本位文化”的論戰
這是五四前后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西學觀。因保守復古、折中調和俱未沖破腐朽沒落的封建文化桎梏,于是徹底蕩滌障礙,成為西化派的政治文化主張。1929年,胡適最早提出“全盤西化”。1935年時,胡適認為,這種提法有語病,因此建議以“充分的西化”取代之。本文為同20世紀60年代李敖的“全盤西化”區分,這里用“充分的西化”提法,粗略看來西化派內部可分為極端西化派和充分西化派。“極端西化”派的代表人物有陳序經、馮恩榮等人。他們認為,文化是整體不可分,要么全盤接受,要么全盤丟棄。而主張“充分的西化”如胡適、吳景超、張佛泉等人則認為百分之百的西化不可能,因為中國舊文化“惰性”太大,只能“打破枷鎖,吐棄國渣”,因此,“不妨拼命走極端”,“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紀的新文明”,結果才會走向“折中調和上去”。然而,以梁漱溟、杜亞泉等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就如何對待中西文化問題與西化派意見相左。他們反對陳獨秀、胡適等人的“西方中心主義”,固執于“中體西用”難以自拔,要求“復興中國文化”,強調文化的調和與互補。陳獨秀、胡適等人從策略上考量堅決反對,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至此,西化主張被推向極致。20世紀20年代后期,基于國共內戰漸歸沉寂的國粹派與新文化派的東西文化論戰,于30年代中期,因嶺南大學教授陳序經在《中國文化的出路》中,批判文化復古派與折中派,重提“全盤西化”而烽煙再起。1935年,陶希圣、何炳松等10位教授共同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掀起知識界對中國文化出路的爭論。然其復古保守的文化傾向實難抵抗五四后中國知識精英對傳統文化的圍剿,加之20世紀30年代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所帶來的文化困境和民族心理焦慮,中國本位文化論于1936年春草草收場。
五四之后,西化潮流不可逆轉,激進的文化選擇漸成主流,但矯枉往往過正,西學的引進建立在胡適等人對中國傳統體無完膚的指責與批判之上,從而使“德先生”與“賽先生”在國人心目中上升為“德菩薩”與“賽菩薩”。
(三)從“全盤西化”到“西體中用”的主張
這是20世紀60-80年代的西學觀。20世紀60年代,反傳統、求西化等自由主義思想在我國臺灣地區盛行,李敖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引起我國臺灣地區的文化論戰。李敖借中西文化論戰為中國思想趨向所求得的藥方是“全盤西化”。李敖所謂的“全盤西化”指的是西方的現代化,包括科學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形態的西化。20世紀80年代,李敖又將“全盤西化”進行調整,指出:“我所謂全盤西化只是充分地世界化,并不是百分之百”,“所謂西化的意思就是要我們面對、選擇、并接受真正現代的文明。”然而,在辯論中,“李敖對傳統文明的態度相對來說是簡單的,他解剖了傳統之弊,清算了傳統文化,在技術上,以矯枉過正的姿態做掩護,在思想內容上,卻并沒有對傳統做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分解和分析,李敖對中西文化優劣的比較,顯得淺顯、直接、粗疏,存在一些偏頗之處”。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所謂“精英分子”賣力鼓吹“全盤西化”論,除卻其政治目的,單就這種極端提法,五四時期,胡適已然批判過,不做復解。同一時期,李澤厚以“西體中用”為主張闡發自己觀點。從價值取向上看,我國許多學者都將李澤厚的主張視為“全盤西化”之變種。李澤厚的“體”指社會存在的本體,包括物質生產和日常生活。現代化和科技皆屬“體”之范疇。而“西”既包括“體”也包括“西學”。“用”既包括西體用于中國,又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學”應作為實現“西體”(現代化)的途徑和方式。因此,李澤厚的“用”指的是適用、適合、應對的意思。“中”即對西學的判斷、選擇、修正、改造中便產生“中用”。因此,李澤厚的“中”應解釋為中國現實的社會存在和傳統思想與觀念。不難看出其觀點是“西體互包,中用互包,西用互包”,難以跳出“以西方的原則為原則”,看似構建了一種新式文化提法,實則互相雜糅,概念混亂,不過“是變相的全盤西化論”而已。
復古也好,折中也罷,抑或全盤西化,中國近現代啟蒙思想家對中華文化的構建、爭論、糾纏與糾結時時影響主導人心。然而從現實看,西化派的矯枉過正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華文化進程,但是使“我們摒棄了本身優良的一面,但卻不自覺地保留了壞的一面;反之,我們吸收了西方最表面、最膚淺及最劣的一面,但卻沒有攝收到西方最深層和優秀的一面。例如,我們盲目地沾染了西方的消費主義和炫耀心態,但沒有貫徹高消費經濟背后那種重視個體的責任感;仿效西方民主選舉形式,但沒有法治的基礎及其他機制去約束操縱選舉的行為;硬生生地輸入西方的科技,對科學背后的哲學及精神卻不加深究;只憧憬和進行西方式的競爭,卻漠視這種競爭對個人發展的正面意義”。
三、現代西方經濟文化優勢對文化自信的沖擊壓力
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愈發看重創新戰略。其卓越、迅捷、開放的特點促進了經濟與科技的互動,從而強化了文化與教育的基礎,使文化再次改變人們的生活。西方經濟科技等領域的優勢,旋即化為一種文化上的壓力,對我國形成強大的現實挑戰。
(一)強大的經濟與科技力量侵襲
西方國家憑借其發達的經濟體系、超強的科研創新能力,主導世界秩序。以美國為例,在技術、人力、資本、信息、軍事、經濟和外交等方面多年來穩居世界第一。即便2009年身處危機之中,美國的競爭力也依然不可撼動。《金融時報》指出,美國在應對衰退方面比多數國家都更為嫻熟,因為美國追求開放、發達技能與流動能力的傳統,使該國在徹底改造自身方面處于比競爭對手更加有利的地位。根據《2015-2016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對全球140個經濟體在促進生產力發展與社會繁榮方面的“全球競爭力指數”進行排名,美國排第三位。冷戰以來,美國憑借對尖端、優勢科技領域的投入與研發,對眾多優秀科研專家、頂尖實驗室、先進科研成果、研發設備,以及核心技術專利水平與數量等優勢生產力的掌控,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也使自身始終保持世界領先地位。這種經濟與科技的全面領先造就了美國文化、價值觀和政治經濟模式在成為世界模式范本的同時,亦達到支配弱國同中心國家保持同步的思想觀念和心理認同基礎,形成一種文化上的認同和霸權。相比之下,我國在改革開放打開國門后,由于未能正確認識中西方經濟差距產生的原因,從而導致部分人從信心滿滿地建設社會主義,逐漸轉變為對社會主義道路和文化的失望。這無疑與某些大國“能將它的法則和意愿(至少通過有效的否決權)大部分施加于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甚至于文化領域”。所產生的霸權息息相關。
(二)發達的文化與教育資源支撐
眾所周知,美國的教育質量和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相較其他國家均高。就教育吸引力來說,中國留美學生2015/2016年度達到328547人,占在美國留學生總數的31.5%。教育與文化交流日益成為西方或美國的國家戰略。始于1948年的“富布賴特”項目是美國國家長遠利益投資的藍本,隨著全球化發展,它日益覆蓋至教育、科技、醫學等眾多領域,造就了一批批與西方世界保持一致的決策層和輿論創造者。“項目”以各種形式資助本國及外國精英人士的教育交流與學習,并向海外派遣志愿者及發放音像制品,依托強勢的經濟科技優勢將美式價值觀打包發給留學生及國外精英人士,使其自愿模仿美國,被西方同化,從而影響并改變其思維框架和行為方式,失去自身特點甘于淪為附庸。針對這種摒棄傳統武力征服,旨在改變人們思維,溫和輸出美式價值觀、政治文化、商業規范及國家習俗的方式,所以有西方學者指出,文化是一種“軟實力”。優質發達的文化教育資源與國家的鼎力協助成全了美國教育,使之轉化為一種特殊的政策工具服務于國家向外推行霸權活動,在為其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也悄無聲息地改造他國的傳統思維。美國學者弗蘭克·寧科維奇指出:“文化手段和政治、經濟、軍事手段一樣,不但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組成部分,在大國間軍事作用有限的情況下,特別是在現代核戰爭中無法嚴密保護本國的國家利益。因此在不受報復的情況下,文化手段尤其成為美國穿越障礙的一種更加重要的強大滲透工具。”
(三)先進的媒體宣傳與浸潤優勢
全球化不僅加速了國際間的融合和信息流動,還為西方文化的擴張性和攻擊性提供了廣闊舞臺。廣播、報刊等傳統媒體的力量正逐漸被基于互聯網及計算機的發展而帶動的如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推特,臉書等新媒體功能所覆蓋。傳播手段豐富,傳播容量巨大,傳播成效顯著,已成為西方媒體宣傳的優勢特色。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整合傳統與現代生產生活方式的交互中,重建一種代表強勢文化的價值觀念及信仰體系,影響思維和人心。而且信息的快速傳播也樹立了西方發達國家先進完美的形象,技術決定論強化了弱國對強國的崇拜,進而擴展為對西方文化的傾慕與認同。文化產業的成熟亦加劇西方文化浸潤與侵蝕的空間。阿爾溫·托夫勒指出:“世界已經離開了暴力與金錢控制的時代,而未來世界政治的模仿將控制在擁有強權人的手里,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絡控制權、信息發布權,利用英語這種強大的文化語言優勢,達到暴力金錢無法征服的目的。”西方先進的媒體宣傳與浸潤在零碎的時間內,輕易俘獲人們的心靈,別有用心的文化粉飾使邊緣國家隱秘地落人中心之國預先挖好的文化陷阱中。西方學者伯努瓦指出:“資本主義賣的不再僅僅是商品和貨物。它還賣標識、聲音、圖像、軟件和聯系。這不僅僅將房間塞滿,而且還統治者想象領域,占據著交流空間。”相比之下,我國媒體宣傳的成熟性與反應性與之存在一定距離。
盡管中華文化曾在漫長的歲月里獨樹一幟,卻在近代西方列強的侵略欺壓和文化交鋒中敗下陣來。近現代啟蒙思想家對中華文化的過分褒揚與批判導致文化自信的急劇衰落。這兩點是中華文化自信衰落的主要原因。近代以來西方經濟、文化、科技、媒體等優勢的侵襲與同化再次給予中華文化巨大壓力。以上三者成為制約近代以來中華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