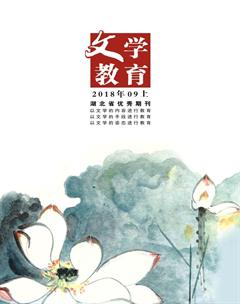賽珍珠與安德森作品中的母親形象比較研究
內容摘要:賽珍珠與舍伍德·安德森這兩位同時代的美國作家,身處不同國度,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所塑造的“母親”形象卻面臨著相似的“失語”狀態,而這兩位相似處境中的母親卻走向了不同的結局。對比探究兩位作家所塑造的兩個形象,有助于讀者準確解讀作家的創作思想,進而理解中西方文化背景下不同文明所決定的母親身份的差異性,以及性別差異對作者對待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抗爭的態度所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賽珍珠 安德森 母親形象 女性抗爭
美國作家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被譽為“現代小說的先驅”,他在1919年出版的小說集《俄亥俄·溫斯堡》中塑造了一群心靈扭曲,行為怪異的“畸人”,這本書“勇敢地走出中西部文化荒涼的誤區,打開了20年代美國小說通往現代化的道路”[1],奠定了他在美國文學史中的地位,并深刻影響了福克納、海明威等后輩作家。在其所塑造的眾多畸人中,“母親”——伊麗莎白·威拉德頗具分量,作家在《母親》和《死》兩個短篇中為我們描繪了她畸形的悲劇人生。無獨有偶,同為美國作家的賽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在長篇小說《母親》(1934)中,也塑造了一位母親。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這樣評價道:“‘母親在賽珍珠的中國女性形象中是最完美的,這本書也是她最好的一部。”[2]當時的《紐約時報》也對《母親》這本小說大為贊賞,稱之為“最具有建筑統一性和簡潔有力特征的作品”,認為她的成就還表現在“她從人類普遍價值觀的角度來描述與我們自己相異的民族”。[3]安德森與賽珍珠兩位同時代的美國作家,在中美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創作出的母親形象有著相似的處境與相異的結局。
一.不同文明中的母親形象
安德森筆下的母親伊麗莎白與賽珍珠筆下的母親生活環境差異巨大:一位是居住在美國小鎮的美國母親;一位是土生土長的中國農村母親,除了她們巨大的文化差異外,她們身上還有許多不同之處,她們的外形相異,對自身命運的抗爭方式與結果也截然不同。然而,這兩位有著眾多差異的母親卻面臨著相似的處境——她們都因身處男權社會而處于“失語”狀態。
《俄亥俄·溫斯堡》又譯《小城畸人》。“小城畸人”這四個字簡單而準確地概括了該書內容,該書主要介紹了居住在溫斯堡的一群畸人身上所發生的故事,伊麗莎白·威拉德也是畸人之一。她的畸形最先體現在形象上,書里形容她“長得又高又瘦,臉上殘留著天花的疤痕,雖然只有四十五歲,卻被一種說不清的疾病耗空了熱情。常在自己凌亂破舊的旅店四處轉悠,了無生氣,像個幽靈一樣”。[4]20
賽珍珠筆下的母親沒有名字,她在全文中都以“母親”稱呼,她的形象與伊麗莎白不同,“寬而且壯的臉和豐滿的嘴唇,顯出被風日侵透的紫色來,她的一副眼睛,在閃耀的火光里發亮——異常清楚,不偏不斜地正臥在眉毛下面。她的臉并不好看,但是充滿著熱情和慈愛。人人都說她是個敏捷的女人,溫和的賢妻良母,并且很孝敬她家里的老太婆”。[5]這無疑是大多數在田間耕作的農婦形象的代表,如她沒有名字而僅僅以一個符號似的“母親”出現一般,這一母親形象具有一種普適性,她不特指誰的母親,而是20世紀初廣大中國農村母親形象的縮影。
伊麗莎白與賽珍珠筆下的母親外形上的差異無疑是顯著的,一個外貌畸形,一個外貌普通,她們不同的外貌也體現出她們所代表的不同群體。伊麗莎白代表了受到大機器影響下的西方社會中的女性形象,她的外貌畸形折射的是一種內心的畸形;而賽珍珠筆下的母親代表的則是最普通的中國農村婦女形象。
不管是伊麗莎白還是賽珍珠筆下的母親,都受到了男權社會帶來的傷害。伊麗莎白年輕時為夢想所作的努力,因為身處男權社會,遭到了小鎮里各種非議,換來了“不踏實的名聲”;在男性掌握絕對話語權的社會中,她始終處在“失語”狀態,年輕時對旅客傾訴自己的夢想,卻換來了他們的不以為然,婚后她無法表達自己內心的痛苦與渴望,甚至對自己最親愛的兒子都無法進行正常交流,在兒子終于按照她希望的那樣選擇離開小鎮時,她激動得不能自已,卻連表達內心喜悅的能力都失去了;在臨終前,她想和兒子說800塊錢的事,然而失語的她一直到死都沒說出來。
賽珍珠筆下的母親更是深受其害,她明明有足夠的能力養活孩子,照顧家庭,但是因為所處的環境,她不得不自己寫家書假裝是男人寄回來的,好掩蓋她“被男人拋棄”的難堪,她甚至希望男人就死在外面別回來,這樣她的自立自強不但能得到眾人認可,還可以立一個貞節牌坊;在與管事意外有了孩子后,她原想一死了之,但是擔心尸體被別人看出異樣會讓孩子蒙羞,她只能冒死打掉孩子;她寫了一封假裝男人死在外面的家書,想以此能與管事在一起,最終也只是被管事玩弄一場。雖然她的丈夫早已拋妻棄子、離家而去,但母親始終不能擺脫他對她所造成的影響,一言一行都深受其擾。母親也處于男性主導話語權境況下造成的“失語”狀態中,在男人拋棄他們一家時她要強裝歡笑,在冒死打掉胎兒又被管事玩弄時她沒法哭泣,唯有假裝收到男人死訊的家書時她才放聲大哭,將自己所有的苦楚痛哭出來,而這一切只是因為在她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女性是無法自由表達出內心痛苦的。
二.中美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抗爭
不管是伊麗莎白還是賽珍珠筆下的母親,都因為身處男性主導的社會中遭受種種痛苦,甚至在他們的男人在家庭處于“缺席”狀態的情況下,仍因為身處的環境而不得不面臨“失語”的狀態。正是由于中美社會發展進程的差異,使得相似處境中的兩位母親,在與社會環境抗爭時,選擇了不同的抗爭方式。
伊麗莎白的掙扎始終擺脫不了對男性的依賴,不論是最早依靠旅店客人、依靠情人還是依靠婚姻,其實,她一直夢想走出小鎮,去外面尋找更精彩的人生。當初在她父親強烈反對她與湯姆的婚事,并給她800塊錢讓她走出小鎮時,她的選擇是與湯姆結婚。在婚后她痛苦并掙扎,但她依舊沒有選擇離開,而是將夢想寄托在兒子身上。她在里菲醫生那里曾找尋到自我,但是這短暫的幸福就像白光閃過黑夜,只帶來片刻的光明,過后她仍深陷在漫漫長夜帶來的迷茫與痛苦中。最后,她尋找死亡以解脫,她將死亡人格化,“有時把他想象成一個強壯的黑發少年,正在翻山越嶺地趕來;有時把他想象成一個身上留有世俗生活印跡和傷疤的男子,冷峻而沉靜”[4]211。伊麗莎白的抗爭始終與男性掛鉤,她的抗爭是消極的,無力的,在發覺丈夫要將兒子引導成一個平庸的人時,她曾激動得顫抖,拿著剪刀想結束丈夫的生命,最終也還是放棄了。
而賽珍珠筆下的母親不同,她雖然也飽受男權社會的精神摧殘,但是她在艱難的人生之路上為了生存,為了年邁的婆婆與年幼的孩子,她毅然扛起全家重擔,種地、賺錢、養家。雖然她的一系列行動都需要假托男人在外工作的名義,但是她是依靠自己打拼出了全家的未來,她養大了子女并且在孫兒出世后得到最終的幸福。賽珍珠筆下的母親比伊麗莎白表現出更堅強的意志和更充沛的精力,她在受到男權意志傷害時不是自我扭曲,而是用極大的毅力、寬容和堅強為自己的生存而搏擊。在偽造了男人的死訊后,她徹底擺脫了男人對她的束縛,再次找回了她自己——那份從少女時期就一直存在的母性。
同為男權社會的受害者,兩位母親卻選擇了不同的抗爭方式,甚至連抗爭結果都截然相反,究其原因,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抗爭的目的不同。
19世紀七八十年代,工業革命浪潮席卷美國,位于美國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亦卷入其中,原本悠閑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被大機器的轟鳴聲打破,小鎮居民在欣喜工業革命到來的同時也感到了巨大的失落與迷茫,這份失落與迷茫被安德森放大成了一個個畸人。除此之外,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正處于經濟政治文化迅猛發展的時期,女性的地位日益提高,甚至在19世紀美國婦女首次跨入高等學府的大門,通過各種途徑,她們獲得參與社會活動的更多機會。[6]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俄亥俄·溫斯堡》中的女性并非為生存而抗爭,她們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層面的追求,她們為之奮斗的是她們內心的渴望,而不是存活的可能。比如伊麗莎白,雖然她家旅館破敗、生意不好,但是她并不是因為這個而掙扎,她一直在追尋的是小鎮外豐富多彩的世界,她痛恨的只是在苦悶小鎮中被苦苦壓抑的內心。這與那個時代美國女性已經超越溫飽層面的追求,而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有關;也與當時脫離了農耕社會,步入工業社會后人們有了一定閑暇來思考生活而不是生存有關。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賽珍珠《母親》的時代背景。《母親》寫于1934年,這個時期,書中所描繪的中國農村還處于男耕女織的農業時代,并且深受中國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男主女從、三從四德等思想的禁錮和毒害,與《俄亥俄·溫斯堡》的時代背景不同,農業時代男性往往是主要勞動力,所以當母親被她家男人拋棄時,第一個要面臨的便是生存問題。雖然母親也有精神層面的掙扎(與管事在廟里茍合),但她更多的還是在進行生存抗爭。也正是這個原因,讓母親的抗爭比伊麗莎白的抗爭顯得成功,因為母親的抗爭是為了活著,而伊麗莎白的抗爭則是為了女性的發聲權。
三.作家本人經歷對母親形象的影響
除了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造成了二者的差異外,作家自身經歷對這兩位母親的塑造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安德森的女性觀受到了他身邊眾多女性的影響,不論是他為了維持家庭生計而過度勞累而早逝的母親,還是同樣早逝的姐姐,都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來,他的母親和姐姐都有著自己內心的向往,然而殘酷的現實讓她們不得不為家庭奉獻自己,犧牲內心的渴望。這點從安德森在《俄亥俄·溫斯堡》的題獻上寫的“謹以此書獻給我的母親埃瑪·史密斯·安德森,母親對生活的敏銳觀察,最早喚醒了我窺視表面之下的渴望”[4]卷首可見一二。
這兩個為了家庭犧牲的女性讓安德森形成了傳統女性觀,即男人為主的思想。而安德森的兩任獨立自強的妻子,又讓他對現代女性有了新的認識。在這些女性的影響下,一方面,他學到了很多,他對這些女性感恩;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女性的強大——“當他需要她們的時候,他很恐懼,害怕失去自己的獨立”[8],這也正是他對筆下的女性飽含同情卻讓她們的抗爭都以失敗告終的原因。《俄亥俄·溫斯堡》的女性一生都沒有走出小鎮,最渴望走出小鎮的伊麗莎白最后是通過兒子才實現的夢想。不過安德森也給小鎮里的女人留有一絲希望,那便是七歲的小坦迪。坦迪出現在以她命名的章節中,她天真爛漫,未受到傳統陳腐觀念的侵害,作者借陌生人之口表達了對女性的一種期望:“我理解她,雖然我們從來不曾相遇過,”他輕聲說,“我理解她的奮斗和挫折。正因為遇到過這些挫折,她在我看來才顯得可愛。從她的這些挫折中產生出女人的一種新品質。我給它預備了一個名字。我管它叫坦迪。我想出這個名字的時候還是個名副其實的夢想家,身體也還沒有變得如此丑惡。這種品質即堅強地被愛。這就是男人需要從女人那里得到而又不曾得到的東西。”[4]127
亞里士多德曾不無歧視地為女人下了這樣的定義:“女人之為女人是因為她們的身體缺少某些性質,也因為這些天然的缺陷而遭受痛苦。”[9]但是安德森卻提出,女人比男人多了一種新品質,這種品質是男人需要從女人那里得到而又不曾得到的——“堅強地被愛”。雖然安德森對待女性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當時那種環境下他的女性觀已屬難得。
“從創作學的角度看,女作家描寫母親,往往有男作家不可替代的優長。由于性別類屬的原因,她們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是相通或相近的。”[10]賽珍珠塑造的母親比起安德森塑造的伊麗莎白來說更富有抗爭性,情感也更加細膩。由于女性特有的同理心的原因,她沒有安德森那種距離感,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以女性體驗洞察母親內心世界及微妙的情感變化,準確把握母親復雜的心理情態,為她描述倫理框架內所能實現的最大快樂和最高人生理想。[11]
賽珍珠就讀于美國弗吉尼亞州林奇堡市的倫道夫·梅康女子學院,她受到美國女權運動的影響,并把它植根于自己的創作之中[12],而長期旅居中國的經驗也讓她對中國傳統倫理觀有著深刻的認識。母親正是在這種雙重文化的影響下誕生的一位女性,她既比中國傳統農村婦女更富有抗爭性,又更多地停留在生存層面的抗爭上,這反映了當時東西方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女性不同的需求。
四.結語
安德森與賽珍珠筆下的母親用各自的方式在強大的男權社會中進行著女性的抗爭,由于時代背景的差異以及作家本人經歷的不同,兩位母親的抗爭也有所區別。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出東西方文明在同一時代的巨大差異是如何影響到兩位美國作家的。安德森飽含同情的筆觸雖然給了女性極大的關注,并且也借由小坦迪給予女性一定的希望,但始終脫離不了他以男性為主導的男權思想,他仍舊有一定局限性;而賽珍珠以女性獨有的視角將一位中國農村女人的抗爭描繪得生動精彩,卻依然受限于中國傳統思想觀念(認為孫子的出生使自己得到救贖)。雖然兩位母親的抗爭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當時那個時代背景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為打破女性的“失語”狀態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參考文獻
[1]楊仁敬.20世紀美國文學史[M].青島:青島出版社,2000:263.
[2]劉龍.賽珍珠研究:授獎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58.
[3]周亞萍.哀傷的詩意——賽珍珠《母親》中的生態女性主義解讀[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3(5):99.
[4][美]舍伍德·安德森.俄亥俄·溫斯堡[M].楊向榮,譯.海南出版公司,2012.
[5][美]賽珍珠.母親[M].萬綺年,譯.上海:仿古書店發行.1936:3.
[6]霍然.《小城畸人》中叛逆女性解析[J].文化研究,2009:235.
[7]賈麗麗.《溫斯堡·俄亥俄》:女性的禁錮[J].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2).
[8]Anderson D D. Critical Essays on Sherwood Anderson[M]. Boston:G.K. Hall,1981:254.
[9]何征.對《小城畸人》的女性閱讀[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1(3):34.
[10]徐紹峰.顛覆與重寫——新時期小說中母親形象的變異原因及意義[J].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1994(2):65.
[11]曲義.男性角色的弱化與男權秩序的內化——賽珍珠與安德森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對比[J].文教資料,2016(10):10.
[12]成秀萍.母性·妻性·女性——論賽珍珠的長篇小說《母親》中的母親形象[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10(5):109.
(作者介紹:傅蕾,集美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